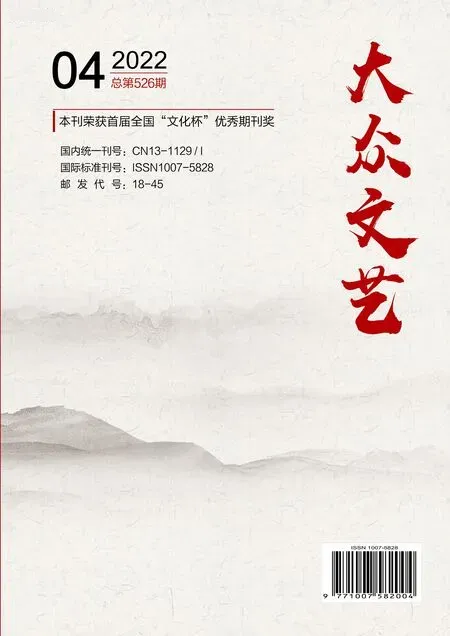北齊時期響堂山石窟造像藝術探究
王鉦雯
(吉林藝術學院藝術學研究所,吉林長春 130021)
響堂山石窟群因造像體量之多、雕鑿之精美,近年來已聞名遐邇。石窟內北齊時期的佛造像一改前朝之風由清瘦變豐腴;享堂融于石窟建制且中心方柱式塔廟窟與三壁三龕式佛殿窟并存,既是賞玩之地也是文化之瑰寶,頗具藝術價值。
一、位置分布及概述
響堂山石窟群位于今河北省邯鄲市峰峰礦區鼓山,因其談笑走動間發出的回聲和“兵亂則鳴”的響聲而得名,主要由南、北響堂山和水域寺石窟構成。鼓山西麓的北響堂山石窟現存主要洞窟九座,開陵墓與造像結合之首創,既是賞玩禮拜之地,又是一座陵寢祭祀的“享堂”。
比起文宣帝高洋(北齊開國皇帝),其父高歡才是北齊王朝的真正締造者,北洞(大佛洞頂)便是高歡入葬(一說為“虛葬”)的陵寢所在。不同于皇家營建的北響堂山,開鑿于北齊天統年間的南響堂石窟其秩序感略低,是一座由寵臣高阿那肱廣施善財而營建的“口口”(千佛)之窟,以第一窟華嚴洞和第七窟千佛洞最為著名。繼北、南響堂山后,小響堂山(水浴寺)依次在北齊年間完成開鑿。
如果說被封為北齊神武帝的高歡擁立元善見建立東魏、遷都鄴城并草創響堂山,那么高洋以及其后的北齊王朝則完成了石窟主體工程的鑿建,后經隋至元明各代增鑿,形成響堂山石窟群,內有大量佛、菩薩、天王、力士造像,堪稱一座藝術的殿堂。
二、響堂造像樹新風
回溯北齊之前的石窟造像可以看出,早期佛像受印度犍陀羅藝術影響,在新疆形成獨特的龜茲和涼州模式。北魏滅涼定都平城繼承此前的造像風格,據印度范式開鑿的“曇耀五窟”以五位帝王為塑像主體,深目高鼻、大耳垂肩、面相方圓、兩肩齊挺,威嚴生畏。而后遷都洛陽的孝文帝進行漢化改革,習南朝文人瘦骨之風開窟造像,呈現出秀骨清像、褒衣薄帶等特征。元魏分裂后定都鄴城的東魏很快也被北齊高洋政權取代,開窟響堂山、天龍山。受高度鮮卑化政權影響,以響堂山為代表的北齊造像在體態上由秀骨變豐滿,雕鑿特征介于北魏與隋唐之間,既承前朝又啟后世。
(一)造像特點與分析
響堂山石窟造像面圓體豐、眉彎似弧、高鼻長目,形似瓶筒,多粗笨硬直;肩寬頸粗、肌肉豐滿,造型樸實敦厚,展現出北方民族的健壯形體。
石窟內佛像面相豐滿、發式螺旋,神態溫和;背鑿以忍冬紋、卷草紋、飛天、蓮花穿插其間的圓輪頭光以示圓滿;身著袈裟,以通肩式、中衣搭肘式為主;寬肩鼓胸、身形粗短,敦實健壯。以北響堂山北洞和南響堂山第一窟華嚴洞中心柱正壁釋迦像為例,佛像摒棄了清羸秀骨,更具重量感、立體感,與曇曜五窟徒具威嚴的佛像相比更莊重溫和。
窟內菩薩造像頭戴花蔓冠、寶繒垂肩,衣裙柔軟適中,腹部略鼓、肢體豐腴,以筒形體態為主,或身姿規矩或身段靈活。最具女性柔美之氣的當屬北洞左大龕左側脅侍菩薩:上身袒且著披帛斜跨瓔珞,下著裙其裙裾緊貼似出水;曲左膝點足尖且重心在右,下肢比例略短卻靈動自然,其靈活生動的造型開唐代“濃艷豐肥”“細腰斜軀”的菩薩體態之先。
此外,弟子和順且脅侍主尊于側,天王披盔甲似北方武將,力士身健壯且造型生動,飛天面豐圓其體態婀娜,眾造像動靜結合、個性鮮明。
(二)風格歸因及影響
元魏瘦骨清像的造像形態到了定都北方(鄴城)、重回鮮卑之氣的北齊王朝手中則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并由此形成影響隋唐的北齊造像樣式。
1.元魏造像顯秀骨
秀骨清像原是陸探微表現南朝文士重玄學尚清談且相貌清秀瘦削的人物畫風。伴隨南北朝藝術的交流并適應于漢化改革,元魏遂將秀骨清像的體態引入石窟雕刻。至此北魏造像由鮮卑的粗獷強悍變為如龍門石窟賓陽洞造像般面容清瘦、削肩瘦長、褒衣薄帶的模樣。
與其說包含元魏在內的南北朝造像所體現的秀骨之風來自士族理想化的人格表現,不如說那種重視精神與義理的瘦骨與微笑是統治者為掩蓋戰亂的苦楚而迫使百姓吸食的精神鴉片,故形成愈瘦削愈高妙、愈悲慘愈微笑的佛陀塑造。佛像睿智的微笑雖在北齊時代轉為笑意卻難掩殘暴統治下的苦難,北齊皇室依然借佛教思想達到實施政治統治的目的。
總體來說,來源于陸探微的繪畫之風、根植于動蕩社會形態的秀骨清像特征成了南朝至北齊以前的造像主流,于元魏時期尤盛。
2.北齊造像變圓渾
雖為漢人建立卻極具鮮卑之氣的北齊王朝,自高歡時期起就極度抵制元魏漢化,于東魏-北齊時期開鑿的響堂山造像一改秀骨而變圓渾,但此時北齊雕刻樣式并未統一。正如唐仲明所說,由于胡漢矛盾促使武成帝“河清改制”并加快了政權的“漢化”,其政治因素的回旋導致了鑿刻特征的些許回歸:菩薩披帛呈X形于腹前交叉,其北洞左大龕菩薩的靈動姿態也變得如中洞般規矩起來,甚至是蹤跡全無,此外袈裟樣式亦有所改變。從總體來看,自武平時期起北齊石窟鑿刻特征整體趨同,并逐漸形成以響堂山為代表的北齊造像樣式。
如果說瘦骨寬袍、面帶睿智微笑的造像特征根植于亂世,那么東魏(北齊)則伴隨朝代更迭而審美突變,故雕刻特征由清癯而變豐腴。若從繪畫與雕塑的關系來看,北齊時期還受“其體稠疊”的曹家樣影響,又盛行南朝張僧繇“面短而艷、得起肉”的繪畫之風,遂開雕塑之體范。
3.豐腴體態啟隋唐
北齊時期除響堂山外,還開鑿包括天龍山、小南海等多座石窟,特點因地而異但大致與響堂山石窟相同。以響堂山為代表的北齊造像整體呈現出由強健體魄代替南朝清弱示病的文士之態,變瘦長為鼓圓并逐漸由線的刻畫轉入立體塑造。
自此從北魏早期云岡石窟的威嚴莊重帝王體貌到龍門時期的瘦骨清像,再到北齊天龍山、響堂山石窟之轉變,逐漸向隋唐的豐腴體態過渡。如果說北齊造像是在高洋的殘暴統治下為適應鮮卑政權而形體敦實健壯,那么唐代的豐腴體征則是盛世之下的雍容華貴之態,極具時代風貌。此外響堂山石窟除一鋪三身或五身之外,還增加了一鋪七身的造像組合,此種模式也于隋唐時代普遍流行。
三、石窟形制與特色
(一)內外部窟龕形制
從外部崖面看,響堂山以覆缽式塔形窟為主,也存在樓閣式塔形窟,融合佛教石窟、意為墳冢的印度古塔窣堵波以及中國傳統木構的建筑形式,是本土與外來樣式相融合的石窟形制典型。此外,于塔身處開帷幔帳形龕、每龕一佛,上為塔剎(覆缽丘)、下為塔基的塔形(列)龕廣泛存在于北響堂山窟內四壁和天宮路中段(含北側)。
若從石窟內部平面看,最具特色的是中心方柱式塔廟窟。中心柱窟從印度傳入并歷經新疆龜茲、云岡、龍門石窟的演變逐漸被佛殿窟代替卻被響堂山重新引入并改進:石窟內柱由四面開龕的多層中心塔柱變為三面開龕的單層中心方柱,并于柱后下鑿低矮甬道,形成獨特的響堂山中心柱窟樣式。然而除北洞、中洞和南響堂第一二窟、水浴寺西窟采用中心柱窟形制外,其余多數石窟仍然沿用北魏以來的三壁三龕式佛殿窟(如南洞)以便禮拜禪修。
(二)塔形窟與中心柱
塔形窟是響堂山典型的石窟形制。然而南響堂山與北響堂山雖同為覆缽塔形窟,卻不同于北響堂的陵寢意味而更像是具有裝飾性質的建制繼承。可以說北齊高洋時期已將響堂三窟看成是可將父、兄甚至自己安葬于此的轉輪王靈廟,以祈盼國祚永隆。以帝陵實葬又以佛教轉輪王入葬塔窟的方式,昭示著皇帝的“雙重天命”政治性身份即一種作為世俗最高統治者的神圣化天命表達。
此外,如果說塔形窟的開鑿與印度傳入的佛塔崇拜緊密相關,那么篤信佛教幾近迷狂的北齊皇室以內矗中心柱的形式開鑿塔形窟則是佛塔崇信之風的高度再現。以北響堂山為例,僅于中心柱正面開鑿佛像的中洞內有脅侍菩薩、外有力士把守,更像是皇室氣派的對應,而北洞卻因其頂部安葬高歡陵墓的特殊性于中心方柱三面鑿龕以便背面深入山體。
獨特的中心柱窟雖對后世的影響不大但對于北齊而言卻意義深遠。如果說塔窟是代表著北齊統治者期盼永生、世代為君的靈塔,那么可以繞行禮拜的中心柱運用到陵寢性質的北洞、中洞則既是具有紀念意義的佛塔簡化物,又是百姓禮佛和祭帝的雙重象征。對于入葬于此的帝王來說,即便王朝覆滅但其轉輪圣王身份并不會為遠去,還可繼續接受萬民的朝拜與供養。
四、藝術價值及啟示
響堂山石窟變瘦長為豐腴的造像特征、一鋪七身的造像組合承北魏啟隋唐;融享堂于建制,其低矮的甬道設計方便僧眾及百姓禮拜;鑿外立面于覆缽塔型又于平面呈現出中心柱窟與三壁三龕窟并存的石窟形制,體現了本土與外來樣式的合璧,由此形成了以響堂山為代表的“北齊模式”,頗具研究意義和藝術價值。
因而可以說走進包含常樂寺、宋代磚塔、磁州窯在內的響堂山風景名勝區,探尋集中國建筑、雕刻、美術等藝術樣式于一身的響堂山石窟群便如同開啟了一場對話古今的時光之旅。然而窟內多數頭像和肢體的缺失也令人感愧,它們或流散異國或于“文革”期間鑿毀。因此繼學者唐仲明通過三維建模技術復原南響堂山第二窟大致風貌后,中國社會還應接續運用數字技術復原響堂山石窟內部景觀。與此同時當下中國還應以響堂山石窟群等文化遺址為起點講好文化故事,開啟文物保護、中外合作、學術交流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