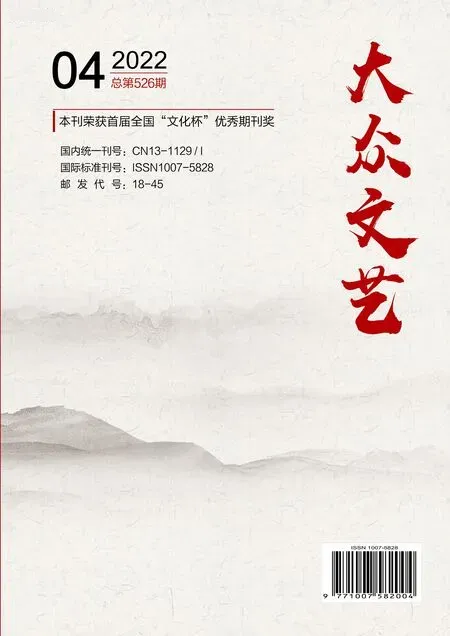淺析美術作品中的羽人形象
李承寅 於玲玲
(南通大學藝術學院,江蘇南通 226007)
一、中外美術作品中的羽人形象淺析
在世界各地的文學、美術作品中都能看到“羽人”“天人”的身影。《楚辭·遠游》中有寫道:“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顧名思義,羽人便是身長羽毛或批羽毛外衣的人。由于文化的地域性,不同區域的羽人都會被當地特有的文化賦予不同的角色和形象。
1.佛教藝術作品中的飛天形象分析
在佛教誕生的古印度,流傳著許多關于天人的傳說,如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講到希達太子誕生時:“天龍八部亦于空中作天伎樂,歌唄贊頌,燒眾名香,散諸妙花。”其文中的天龍八部,便是指佛國世界的“天人”。不過學術界對此還有一定的爭議,有的學者認為天人是天龍八部的總稱,也有的學者認為天人是天龍八部中的“乾闥婆”與“緊那羅”。
在古印度各個地區的雕刻作品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天人的雕刻。在巴爾胡特佛塔的雕刻作品《圣樹供養》中可以發現,在雕刻的最上部分有兩個飛來的飛天。他們在人們供養的圣樹之上,他們的身體橫向,一個從左邊飛來一個從右邊飛來。翅膀張開扇動著,左邊的飛天一手握花籃一手抬起作散花狀,右邊的飛天雙手捧著一串花環,似乎想要獻給圣神的菩提樹。巴爾胡特的佛教雕刻作品中的飛天大部分動作略微僵硬且只表現上半身,也許這是藝匠們給觀者專門留下的思考空間吧。
同在圣樹供養這個主題表現的作品中,山奇大塔的飛天的形象略微產生了一些變化,變成了半身人半身鳥的形象,有點像希臘神話中誘惑水手的海妖塞壬。在印度佛教壁畫中,半身半鳥的天人很常見,他們一般為四身或者六身,被稱為迦陵頻伽。山奇大塔中的飛天一手持花環一手舉著裝滿鮮花的盤子,動作比巴爾胡特中的天人雕刻更為生動形象,表情雕刻得更加真實,面部的角度也各有分別。可以見得,佛教中飛天的形象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為生動,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之下,佛教飛天往往和基督教天使扮演著相似的角色,都是作為宗教題材藝術作品中的配角,逐漸形成一種符號化的形象語言。
在后來的印度佛教藝術作品中,飛天逐漸形成了固定的動作,有“散花式”“前后腳騰飛式”等等。當佛教傳入中國,漸漸形成了璀璨的敦煌藝術。飛天的翅膀也被去掉,只留下滿壁風動的飄帶讓人感受其靈動與飄逸。中原美術對飛天藝術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北魏時期形成的眉清目秀、巧笑倩兮、身體修長、衣裙飄舞的飛天形象,被稱為“中原風格”。正是由于“氣韻生動”觀念的影響,藝術家們注意到了飛天的整體神韻,忽略了飛天的身體比例,添加了極具韻律感的飄帶、衣褶。
2.道教影響之下死后的普通人形象分析
道教的興起,使飛行、升仙不再是一種幻想,而成為一種通過努力就可以完成的實踐活動。以長生不老、得道升仙為最終目的的道教中,關于飛行的幻想源遠流長。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T型帛畫就給我們構建了一個死后的世界。金烏、玉蟾、巨龍、升仙的墓主人一系列的圖像表明,當時的人們在道教的影響之下對人死后升仙享福的無限憧憬。直到魏晉時期,對這種神仙的描繪也非常普遍,在中國西北酒泉出土的丁家閘五號墓的南頂有一個羽人形象,他正張開雙臂在空中飛行,兩條腿向上翹著,肩膀后有一對翅膀在扇動,像是在保持平衡的樣子。裙子上裝飾著粉色和白色的衣褶,隨著風飄動,裙子的邊緣還綴有羽毛的裝飾。臉上也帶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經典妝容,神情熠熠,伴隨著身邊的巨龍與祥云,似乎在享受著得道成仙的樂趣。這也許就是古代中國人心中,羽化升天的真實樣子吧。
道教中的羽人形象一般繪制在墓室里,以墓主人的形象為原型進行藝術加工,以期盼死后羽化升仙。因此,道教中的羽人形象大多描繪的是普通人的樣子。與基督、佛教不同的是,道教中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飛升成仙,仙界的大門向每一個普通人打開。
二、羽人形象誕生的原因分析
1.人類地對鳥類的翅膀崇拜
翅膀是鳥類飛行的工具,在人們的想象之中,只要翅膀足夠大,便可以承載自己進行飛行。早期羽人形象的誕生,正是對鳥類的崇拜,而這種對鳥類的崇拜實質上是對鳥類翅膀的崇拜。在《山海經》之中,也有大量的有翼動物、羽人國之類的描述。古人把鳥類的翅膀與人類嫁接,滿足了自身對飛行的渴望。
在各地的神話故事或傳說之中,也有許多鳥類的傳說,甚至把鳥類作為圖騰也非常常見。在中國傳說中的,鳳凰、玄鳥、鯤鵬、金烏都是以鳥類為原型進行發展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商民族就把玄鳥作為自己圖騰,而玄鳥被認為是以燕子為原型衍生出的。先秦時期的傳說也證明著鳥類對人的影響之大:在洪荒之時,地上的草叢中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蛋,蛋孵化出來便是一只鵪鶉,再由鵪鶉演變成人類。在長江、黃河出土的遠古彩陶盆也有許多鳥類的紋樣,比如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鸛魚石斧罐》及《魚鳥紋彩陶壺》,都是鳥類在人類文明形成初期對人類產生重要影響的證明。
2.男權社會之下色欲的產物
印度的佛教藝術出現了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在神圣莊嚴的佛教形象之中,出現了充滿色欲的男女天人形象與故事,與佛教嚴肅、寡欲的特點截然不同。
印度佛教藝術中的天人們,有時會男女成對出現,往往第二性征明顯,且舉止親昵。比如阿旃陀第十六窟的飛天,左邊是身材魁梧的男性飛天,右邊是半身赤裸的女性飛天。女性飛天的右手從男性飛天的脖子后繞去,男性動勢向女性前傾,兩人作曖昧依偎狀。女性飛天的左腿自然的跨在男性飛天的大腿之上,右腿也疊在左腿之上,男性飛天的右手也緊緊握著女性飛天的腳踝部位,兩人舉止親昵。這樣的男女飛天的曖昧形象,我們在很多處的印度佛教藝術中都可以找到。在阿旃陀的第二窟的天人壁畫,刻畫了兩依偎在天空飛行的男女飛天。這種表現男女之情且故意凸顯女性之美的形象,就是古印度藝術之中,所謂的“艷情味”。一邊表現莊嚴感的同時,一邊又表現著極具世俗味的藝術形象。這便是古印度佛教藝術中有趣的矛盾沖突。這種矛盾沖突,往往體現了男權社會下女性藝術形象中色欲的介入。
我們可以從古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找到關于創世紀之初的“攪海”的故事:“這些美妙秀麗的天女,總數一共有十六億。羅摩呀!他們還帶著數也數不清的女婢。所有的神仙和檀那婆沒有一個想娶她們。因為沒有人把他們娶,他們就成了公共的女人。”(《季羨林文集》第十七卷)倘如把這些天女的故事放置到現如今的任何一個女性的身上,對她來說都是一種災難,她們沒有犯下任何過錯,卻淪落成神世界的娼妓。除此之外,天女們往往在故事中被神派遣,利用自己的美貌來誘惑他人以達到某種目的。
三、“天人合一”與“征服自然”的哲學思想對天人形象的影響
中西方哲學方面對天與人之間的關系有著本質上的差別。在中國的哲學思想中,人與自然應當是和諧相處、共生的,這正是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的體現,在西方的哲學思想中,人是萬物的尺度,自然是客觀存在的事物,人應當多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
天人合一的思想影響了中國的佛教藝術,讓飛天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逐步變成一個個姿態萬千、各有風趣的“人”的形象。古印度的佛教中的飛天發展到后期,演變出了具有顯著特點的飛天形象并具有程式化的飛天形象。在北涼的洞窟壁畫飛天沿襲了這一傳統,我們可以通過服飾、頭光辨認出飛天。魏晉以來,隨著“魏晉風度”的吹襲,飛天逐漸具備了中原的特色。身子瘦弱、體態修長,顯得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但是這還不夠,還要配上較多的衣服,衣帶隨著風飄飛,反倒有一種飄飄欲仙的樣子。飛天們換上了中原的衣服,頭上的光環有時也消失不見了。我們可以從江蘇省丹陽市出土的畫像磚中看見,飛天換上了中原地區人們的衣服,修長身體被隨風飄動的衣帶所裹覆。莫高窟北魏窟中同樣也出現了很多中原化的飛天形象,第285窟的兩身聽法的飛天便是漢族少女的形象,同時該窟也出現了兩位裸體的童子飛天。飛天第一次,以普通人的形象出現在人們面前,讓人和神之間的隔閡不再如溝壑。莫高窟飛天的這一變化,標志本土佛教藝術的世俗化,便是人與神打破隔閡,達到合二為一的地步。北魏時期的敦煌飛天為后世的飛天演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隋代以來的飛天形象,逐漸去掉了標志性的頭光,讓神蛻變成了人。
天人形象作為世界各地共通的一種藝術形象,在各個地域產生了不同的樣式。每個地區的飛天形象都有其地域的特點,這也正是藝術的地域性特點之體現。生理特點是心理審美的前提,即生理的需求決定了審美方式。因此,由于地域差異,飛天的形象也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世界各處人們對于天空的渴望,以及人們對神界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