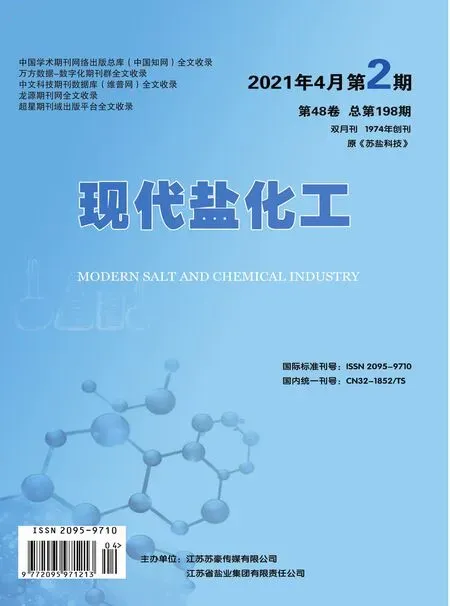新精神活性物質的研究進展
李妮娜
(上海迪安司法鑒定有限公司,上海 200433)
世界衛生組織給新精神活性物質的定義為:通過主動或被動的方式進入人體生理系統后,能夠影響人體精神判斷能力的物質。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通過對國際上因濫用新精神活性物質而引發的犯罪問題進行分析,給出了新精神活性物質的定義:不在《麻醉品單一公約》和《精神藥物公約》的管制范圍之內,以任何形式被濫用,都會威脅公共衛生健康安全的物質。我國對新精神活性物質也有較為明確的定義。2015年9月,公安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國家衛生計生委和國家禁毒委員會辦公室聯合制定的《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列管方法》中,將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定義為“未作為藥品生產和使用,具有成癮性或者成癮潛力且易被濫用的物質”。如今,新精神活性物質卻被認為是主要為娛樂消遣而生產的“合法興奮劑”“設計師藥物”或者“植物興奮劑”,并且在這種物質的制造過程中,通過有意識地衍變來逃避法律的制裁,同時對大眾隱藏其毒品的身份[1]。
1 新精神活性物質的種類和特點
1.1 新精神活性物質的種類及其危害
合成大麻素類是濫用最多的新精神活性物質之一,為大麻素受體激動劑。合成大麻素屬于烷基吲哚和環己基酚類,能夠與已知的大麻素受體CB1和CB2結合,產生的致幻作用與四氫大麻酚(THC)相似[2]。長期吸食合成大麻素類,會產生心血管系統疾病及精神錯亂,其成癮性和戒斷癥狀也與天然大麻類似。合成大麻素常常被高比例地混合使用,在藥理上,藥物可以在人體內發揮協同作用,可使人獲得欣快感,具有抗焦慮、抗抑郁等效果,但大量吸食則會引起偏執、心悸以及幻覺[3]。
卡西酮類是常見的新精神活性物質,比如甲卡西酮、4-MEC和MDPV等。藥品形態多樣,有片劑、粉末、膠囊、晶體等,可以引起多巴胺釋放,產生刺激性影響[4]。吸食卡西酮類物質有較為明顯的藥理學和毒理學作用,會對人體健康產生較為嚴重的損害[5]。濫用卡西諾酮的臨床癥狀包括焦慮、抽搐、恐慌、記憶力減退、注意力不集中、幻視、幻聽、嘔吐、大量出汗、癲癇、腹痛、眩暈、偏執及妄想等癥狀,長期過量使用,易造成不可逆的永久性腦部損傷甚至死亡[6]。卡西酮類化合物具有非常相似的化學結構,例如3-MMC和4-MEC的區別僅是苯環3位的甲基換成了4位、氨基上的甲基取代換成了乙基取代以及3-MMC與3-CMC也只是苯環取代基不同。這些細微的化學結構改變,使得卡西酮類物質難以及時定性且很難受到法律限制[7]。
色胺類是一組單胺生物堿,基本結構是吲哚乙胺,其與內源性神經遞質5-羥色胺(5-TH)非常相似,起到了5-HT2A受體激動劑和5-TH重攝取的抑制劑作用,進入人體后能引起視幻覺,如感覺、直覺的改變,甚至出現精神分裂癥狀[8]。
植物類新精神活性物質,如墨西哥鼠尾草,原產于墨西哥,可作煙草吸食,也可以咀嚼和泡茶[9]。因為有迷幻性,若被濫用,會產生類似麥角酸二乙酰胺(LSD)和苯環利定(PCP)經典迷幻劑的作用,只是持續時間和損傷程度相對較小,但其引起的迷幻作用足以讓人興奮以及產生焦慮人格解體等,對吸食者和社會將造成無法預估的后果。
除此之外,還有苯二氮卓類、苯乙胺類、哌嗪類物質等,種類繁多,結構復雜,幾乎在藥理上都具有成癮性。合成的新精神活性藥物不斷調整分子極性和結構,使藥品進入人體后,中樞神經系統作用增強,對吸食者的身體造成極大的威脅[6]。了解新精神活性物質的毒性作用,是為了更好地監管和監控,以減少其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危害。
1.2 新精神活性物質的特點
1.2.1 不在國家管制藥品之列
新精神活性物質是在被管制藥物分子結構上,利用化學方法,合成具有相同或相似精神活性作用的物質。因為這種新合成的化學結構與國家現有的管制藥品有一定差異,所以很難運用法律對其制造以及銷售行為加以制裁。由于各國規定管制的精麻藥品的種類不盡相同,新精神活性物質在種類上也有所差異。我國早在1996年便將卡西酮類藥物中的卡西酮和甲卡西酮列為國家管制的第一類精神藥品,但由于在其他國家未予列管,仍屬于新精神活性物質,這就在跨國執法上存在一定的難度。毒品的濫用走私問題已經使許多國家的禁毒部門忙得焦頭爛額,對于新精神活性物質的醞釀發酵問題根本無暇顧及,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這種“準毒品”泛濫[10]。
1.2.2 濫用后果嚴重
新精神活性物質在社會上造成的濫用危害,與國家規定管制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相似。一方面,新精神活性物質由于具有興奮和致幻作用而吸引毒品消費人群;另一方面,新精神活性物質又由于其較強的藥物依賴性,容易被濫用成癮[11]。藥物成癮是一種慢性復發性腦病,典型特征為強迫性覓藥、無限制用藥、中斷用藥后出現戒斷癥狀,會對人們身心造成嚴重傷害[12]。
1.2.3 更新換代快
為逃避法律的懲處,境內外不法分子會在一種新精神活性物質被部分消費國家管制后,研發出尚未列管的新品種,因此,新精神活性物質品種在快速增加。目前,由于不法分子改進了合成方法,加快了新精神物質更新換代的速度,再加上吸毒人群的壯大,毒品貨物供不應求。犯罪分子利用新精神活性物質變種靈活、合成簡便的特點,不斷尋找新物質[13]。然而,立法的速度往往沒有如此快捷。116種新精神活性物質被一次性增列在《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列管辦法》中,卡芬太尼、呋喃芬太尼、戊酰芬太尼、丙烯酰芬太尼4種物質,在2017年2月被公安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以及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列入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制品種增補目錄,將我國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質增至134種。國家在16個月內增加列管18種新精神活性物質,也只是對犯罪分子已研發品種的補救性防控措施,更多新研發的新精神活性物質仍未被列管[14]。
2 新精神活性物質的檢測
2.1 氣相色譜-質譜聯用法
氣相色譜-質譜聯用法將氣相色譜和質譜的功能相結合,質譜作為氣相色譜的檢測器,提供更加豐富的碎片信息,靈敏度高、分離效果好、分析速度快,是一種實用的分析方法。衍生化雖然程序相對煩瑣,但是可以改善化合物的揮發性,形成很好的峰形,使得此方法在新精神活性物質的分析方面得到廣泛的應用[15]。
2.2 液相色譜-質譜法
與氣相色譜-質譜聯用法相比,液相色譜-質譜法不需要進行衍生,對于不易揮發、穩定性差的新精神活性物質,可以簡便快速地進行分析。液相色譜與串聯質譜的聯用可以提高實驗效率,且重復性好,適用于新精神活性物質的快速鑒定。
2.3 核磁共振法
核磁共振可以更好地識別未知物,如果單純地使用氣相色譜-質譜聯用法或液相色譜-質譜聯用法,只能提供有限的結構信息,并且新精神活性物質結構復雜,會產生誤判的風險。如果與核磁共振相互配合,提供更加完整的結構信息,可以對新精神活性物質進行更準確的分析[16]。
2.4 紅外光譜法
紅外光譜法是一種廣泛用于藥物研究和結構鑒定分析的技術,可以提供豐富的化學結構信息,具有檢測迅速、操作簡單、重復性好、靈敏度高、檢查使用量少等特點,但不適合混合物中目標化合物的識別,因此,需要先對查獲的新精神活性物質進行分離提純,之后才能進行分析。此外,分析工作中還有一些方法,比如毛細管電泳法、薄層色譜法、酶聯免疫法等。
3 新精神活性物質的管制方法
據預測,由于新精神活性物質的制造方法相對簡單,衍生、變異品種多,市場復雜易變,未來我國新精神活性物質違法犯罪現象可能出現反彈上升。由于新精神活性物質品種的持續增多,制造和走私新精神活性物質可能出現新問題。新精神活性物質濫用現象的加劇,也使新精神活性物質的管控、查處、打擊等工作面臨新的挑戰和壓力。
新精神活性物質是為了逃避法律管制設計出來的,每當某種新精神活性物質被列入管制后,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有新的替代物質被創造出來,使被列入管制的物質的濫用性大幅下降,因此,新精神活性物質很難被管制。以美國為例,最初JWH-018是濫用最嚴重的合成大麻素,占尿檢陽性樣品總數的87%。但自2011年列入管制后,該物質迅速被另一種合成大麻素AM-2201取代,占陽性樣品總數的比例高達99%。卡西酮類物質也存在同樣的現象。2011年以前,美國濫用最多的卡西酮類物質是MDPV和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二者合計占陽性樣品總數的90%。但自2011年列入管制后,二者幾乎在市場上消失,而新出現的卡西酮類物質PVP,占陽性樣品比例達85%。
目前,各國正在積極采取適合本土的管制方式,一般在美國、英國、德國、丹麥及西班牙等國采取臨時管制。當相關部門發現一種可能存在濫用風險的新精神活性物質時,可在1~2年內臨時管制,管制措施等同于正式列管毒品。在此期間,警察及衛生部門有充足的時間對該物質的危害進行評估,最終決定是否正式將其列管。在英國、德國和荷蘭,臨時管制文件由相關部門的部長簽署即可生效,不用提交議會通過審議,有效保證了臨時列管的及時性。美國則使用類似物管制,含義是“對人體作用(興奮、麻醉、致幻)類似或強于管制毒品且化學結構與其類似的物質也屬于管制范圍”。通過類似物管制法,有效解決了層出不窮的新精神活性物質的管制問題。但是由于“類似物”本身的定義含糊不清,法庭在很多情況下難以判斷一種物質是否屬于管制毒品的“類似物”,而美國目前也沒有給出關于“類似”標準的具體解釋[17],使其在實際操作中有一定的困難。骨架結構管制被美國、俄國、澳大利亞和諸多歐盟國家使用,含義是將含有特定化學骨架結構的物質全部納入管制范疇,屬于“類似物管制”的延伸,定義更明確,可操作性更強,有效解決了通過化學修飾創造新的物質,進而逃避管制的問題,不足之處在于不含已管制骨架結構的新精神活性物質仍被發現和濫用,且對國民經濟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因為一些在制藥、化工等領域可能有潛在使用價值的物質,由于含有管制骨架結構而被列管,其研究和開發都會受到限制[18]。
在我國,與傳統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列管方式相比,《非藥用類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列管方法》規定,以國家禁毒主管部門,即國家禁毒委員會辦公室為主負責,會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衛生計生委共同進行新精神活性物質等非藥用類精麻藥品品種的管制調整。同時,將聯合國已管制或已在國內形成現實濫用危害的品種,以及我國有生產、無濫用,但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已造成濫用危害的品種納入列管范疇。目前,已有170種新精神活性物質被我國管制[19]。
4 討論
綜上所述,隨著新精神活性物質被進一步研究,人們認識到新精神活性物質濫用的危害和防控的緊迫性。目前,地下實驗室仍然不斷加大對精神活性物質的研究力度,新的種類和數量持續增加,因此,應當加大對新精神活性物質分析方法的研究力度,加強危害認識,積極建立防控機制,有效抑制新精神活性物質的濫用。聯合國對新精神活性物質管制的倡導建議包括兩個方面:建立預警系統和完善管制措施。首先,以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為樞紐,以實施“分析—報告—趨勢”方案為重要途徑,在全球、區域和國家3個層面上建立預警系統。其次,將管制措施分為法律管制與非法律管制,如制定臨時性管制法案、“一般性”分類法、“類似物”分類法和“緊急分類”等,抓住防范與遏制合成毒品濫用的最佳時機,在國家主管機構對有關精神活性物質進行全面評價之前,避免讓公眾面臨不必要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