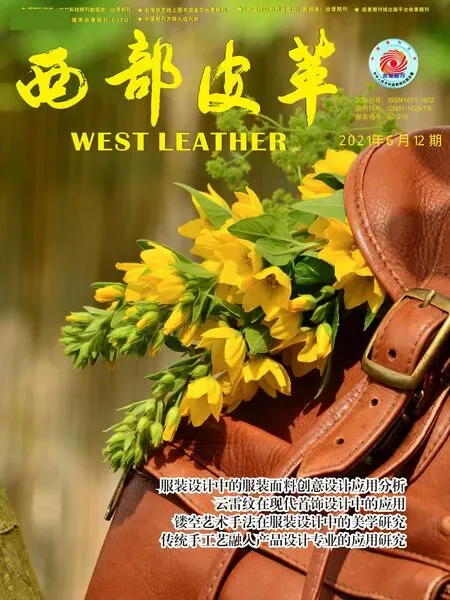苗族鶺宇鳥圖案在設計中的跨界融合與創新
李秋,向婭華
(凱里學院,貴州 凱里 556000)
在《考工記·總序》中記載:“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百工是最早對于手工藝的稱呼。手工藝是解決人們在生活起居中所遇到的衣食住行相關問題的技能知識。
用現在的概念來說,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了“民族性”“非物質性”“文化性”“遺產性”“保護性”這幾個特點。它是我們民族個性、民族審美習慣的“活”的顯現。
少數民族為了生產生活而創造的勞動工具與生活用品,是在其獨有的生存環境中形成的,與其傳統文化相輔相成的關于萬物形成的認識以及行之有效的生產生活方面的實用技藝,不僅歷史悠久,品味獨特,而且體現出民間工匠的設計智慧,值得我們珍惜和學習。
1 何為鶺宇鳥圖案
在苗族的傳統圖案中,有一個圖案是不可不談的,那就是鶺宇鳥圖案。放大來說,圖案相當于是古人留給我們的可視化語言。無論身處于任何一個時空,藝術的語言都將寫照這個時代的心態和情感。在這里,它們有著各自更為深層的歷史寓意和意識形態,并不只是簡單的一個圖騰或是紋飾而已。從反面來說,它們是先民以動物為圖騰符號來傳達一個情感炙熱的浪漫世界。
苗族同胞們在艱苦卓絕的遷徙生活和抵抗外來侵略者的頑強斗爭中,形成了拼搏奮進、砥礪前行的民族精神。為了緬懷祖先和感恩萬物,產生了眾多的節日,也有著眾多傳說。
鶺宇鳥圖案的傳說也曾被苗歌記錄流傳下來。在苗歌中記錄到:“妹榜妹留(蝴蝶媽媽)與水泡游方,懷十二個蛋并將其全部生出,牛幫筑窩,鹡宇鳥幫孵蛋歷經多年。期間想飛走被姜央叫回,孵出姜央(人)、雷公、龍王、象、牛、羊、雞、蛇、蜈蚣、山貓、虎、狗共十二兄弟。”將其完整解釋下來:“楓樹是生命宇宙樹,楓樹的根演化成布谷鳥和黃鸝,樹枝演化成鹡宇鳥,樹葉演化成燕子,樹心孕育出了蝴蝶媽媽,蝴蝶媽媽與溪流中的水泡談情成婚,生下十二個生命蛋,鹡宇鳥用三年時間孵這些生命蛋,終于孵出了人類祖先姜央和天上地下所有生命,楓樹、蝴蝶和鹡宇鳥就成了三位一體的生命始祖神,成了生命始祖的圖騰符號。”[1]
這是苗族祖先流傳下來的故事,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苗人最崇拜的便是楓樹、蝴蝶媽媽以及鶺宇鳥。
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鶺宇鳥的圖案一般出現在苗族染織、刺繡等手工藝品上。鶺宇鳥隸屬于鳥紋,而鳥紋布局是存在于各個角落的,并且出現的頻次非常多。
在其本身的圖案分析上,鶺宇鳥呈現出一種振翅高飛的鳥的形狀,翅膀強勁有力,并且充滿力量感,顯得十分威武。一般而言,鶺宇鳥紋樣表現的是側面,所以只描繪一只眼睛,但十分銳利。其尾端則是有著多根長長的羽毛,類似于孔雀般的長尾羽毛。兩足呈現出鷹一般的尖腳,一般是半著地的樣子,像是正要起飛或者著地。
鶺宇鳥圖案并不像某一單獨的實體鳥的樣子,更加是像各種鳥類的綜合體。鶺宇鳥是苗族傳說中的動物,現今比較難去討論其真正的動物實體,但是在這一圖案的流傳中,其形象是苗族先人經過優化組合以及想象融合在其中,是神化的超自然形象。
鶺宇鳥外形給人一種“質樸,粗拙”的感受,但是其中卻具有十分深刻的內涵之美。它是苗族紋飾的冰山一角,但卻也可以以小見大。它包含了我們對于自然之物和社會各個層面的認知和感悟。在歲月的積淀中,包含了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一種向往和期盼。
在其構圖及色彩上,一般而言,鶺宇鳥周邊通常有其他小紋飾的搭配。紋樣的構圖形式以及審美法則決定了這一圖案會有基本的程式化特征,如上下左右對稱又或者是成散落狀,具體如何構成就得從其所在的繡片或者手工品中具體分析了。總體來看,其以鶺宇鳥為中心,周邊飾以花鳥魚蟲以及一些幾何紋,花樣較多,顯得十分靈動活潑。在色彩上,鶺宇鳥也將分為兩種情況:一則是出現于藍染中,都是不同層次的藍色;如若出現于刺繡和織錦中,則色彩呈現出多樣化。一般而言,他們多采用紅色、黑色、藍色等色彩,整體顏色顯得高級而具有美感。不同的顏色也會代表不同的感覺,如紅色是喜慶、富貴的象征,黑色則更為沉著與深邃。
“渾然天成,弄拙成巧”是對鶺宇鳥的最佳評價。在這里,是個紛繁多樣的世界,有神有人,有奇珍亦有異獸。鶺宇鳥或許是其中的一種表達形式語言,但是他們所抒發的古人的那種天人合一、旺盛生命力的情感是無比強烈和濃郁的。
2 鶺宇鳥圖案的跨界創新運用
傳統圖案、傳統手工藝等如何活態傳承一直都是當今設計的關注焦點及難點。如何真正地將所謂的“老氣”“過時”“土氣”的傳統圖案及手工藝活化,以一種嶄新的姿態來面對新時代,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鶺宇鳥圖案的提取,是先從節日中感受苗族先民艱苦奮斗、堅韌不拔、崇拜自然、信仰萬物的精神,再從中提取視覺元素。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再次被這種敢于嘗試、勇于探索的精神所鼓舞,從而加深我們對中國精神的內化。
2.1 鶺宇鳥圖案在家居軟裝設計中的創新
鶺宇鳥圖案之前基本是存在于黔東南少數民族的傳統服飾中,但在當下面對這一傳統紋樣的活化,是可以將其范圍擴大化的。于是,在當地或其他手工藝者將這一圖案與染織工藝結合,運用到了家具軟裝這一新領域中,創造出獨特的苗族少數民族風味的裝飾風格。
鶺宇鳥創新運用案例是石方迷在第二屆全國蠟染藝術大賽中的獲獎作品,在其設計說明中寫到:“作品的靈感來源于丹寨苗族的圖騰——鶺宇鳥。丹寨苗族被譽為中國鳥圖騰的最后部落,原系中國鳥圖騰文化一個支脈。在悠長綿延的歲月中,鳥圖騰作為一種原始的宗教信仰已深深烙印在了丹寨苗族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崇拜著鶺宇鳥,將它畫在自己本民族的服飾上,色調素雅,風格獨特,顯得樸實大方,以清新悅目的蠟染來表現。以苗族的鶺宇鳥元素的非遺蠟染文化來繪圖,呈現出以藍為底、白為圖案的民族特色。”
從這里得以看出,鶺宇鳥圖案圖案突破了傳統的應用印象,運用到了現代家居中,如床上用品、窗簾、枕套、桌布等等。當代人們逐步從對物質方面的追求轉向了對于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追求。設計師又開始發現民族地區傳統手藝的美學文化和工藝文化,并且希望通過它來影響自己的日常生活,使得生存氛圍更加美好。
2.2 鶺宇鳥圖案在標志設計中的創新
楊再美與單琪設計師合作鞋子服飾品牌的logo 設計。logo 采用鹡宇鳥的造型,簡化外型,鳥身保留刺繡幾何紋樣,色彩沿用刺繡的紅、綠、藍等原色。
國家級苗族刺繡傳承人楊再美于2016 年參加上海大學織繡研修班后,與一家中國原創鞋履品牌合作,將鹡宇鳥刺繡紋樣運用于裝飾高檔定制靴。黔東南的刺繡手藝由此走向世界,面對歐洲客戶起價便達3000 元人民幣。楊再美因此帶動一批繡娘,讓苗族刺繡亮相國際舞臺,在收獲經濟效益的同時,也使這門傳統手藝獲得向前發展的內驅力。
鹡宇鳥圖案也經過了設計,使其更為簡約和符合現代人的審美,讓它可以更好地運用到更多的方面。傳統的圖案開始兩條道路并行,一條則是完全本真地保留下來,另一條則是在保留本身圖案的特色上,將其簡化、變形以及發展。
李立新先生于2014 年5 月在《裝飾》雜志中發表《一種被忽視的工藝史資源轉換方式——非延續性工藝的再生產研究》,文章中提出一種再生產方式,即沒有受到研究者關注的傳統工藝非延續性,其在傳統工藝急速消亡的同時,有一些新工藝物種正在悄然誕生。這些新工藝類型并非傳統工藝的延續傳承,而是通過移植、升華的方式被產生出來。這本質上便揭示了一部分現代手工藝的再生產模式。[2]將富有鹡宇鳥圖案的傳統文化保留下來,再將其美化,既有自己民族鮮明的藝術特色,又在發展中具備現代的審美。
2.3 鶺宇鳥圖案在服裝與服飾設計中的創新
如同鶺宇鳥圖案運用于家居軟裝設計中一樣,其可同時運用于服裝與服飾中,并加以創新,改變其固有印象,拓寬其領域。鶺宇鳥圖案在服飾中的運用非常廣闊,小到衣服扣上的圖案,大到禮服圖案的設計。這一傳統圖案不再是印象中只有少數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才可以穿戴的圖案,它開始經過設計后,成為了當今社會大家都可以搭配的裝飾。
2020年9月,貴州首屆藍染文化交流活動已經成功舉辦。在這里,可以看到各種的藍染作品,除卻其他的肌理紋飾之外,鶺宇鳥圖案的創新運用也成為了一大亮點。傳統圖案可以通過再設計、再創新、再融合,去探討其在服裝與服飾設計上的創新。
在創新中,最大的意義其實是擴大其運用領域,并且打破刻板印象。例如說,鶺宇鳥圖案在圍巾中的運用,一般很難想象一只神鳥作為圍巾的裝飾圖案,又或者是很難想象這種圖案是否適合都市人群。可當將圖案進行發展與改良之后,再加以傳統手工藝的加成,使得經過藍染工藝的鶺宇鳥圖案圍巾更具有一種民族特色以及飄逸感,成為了人人都可以穿戴的裝飾品。更可以將其運用于文化創意產業中,打造更加不一樣的鶺宇鳥圖案。
3 結語
從以上案例中,我們體會到苗族傳統元素源遠流長,綿延不斷。傳承圖案,繼承文化,匠人和設計師們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給“過去”一個“未來”。有這樣一句話形容黔東南:“中國聚寶盆,大美黔東南”,如果將這個“寶”聚焦在傳統工藝文化這個點上,那么我們可以借鑒的資源非常多,比如:蠟染、刺繡、銀飾、織錦、苗侗建筑等等。
立足黔東南本土,挖掘出更多的民族元素來做設計,使我們的文化大放光彩,讓傳統的元素不再是山野中的一朵小花,它可以是走向世界的民族之花,走向更加華美的舞臺,堅定“四個自信”,堅定文化自信,提升中國力量!
民族民間的傳統手藝雖保留著本色之味,卻也在社會的變化中存在著發展的困境。當然傳統手工藝遭遇的困境也是當代設計的機遇,而這些民族民間傳統藝術在被日益關注的大環境下,如何做到還原本身滋味的同時,又能得到更好的發展,這是值得深思、探討的問題。
傳統手工藝不斷融合發展,其境遇大致可以分為兩種:“第一,部分消亡,部分成為陳列藝術品。第二,現代化語境下手工藝品現代性的缺失。”傳統手工藝及其圖案是傳統文化的反映,我們可以通過設計使機器生產的“理性”現代感與手工的“感性”傳統感相融合,又或者是基于新的生產方式通過設計使手工藝產品回歸大眾生活,將新型材料與工藝融入傳統手工藝中,再通過包容的心吸收世界的文化創意。[3]
少數民族地區傳統圖案及其工藝的生存環境可基于:第一,當代生活下人們對手工藝關注度的持續提高。第二,民族傳統手工藝的自我喚醒與新生。第三,機械化影響下的鄉土生活衰退。這三點在民族地區當代傳統手工藝的生存環境特點里相互依存,并以此作為今后更為直接、清晰明了地對手工藝文化進行深層探索的基礎。
綜上所述,文章僅僅只是列舉了黔東南豐富的民族藝術文化中的一個較具代表性的案例,為民族藝術文化的研究選擇一個新的視角,希望所作的分析和闡釋,能對后續的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