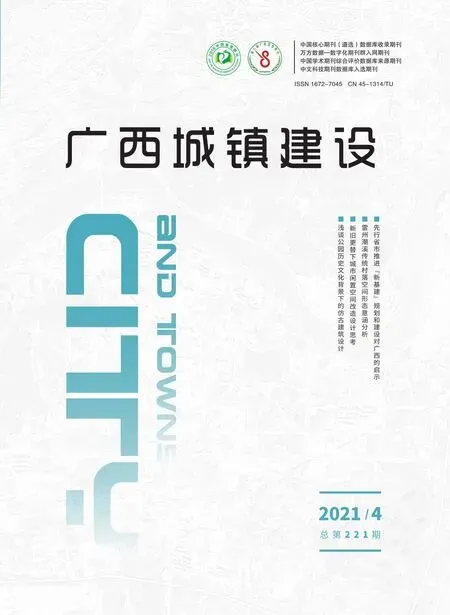完善合流制的改造探討
□ 郭銳敏
1 國內排水體制的發展歷程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排水體制經歷了三次主要變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受城市規模及居民生活習慣的影響,排水采用直排式合流制。城市區域的雨水、污水混合納入同一個根排水管道,就近直接排放進入自然水體。簡潔的管道系統有效解決了城市積水的問題,但是直排污水未經處理,對自然水體造成了嚴重的污染。
1980—1990年間,為解決直排污染問題,多個城市對排水管道系統進行截污改造。旱流污水通過截流干管全部引至污水處理廠,解決晴天污水排放問題。但雨天時,由于污水處理廠能力有限,大量摻混了污水的雨水只能從截流井溢流到水體中,造成了污染。同時,由于溢流井連通了水系和城市排水管道,水系高水位條件下存在倒灌風險。
1987年,《室外排水設計規范》(GBJ 14—87)的發布,正式提出城市新建城區宜采用分流制排水體制,分流制開始成為發展的主流。雨污水采用兩套獨立的排水系統,污水無論晴雨天,均可完整收入污水處理廠,解決了污水溢流污染水體的問題。
2 分流制改造的難題
許多城市的排水規劃都提出要將原有的合流制系統逐步改造成分流制。但各城市在改造過程中,均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難題。
技術條件方面:老城區地下空間有限,各種已建管線缺乏規劃,重力流管道的改造難度特別大;改造工作難以推進,管網只進行了部分改造,或因各種原因中途停止,這些不完整的分流改造,又引發了新的污染問題;分流后的雨水管網,存在初雨污染問題;管網體系存在錯接、混接的風險。
改造費用方面:2套管網造價高;部分城市傳統建筑和歷史遺產較多,改造的代價巨大;為了控制初雨污染,需要配置大容積的初雨調蓄池,增加土建投資;改造后的污染物削減效果與工程投資需要統籌衡量。
維護管理方面:為防止后續出現違規混接和排放,需要投入了更多人力進行監管,否則會產生兩套混流系統。
昆明、武漢、廣州、北京等城市已經進行了多年的分流制改造,投入巨大的費用,并進行了悉心的設計布置和社會工作,但至今仍然無法全面實施推進[1]。水污染治理的壓力和雨污分流的過程艱難,有目共睹。
3 發達國家的合流制進展
國外發達國家也經歷了“合改分”的時期,比我國更早遇到推進瓶頸,也更早地思考污水溢流(Combined Sewer Overflow,CSO)污染控制的方案。
3.1 美國
美國現存合流制排水系統的城市分布在32個州,主要位于美國東北部的5大湖區,以及西部發展較早的部分地區,這些城市大部分沒有選擇進行大范圍的合改分工程,而是轉向對合流制溢流污染進行有效控制[2]。
美國的城市污水處理廠大部分建設在遠離城市的郊區,充足的場地可以配置大規模的處理能力,并且國家政策給予考核特例,允許在暴雨情況下,混合污水只經過一級處理加消毒就能排放,因此可以普遍采用截流倍數高達4的“大截流系統”,提高污水收集量。
3.2 德國
德國現有的合流制排水系統多分布于南部城市。據2016年的統計數據,德國合流制管網長度占全境管網總長的53.5%[3]。
德國1970年開始大量建設雨水調蓄設施,2016年各類雨水調蓄設施達到54069個,調蓄容積共計6079×104m3,人均0.738 m3[2]。
合流制區域的污水排放需要事先獲得政府的排放許可;在系統設計及運營中,借助自動設備及精確監測儀表,嚴格控制干管的最大流量不超出污水處理廠的處理能力,同時對源頭雨水進行分散控制,減少系統的雨水量。德國主要通過調蓄來應對CSO溢流污染。
3.3 日本
1980年開始,日本國土交通省著力推進合流制溢流控制,強調完善管網系統,提高截流能力。1999年,日本有合流制排水系統的城市共195座,其中11座城市的人口超過100萬[2]。
日本制定了明確的合流制改善目標,如各排放口全年外排的污染物平均濃度不超過40mg /L,控制溢流次數等。由于易受臺風影響,加之城市建筑密度高,部分城市建造了調蓄隧道或者大管徑的截流干管,統籌考慮防澇與溢流控制。
考慮到合流制改善工作建設周期長,影響城市環境交通以及居民的生活,日本很多城市的改善策略,傾向于對溢流排口的排水進行就地處理,從而衍生了許多創新凈化技術。
3.4 國外經驗小結
各國的總體思路都是削減外排污染負荷,但各國的國情、基礎設施及管理水平不盡相同,在策略上各自有所側重。美國采用大截流系統,盡可能地收納處理雨污水,是基于污水廠的地理優勢及充裕的城市空間;德國重視調蓄以及精確的截流控制,源于嚴謹的系統觀念以及成熟先進的設備制造工藝;日本側重于深邃及就地處理,更多是因為極端天氣易發、人口密度高、城市空間緊張以及民眾對社會和環境質量的高要求。
但應注意的是,無論美德日哪一國,均有專門的政策規章及專屬的負責機構支持推進合流制建造。
4 國內推進合流制的難點
對比美德日3種典型,中國的情況與日本更相似,但卻無法直接搬用方案,因為國內推進合流制有自己特有的難點。
4.1 合流管網形式多樣,系統復雜
由于建設指導思想的更迭、城市高速發展引起的空間條件急劇變化、建設管理水平滯后以及臨時治理措施缺乏統一指導等因素,導致國內現存4種類型的合流制排水系統。
合流制排水系統。該系統又可細分為完善及不完整兩種。完善合流制是指系統包括了源頭低影響開發技術,管網截流量匹配污水處理廠能力,調蓄設施及就地處理設施,是合流制改善的目標形式;不完整合流制是指缺失了一項或多項的上述內容,常會出現污水廠前溢流、污水負荷量低、貯存污水無法處理的情況,這是國內大量合流制管網的普遍現狀。
存在較多錯混接的分流系統。分流建設中,由于施工及監管的不規范,造成多處雨污水混接,形成2套混流管網。最終造成污水管網的收納水量大,雨水網管的排放污染嚴重。
分流制改造過程中的過渡系統。該系統按分流制設計及施工,但由于空間、經費及推進受阻等問題,系統未建設完全且有可能將長期處于這樣的中間狀態。也有存在由于資金或者改造難度大等問題,優先對道路進行分流改造,而小區地塊內仍保留合流制的情況,此時雨水管道只能收集市政道路上的雨水。
山水及雨污混合的排水系統。結合行洪、排澇管涵渠道設置的,混合多種水流的排水系統,多見于沿海及山地地區。旱天污水濃度低,雨天溢流量大。
上述多種類型合流制共存的復雜情況,使得國內制定政策和進行改造的難度加大,改造推進難以進行,排水系統溢流的頻次更高,形成嚴重的污染危害。
4.2 各地改造條件差異大
不同規模的城市,其改造目標和難點完全不同。大城市發展較早,排水體制的指導方向更迭頻繁,存在多種管網形式。合流制管網處在核心老城區,已建的地下管線復雜,改造空間十分有限,改造工作對民眾的生活影響較大。小城市市政基礎不完善,管理維護水平較差,資金也難以維持長時間的改造工程。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點。地上傳統建筑群、地下古跡、文化遺跡等直接影響改造技術,需要巨額的維護成本;自然地理特征造成的高地下水位,需要考慮外水入滲、倒灌;南方城市需要考慮結合防洪排澇;山區城市地質不良區域的改造成本高昂。
4.3 缺少指導性政策和法規
相比國外,國內合流制系統的支撐性政策法規缺口較大。管控內容的空白,使得執法和監管缺乏依據;指導思想不統一,方向不堅定,容易受到社會阻力、技術條件的影響,系統的建設在合流制與分流制之間反復變換[4],形成了不徹底的分流系統。
缺少國家標準和技術規范的支撐。國內目前還沒有針對溢流次數的設計標準及方法[5];對于截流倍數,規范取值2~5,范圍寬泛缺乏針對性,設計完全憑借經驗,也經常伴隨矛盾。
對于下游需新建污水廠的情況,若倍數取值大,則管網和污水廠規模大,投資高,污水被稀釋,造成入廠濃度低,難以響應國家污水處理廠提質增效的要求;而取值小,又缺乏指標判斷是否能滿足溢流污染的控制要求。
對于下游已有污水廠的情況,倍數只能根據污水廠的冗余能力選擇,取值過大則出現廠前溢流;如果冗余足夠,系數取高值,雨天又存在污染物濃度低、水量大的問題,對生物處理設施不利。
4.4 建設管理維護能力不足
管網狀態混亂,管理難度大。國內現有的合流系統類型本就復雜,再加上建設管理不當、違法成本低等因素,建成管網中錯接、混接、亂接的現象較多,加劇了混亂狀態。
維護人員的素質水平較低、經費不足等原因制約著整體管網的運行效率。淤積、破損、滲漏等問題,使得截流管道能力下降,出現旱季沉積物增多、雨季溢流嚴重、污染地下水等問題。
個別地區應付心態重,改造策略不當,加劇污染影響。為了應對考核,改造缺少統籌考慮,采用封堵溢流口等方式粗暴解決,削弱了排水能力,增加內澇風險。
缺乏系統的整體意識。為了單一的防洪或者景觀水景需求,通過設置閘壩等方式,隨意改造水系水位和河道運行狀態,使得部分管網及排口長期淹沒在常水位之下,加劇管網運行壓力。
5 完善合流制的改造思路
針對國內存在的推進難點,結合國外的改造經驗,我國的合流制污染控制措施應該貫徹削減外排污染負荷的原則,但又應該秉持自己的改造特點。
根據排水的過程,以管網為主體,減少水量的思路為:減少進入管網的雨水量;增加進入污水廠的混合水量;將本應溢流的混合水量暫時貯存待后續處理。具體而言,控制措施為源頭減排、管網優化維護、調蓄處理、完善規章標準。
5.1 源頭減排
源頭減排的目的是減少進入排水管網的雨水。結合海綿城市措施,將雨水就地留存、下滲,實現錯峰排放,同時利用植物和土壤截留過濾雨水中的污染物。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且措施多樣,包括綠色屋面、透水鋪裝、下沉綠地、生物滯留帶及雨水花園等,結合景觀利用建筑群之間的零碎空間,完成雨水控制。
5.2 管網優化維護
截流倍數是核心參數,需要統籌考慮現有污水廠的規模情況、城市下墊面的情況、工程資金量、建設管理水平,而現有規范對其卻缺乏有針對性的指導。結合現有的計算機模擬技術,將工程數字模型化,根據治理目標,反推出不同截流倍數下的設施配置,組成多個方案比較,可以直觀有效地進行決策,避免了依靠經驗、邊做邊改的方式。
重視管道的清洗及疏通,積極宣貫并提高周邊居民的正確排水意識,將管網排水能力維持在良好的狀態中。破損管道的修復及錯混接整改,是無法避免并需長期堅持的工作,需要主管部門重視并給予政策支持。
5.3 調蓄處理
在管路中設置調蓄水池,能夠有效增加污水截留倍數,控制初期污染濃度較大的污水,將其錯峰排放至污水處理廠。通過監測儀表對截流井內實時水位和水質的精確計量,配合自動化閘門及堰板,可以隨時調整截流倍數,有效防止外水倒灌。調蓄水池的布置位置靈活,可以分散布置在零星空地中,也可以集中布置,布置在管網上游還可以有效減小下游截流干管的管徑。
在溢流端建造人工濕地除了可以調蓄溢流水量外,還能利用植物去除水中的污染物,污水停留時間越長去除效果越好[6]。人工濕地同時能起到美化城市、改善生態的作用,由于需要較大的占地,宜結合景觀布置。
在溢流端安裝就地處理設備可以有效削減外排污染負荷。已有學者研究旋流分離器在末端處理中的應用[7];也可以結合雨水調蓄池,增設斜板沉淀隔間,對溢流水量進行就地處理。
5.4 完善法規、標準及管理
與國外相比,法規標準是國內推行完善合流制的最大欠缺。溢流污染CSO控制需要法律法規提供支撐依據,以保證工作順利實施。規劃的編制要具有針對性,根據各城市的特性及發展趨勢進行補充或者修編。各部門之間需要加強溝通協調,保證政策的一致性,避免目標反復。
設計標準急需完善和細化,單依靠經驗選擇參數及工藝,無法保證設計的可控性。要加強排水監督管理,重視管網運行維護,大力整改錯混接,提高居民的正確排水意識,保障管網處在良好的運行狀態。
6 結語
吸取污染治理的經驗教訓,國內已不再一票否決合流制。國外的成功治理案例也給予了合流制新的活力。在日漸成熟的自動化設備及精確監測儀表的幫助下,曾經的合流制缺點正在逐個被解決。
合流制和分流制不應有優劣之分,兩者更應作為互補方案,根據當地區域特性來搭配選擇。在完善合流制的道路上,我國還有必須要克服的一系列難題,這是一條漫長但可行的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