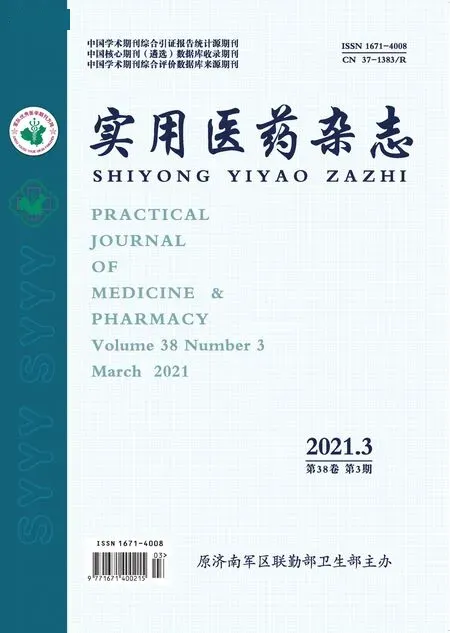火神山醫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心臟損害的超聲影像學研究*
李 珂,李順飛,何偉華,張明德,姚穎龍,張振華,朱賢勝,郭 棟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傳播迅速,感染率高,具有致死性等特點,已引起廣泛關注[1-3]。據報道,在一項對90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患者的調查研究中,有50%的患者伴有慢性疾病,而其中80%為心血管疾病[4]。此外有研究顯示,COVID-19 感染患者中,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比例高達17%,表明COVID-19 患者易發生心臟損傷[5]。根據國家衛健委第六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6],COVID-19 的臨床分型: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其中,重型、危重型COVID-19 具有臨床治愈緩慢,病死率高的特點,而輕型、普通型COVID-19 的臨床治愈率高,病死率低。僅有少數輕型、普通型患者可轉發為重型或危重型。該研究應用特診彩超,對比分析COVID-19 輕型、普通型肺炎與重型、危重型肺炎患者的心臟損傷范圍及損傷程度。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20 年2 月—3 月火神山醫院收治的COVID-19 感染患者62例。納入研究的診斷標準:(1)RT-PCR 檢測新型冠狀病毒核酸陽性;(2)肺部CT 提示雙肺呈急性滲出性(片狀或云霧狀)毛玻璃樣改變;(3)臨床有發熱、干咳等癥狀;(4)有武漢旅居史或接觸史等。根據臨床分型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研究組為已確診重型、危重型COVID-19 患者共37例,其中男25例,女12例,年齡34~87 歲,平均59.4 歲。對照組為輕型、普通型COVID-19 患者共25例,其中男9例,女16例,年齡28~69 歲,平均51.9 歲。
1.2 方法運用Philips EPIQ 5 彩超儀及GE LOGIQ V2 便攜式彩超儀。掃查入組患者的心臟結構、室壁運動、左心功能(EF 值)、瓣膜反流、肺動脈壓、心包積液等情況來獲得數據。
1.2.1 心臟結構測量 分別測量2組患者左心房(LA)、右心房(RA)、右心室(RV)、左心室(LV)的橫徑。左心房LA>40 mm 為增大、右心房RA>40 mm 為增大、右心室RV>30 mm 為增大、左心室LV>50 mm為增大[7]。該組試驗數據中,心房心室橫徑增大記為陽性(+),每增大10 mm 增加一個(+),心房心室橫徑在正常值范圍記為陰性(-)。例如:左心室橫徑<50 mm 記為(-),左心室橫徑51~60 mm 記為(+),左心室橫徑61~70 mm 記為(++),左心室橫徑>70 mm記為(+++)。
1.2.2 室壁運動分析 以左心室長軸為標準切面,該組試驗數據中,不嚴格區分瓣口、腱索、乳頭肌、心尖水平,嚴格區分前間隔及左心室前壁、后間隔及左心室后壁,運動波幅無異常(-),運動波幅減低4~5 mm(+)、運動波幅減低3~4 mm(++)、運動波幅減低<3 mm(+++)。
1.2.3 左心功能測量 運用Simpson 法測量左心功能EF 值。該組試驗數據中,EF>50%(-)、EF:41%~50%(+)、EF:31%~40%(++)、EF<30%(+++)。
1.2.4 瓣膜反流測量 根據第二版超聲診斷學心臟瓣膜反流測量法,測量二尖瓣 (MR)、三尖瓣(TR)、主動脈瓣(AR)、肺動脈瓣(PR)的反流。該組試驗數據中,無反流記為(-)、少量反流記為(+)、中量反流記為(++)、大量反流記為(+++)。
1.2.5 肺動脈壓測量 運用簡化伯努利方程計算肺動脈壓(排除先天性心臟病),肺動脈壓=三尖瓣口反流壓差+右心房壓[7],正常肺動脈壓范圍為15~30 mmHg,>30 mmHg 診斷為肺動脈高壓。該組試驗數據中,無肺動脈高壓記為(-)、輕度肺動脈高壓30~50 mmHg 記為(+)、中度肺動脈高壓51~70 mmHg記為(++)、重度肺動脈高壓>70 mmHg 記為(+++)。
1.2.6 心包積液 根據第二版超聲診斷學測量心包積液,該組試驗數據中,無心包積液記為(-)、少量心包積液記為(+)、中量心包積液記為(++)、大量心包積液記為(+++)。
1.3 統計學分析所有資料信息均采用Excel 軟件建立數據庫,進行數據整理。運用SPSS 23.0 統計軟件,對整理后數據進行χ2檢驗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心臟結構變化對比發現,研究組出現心臟結構異常者有13例(35.1%),而對照組心臟結構異常者有5例(20.0%),少于重癥組(含危重型),經統計學分析,2組在出現心臟結構變化的異常率上無明顯統計學意義(P>0.05)。但分析2組患者在心臟結構變化累及2 個房室的例數上,研究組有5例,對照組僅有1例,提示研究組心臟結構變化更為明顯。
2.2 室壁運動分析研究組出現室壁運動異常者有7例(18.9%),而對照組室壁運動異常者僅有1例(4.0%),輕型組(含普通型)在數量上少于重癥組(含危重型),經統計學分析,2組在出現室壁運動異常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比較2組室壁運動異常發生部位,僅前間隔及左心室前壁出現異常者有6例,僅后間隔及左心室后壁出現異常者有0例,二者同時出現異常者2例,顯示COVID-19 患者更易出現前間隔及左心室前壁運動異常。
2.3 左心功能測量通過比較,研究組左心功能EF 值出現異常者有5例(13.5%),而對照組左心功能EF 值異常者有1例(4.0%),輕型組(含普通型)在數量上少于重癥組(含危重型),經統計學分析,2組在左心功能EF 值異常上差異無明顯統計學意義(P>0.05)。
2.4 心包積液研究組出現心包積液者有16例(43.2%),對照組出現心包積液者有8例(32.0%),輕型組(含普通型)在數量上少于重癥組(含危重型),經統計學分析,2組在出現心包積液者數量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進一步比較發現,研究組出現2例中量心包積液(++),而對照組均為少量心包積液(+),提示重癥組(含危重型)出現心包積液的量較多。
2.5 瓣膜反流測量研究組出現心包積液者有15例(40.5%),對照組出現心包積液者有4例(16.0%),輕型組(含普通型)在數量上少于重癥組(含危重型),經統計學分析,2組在出現心包積液者數量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進一步對比發現,研究組有3例中量反流(++),而對照組均為少量反流(+);在該研究所有COVID-19 患者中,單獨出現三尖瓣(TR)和二尖瓣(MR)反流者均為7例,二者同時出現者有4例。且三尖瓣反流(TR)與肺動脈壓增高相關。
2.6 肺動脈壓測量研究組出現肺動脈高壓者有4例 (10.8%),對照組出現肺動脈高壓者有2例(8.0%),輕型組(含普通型)在數量上少于重癥組(含危重型),經統計學分析,2組在出現肺動脈高壓者數量上差異無明顯統計學意義(P>0.05)。此外,研究組出現2例中度肺動脈高壓(++),而對照組均為輕度肺動脈高壓(+),間接表明重癥COVID-19 患者更易發展為嚴重的肺動脈高壓(表1~3)。
3 討論
COVID-19 疫情的暴發嚴重威脅人類的健康。SARS-CoV-2 具有高傳染性特征,全人群普遍易感,總病死率較SARS 低,但重癥COVID-19 患者常因機體多個器官、系統受損。國內外多項流行病學研究提示,COVID-19 患者中常合并基礎疾病,其中以高血壓、冠心病多見,此外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中病情較重,死亡風險上升,提示新型冠狀病毒更易感染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8],但不同臨床分型的COVID-19 患者心臟損傷并發癥的區別方面少有評估研究。筆者結合臨床實踐,對已確診住院的重型、危重型COVID-19 患者的并發癥,尤其是心臟損傷并發癥給予評估。彩超結果顯示,重型(含危重型)患者均出現不同程度心臟結構、室壁運動、左心功能異常,心包積液、瓣膜反流、肺動脈壓增高(不排除患者獲得新冠病毒肺炎之前,心臟已存在的相關損傷)。通過統計分析,僅有心包積液、瓣膜反流異常者出現例數與輕型(含普通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瓣膜反流中,以肺動脈壓增高引起的三尖瓣(TR)反流更有臨床意義。從心臟損傷嚴重程度上,輕型(含普通型)患者心臟受損均不明顯。另外,影響重型組患者愈后的其他因素還包括年齡、慢性疾病、腫瘤等。需要提及的是,在心臟評估過程中對每名患者的胸腔積液情況進行了摸查,結果發現COVID-19 不以胸腔積液為主要表現形式,僅少數患者表現為少量胸腔積液,這是區別其他肺炎的一個特點。目前認為COVID-19 感染相關心臟損害明顯影響COVID-19 嚴重程度,臨床上對罹患心血管基礎疾病者要高度重視,密切監測和治療[9,10]。

表1 37例COVID-19 重癥、危重癥組心臟損傷情況

表2 25例COVID-19 輕型、普通型組心臟損傷情況

表3 COVID-19 重型組、輕型組心臟測量值的統計學分析
總體來說,鑒于該研究受樣本例數和試驗條件及研究者水平的限制,研究結果可能有失偏頗,下一步還需進一步加大樣本,采取更加科學的研究設計,提高研究結果的準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