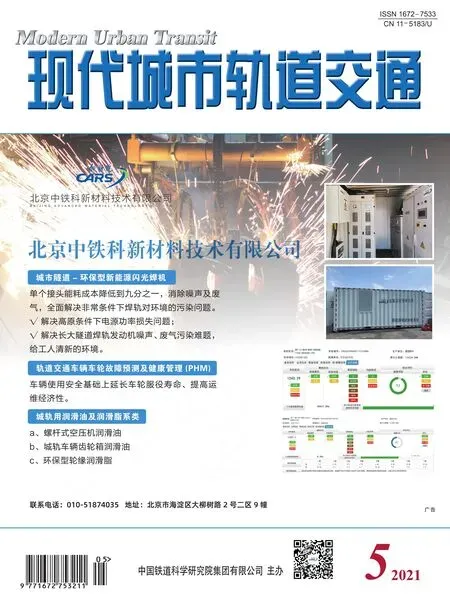后疫情時代國際鐵路工程承包合同中不可抗力條款使用研究
湯學文,趙 鑫
(鐵科院(北京)工程咨詢有限公司,北京 100081)
隨著“走出去”戰略的推進,我國的海外工程承包業務持續增長,對外投資合作機制不斷深化,掀起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與能源資源建設的新高潮。在“交通強國、鐵路先行”的戰略部署下,我國鐵路相關企業正在加速走出去的步伐。然而,由于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簡稱“新冠疫情”)的襲擾,我國企業參與的許多國際鐵路工程項目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工程延期、停滯等影響。隨著新冠疫苗的投入使用,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國際疫情發展的整體態勢也由突發期的高位增長向常態防控轉變,全球已進入疫情常態防控時代(以下簡稱“后疫情時代”)。可預見的是,在未來一定時期內,全球疫情形勢依然嚴峻。疫情的肆虐使我國的國際鐵路工程承包企業蒙受了工程合同履行停滯、工程停產延期的重大損失。如何在合同締約時運用合同中對于以新冠疫情為代表的突發性不可抗力事件的規定維護自身權益,是這些企業在后疫情時代必須考慮的問題。
1 后疫情時代背景
自2020年1月起,新冠疫情愈演愈烈,迅速席卷全球。2020年1月3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將新冠疫情定性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2月28日,將疫情全球風險級別由“高級別”調至“非常高級別”;3月11日,宣布新冠病毒進入全球大流行狀態。截至2020年11月19日,全球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56 499 901例,累計死亡病例1 353 368例,116個國家和地區確診病例超過萬例。據國際金融協會(IIF)報告顯示,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2020年全球債務規模將歷史性地堆積至277萬億美元,債務總額與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將達到365%。
可以預見的是,在2021年,防疫將與經濟發展一起成為全球發展的主題,全球將進入后疫情時代,疫情防控常態化也將成為未來世界發展的一個鮮明特征。
2 疫情下的國際鐵路工程承包項目現狀
開展國際鐵路工程承包項目實質上是一種跨國經營行為。由于承包國際鐵路建設工程及相關成套設備的出口均涉及我國對外關系,受復雜的政治和經濟因素影響,而且相關技術和商務談判有著自身體系及嚴格要求,加之鐵路行業具有與生俱來的行業準入壁壘和較低的平均利潤率,因此我國鐵路企業在開展國際鐵路工程承包項目時需將風險因素放大考慮。
在“一帶一路”戰略下,國際鐵路工程業務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在后疫情時代這一特殊時期,承包國際鐵路工程項目的壓力將更為突出,具體體現如下。
(1)受疫情影響,國際鐵路工程項目的資金流轉會受阻,原因在于疫情帶來的履約周期延長必然導致固定成本攀升與收款期延遲。
(2)部分企業的境外項目由于貸款不能及時還本付息,其信用風險也將提升。
(3)疫情會對海外項目人員管理,人員的簽證辦理、進出境,以及貨物采購等各方面產生影響。
(4)工程項目所在國可能會以政府命令的方式要求工程承包企業、分包商與供應商參加防疫項目建設,使其短期內無法履行合同,從而導致其花銷攀升及項目延期。
3 FIDIC 條款中不可抗力相關規定
國際咨詢工程師聯合會(FICID)編制的FIDIC條款(也稱為“FIDIC施工合同條件”)是當前國際工程承包合同的締約藍本和主流參照,有多種版本。本文選取目前國際工程總承包(EPC)項目廣泛采用的合同版本——《設計采購施工(EPC)/交鑰匙工程合同條件》2017版(以下簡稱“FICID銀皮書”)作為對象,深入研究其關于不可抗力條款的規定。
在合同中設定不可抗力條款的目的是,在發生不可預見、不可避免且不可歸責為合同方責任的事件時,賦予受不可抗力影響方主張免除合同項下責任的權利。從實操層面看,不可抗力條款已演繹為國際商務、建設等類型合同所必備的風險分配條約,即以約定的方式,將不可預測和不可避免的事件擬制為合同項下的免責情形,使之普遍適用,以避免承擔不可規避的責任。當前,不可抗力條款已被廣泛應用于各種國際工程承包合同文本中。
3.1 不可抗力的界定
3.1.1 概念及外延
FICID銀皮書第18.1款中,將例外事件(即不可抗力事件,以下均稱“不可抗力事件”)界定為同時滿足下述4個條件的事件或情形:①一方無法控制;② 該方在簽訂合同前,不能對其進行合理準備;③發生后,該方不能合理避免或克服;④不能主要歸因于他方。
其外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6條:
(1)戰爭、敵對行動、入侵等;
(2)叛亂、恐怖主義、革命、暴動、內戰等;
(3)人員騷動、混亂等;
(4)雇員罷工或停工;
(5)戰爭軍火、爆炸物質、電離輻射或放射性物質造成的污染等;
(6)自然災害,如地震、海嘯、火山活動、颶風或臺風等。
其中,前5項是“人禍”,第(6)項是“天災”。
3.1.2 新冠疫情的相關定性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在新冠疫情發生后,我國眾多司法機構都將其定性為不可抗力。根據FIDIC銀皮書第18.1款中判定不可抗力事件成立的4個條件,也可將新冠疫情定性為不可抗力事件。
從實操層面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貿促會”)建立的認證平臺已經有針對性地開放了《新冠疫情屬不可抗力證明書》的在線申請,目的是使國際工程承包企業可在當下及后疫情時代提出不可抗力免責要求。中國貿促會出具的《新型疫情屬不可抗力證明書》不僅在我國具備較高的權威性,而且得到了全球200余個國家政府、商會和企業的認可。
但這并不代表在所有國際鐵路工程承包合同中,新冠疫情都可以解釋為不可抗力。根據前文分析可知,在遵循FIDIC銀皮書訂立的合同中可將新冠疫情定性為不可抗力,但在部分未遵循或未完全遵循FIDIC銀皮書訂立的合同中,這一條卻不適用,而這也考驗著我國企業訂立國際工程承包合同的智慧和能力。
3.2 不可抗力情形下當事人的義務
在時效期限內行權,作為一項約定俗成的國際原則,被納入各種國際公法和條約中,FIDIC條款也不例外。
FIDIC銀皮書第18.2款(例外事件下的通知義務)明確指出不可抗力事件發生后受影響一方當事人維權的程序性要求,即受影響一方需于14天之內向另一方發出告知通知,并說明受不可抗力影響的情況,以保證項目他方當事人能夠迅速判斷和及時應對。這也是第18.4款(觸發索賠程序)的程序性要件。此外,FIDIC銀皮書第20.2款(費用/工期之索賠)第1段中對索賠通知存在28天的時效要求。因此,國際工程承包企業須在滿足第18.2款與20.2款中的2個通知時效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就不可抗力事件導致的各種后果主張有效索賠。
此外,承包企業應采取措施,盡量降低不可抗力事件的影響,如更改項目實施方案等,即履行不可抗力事件下的減損義務。
3.3 不可抗力下的合同終止
不可抗力條款設立的目標在于賦予受影響一方當事人自主選擇終止國際工程承包合同的權利。FIDIC銀皮書第18.5款第1段對國際工程業主和承包企業在不可抗力事件下終止合同的訴求做出了細致規定,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終止通知7天后生效的2種情形:
(1)國際工程項目因通知文件中涉及的突發事件受阻,時間連續且達到84天;
(2)國際工程項目因上述同一突發事件受阻,時間不連續但累計達到140天。
4 合同中不可抗力條款的應用
在后疫情時代國際鐵路工程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對于合同中不可抗力條款進行分析運用的核心點在于索賠,其涉及的可索賠性、索賠范圍與和合同終止后的清算均為核心要點,下面對上述要點展開針對性分析。
4.1 承包企業的可索賠性分析
探討國際鐵路工程承包企業是否可就不可抗力條款主張索賠,應結合FIDIC條款展開分析。根據FIDIC銀皮書第18.1款,如果發生第(6)項中的自然災害,承包企業不得提出相關費用索賠;如果涉及第(1)項中的戰爭、敵對行動、入侵等情況,無論其是否發生在工程所在國,承包企業均可提出費用索賠;若為第(2)~(5)項中的情況,則只有當其發生于工程所在國,承包企業才可主張費用索賠;對于其他未竟事項,承包企業均不能提起費用索賠訴訟,但可以索賠工期,申請延期履行合同。
由于國際鐵路工程承包企業不能在上述所有情況下主張費用索賠,因此針對新冠疫情,為維護自身利益,承包企業可以購買針對其專設的風險類保單,如國際工程完工延遲險、國際工程運營中斷險。如此,不僅可以規避國際工程承包合同中不可抗力條款部分情形適用模糊的問題,還能夠提高項目的可索賠性。
4.2 承包企業索賠范圍界定
后疫情時代,國際鐵路工程建設項目雖然仍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但大部分可以繼續履行。針對當下正在履行的項目,根據FIDIC銀皮書相關規定,我國承包企業可在履行通知和減損義務后,向業主提出索賠,索賠內容包括2個方面:①相應延長的工期;②額外發生的成本費用。
此時,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新冠疫情可判定為不可抗力,承包企業也只能索賠成本費用,而無權就利潤提出索賠。此外,承包企業的具體索賠范圍應根據承包合同中的相應規定來確定。例如,若承包合同中明確規定,在遭受不可抗力時,承包企業只能索賠工期,不能索賠費用,則承包企業無法向業主索賠成本費用。
4.3 合同終止清算時的費用償付范圍
盡管大部分國際鐵路工程項目可以履行,但依然存在合同終止的情況。此時,無論是承包企業還是業主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提出終止合同,都會導致項目清算。根據FIDIC銀皮書規定,當國際鐵路工程合同終止清算時,承包企業有權獲得下列費用償付:
(1)承包企業已完成工程所對應的應付而未付的工程款;
(2)設備和臨時工程撤場費;
(3)人員勞務撤場費;
(4)因實施工程而合理發生的其他費用或債務,如分包合同終止費等。
作為一般性規定,FIDIC銀皮書上的規定只能作為參考,承包企業在國際鐵路工程項目終止清算時所能得到的償付還需依據承包合同判定。許多項目業主都會在合同談判時要求將上述第(4)項排除在合同終止清算補償之外,尤其是分包合同終止費,甚至只保留第(1)和第(2)項,即剩余工程款和設備材料費。
4.4 海外特許經營鐵路項目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條款
海外特許經營鐵路項目與近年來較為流行的EPC合同相似,有專門性的不可抗力條款,內容也大都參照FIDIC銀皮書相關規定,即承包企業應在時限范圍內履行通知義務,必要時還可向下游承包企業尋求支持。海外特許經營鐵路項目合同通常將不可抗力細分為政治性不可抗力和其他不可抗力;而且還規定在政治性不可抗力情況下,投資方、承包企業還可獲得更為廣泛的救濟賠償。由于各國國情不同,海外特許經營鐵路項目合同所規定的救濟機制與相關投資協議的規定也不相同,因此還需要結合當地法律及相關投資協議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5 承包企業規避不可抗力風險的手段
后疫情時代,在締結國際鐵路工程承包合同時,我國企業應做好以下6點。
(1)注重對不可抗力條款的審核,確認該條款的存在及其對新冠疫情等不可抗力事件的適用性。
(2)一旦發生疫情等不可抗力事件,應確保在14日內發出告知通知,并在約定期限內發出索賠通知,具體時限應在締約時明確約定。
(3)對于已簽訂的履行中合同,應積極補簽不可抗力條款,如無法補簽,應及時購買國際工程完工延遲險、國際工程運營中斷險等保險,以分擔因疫情反復而導致的項目誤期風險。
(4)作為承包企業,應在締結承包合同時,明確不可抗力條款下的索賠內容(工期或費用),最好將二者都納入索賠范圍內。
(5)締結合同時,應明確在項目終止清算時的費用償付范圍及內容。
(6)針對海外特許經營鐵路項目,應參照相關規定,提前做好擘劃。
6 結語
在鐵路“走出去”的戰略背景下,我國企業主導的國際鐵路工程項目正加速開展。后疫情時代,我國企業應結合FIDIC條款,通過在合同中明確不可抗力條款,對疫情這一風險因素加以控制;此外,還應認識到,不可抗力條款對于疫情也并非絕對適用,因此需綜合考慮鐵路項目所在國相關法律、國際工程承包類保險及實操經驗,做好應對措施,以更好維護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