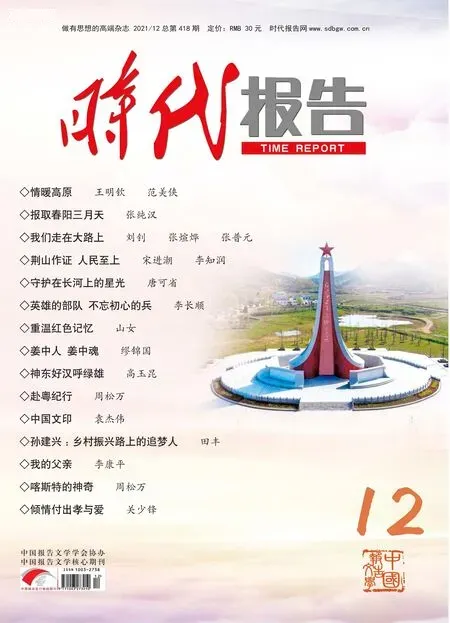海闊憑魚躍
何競


剛過而立之年的于海躍,長著北方男兒的標準身材:高大魁梧、腰板硬朗、肩寬腿長。國字臉的皮膚黝黑,鼻梁上架一副近視眼鏡,笑起來真誠而靦腆。
于海躍沿著碧巖閣旅游驛站的石頭階梯,箭步如飛地拾階而上時,階梯旁邊的小攤位后面,傳來了此起彼伏的聲音:“于書記,吃個雞蛋嘛,熱乎乎的。”“于書記,新花生要不要嘗嘗?”“于書記,自己拈個粽子吃喲。”
于海躍笑瞇瞇的,向左右兩邊的攤主拱手道謝,他們是一群特殊的小攤主,有個共同身份:潛經村建檔貧困戶。這是于海躍和驛站協調,免費安排給貧困戶的小攤位,能遮雨擋風,小商販集中在階梯兩側擺攤設點,也減少了之前一見導游帶游客前來,小商販便各自拎著竹籃,蜂擁而上的情況,不少游客對這樣的“激情推銷”直呼“無福消受”,拒之不及。
倒退10多年時間,于海躍壓根想不到,自己會從遙遠的大東北,來到華南桂林,并且在一個名叫潛經村的地方擔任第一書記,彈指間已是6年光陰如水流走。
初涉“戰場”
2011年秋,于海躍大學畢業后來到水利局工作。2015年10月,于海躍接受組織安排,赴潛經村擔任第一書記。
潛經行政村位于桂林市雁山區草坪回族鄉,距桂林市中心32公里,屬自治區“十三五”貧困村,下轄潛經、蘭口、明村等3個自然村。2015年年底,于海躍完成初步摸底,并完成精準識別入戶打分工作,經自治區劃定建檔立卡貧困戶分數線,得出數據結論:潛經總人口2051人,貧困人口452人,貧困發生率23.22%。
進行精準識別過程中,于海躍做了一件外人看來很不可思議的事:否決了一戶的貧困戶資格。原因很簡單,這位老人的兒子,恰是政府公務人員。政策有規定,家中有國家公職人員的,屬“八個一票否決情形”,不得享受貧困戶待遇。
有人嘀咕,第一書記初來乍到,敢在公家人頭上動土?于海躍想:只有動了領導家屬,才會讓群眾看到脫貧攻堅的公平無私本質,它決不會因為誰擁有特權而格外偏袒。之前村里人對于選誰不選誰,抱著十分無所謂的態度:“反正領導定了就是嘛,你們說是誰就是誰。”于海躍的猛然一擊,擊打出了公平公正的渾厚回聲,令老百姓精神一振,他們嘴上不說,心里都悄悄給這個年輕人豎起了大拇指。
于海躍這個第一書記,說來并不好當,潛經村、蘭口村、明村是3個自然村,如今要將它們納入統一管理,山高路遠的困難好克服,人心團結、牢牢凝聚卻不是那么容易達成的任務。
拿潛經自然村而言,它隸屬于桂林市雁山區草坪回族鄉,位于漓江中上游,處南嶺山系的西南部,距草坪回族鄉政府所在地7公里,距桂林市區30公里。平均海拔高度為150米,為中、低地形,境內屬于典型的巖溶地形,兩側高、中部低,處在自西北向東南延伸的喀斯特盆地中。潛經村是元代回民居住地。相傳村后有一山洞,曾經藏著《古蘭經》,潛經村的村名便由此而得。
潛經村人均耕地面積八分,其中田地只占二三分,剩下的是山地,以前老百姓種植水稻、玉米、甘蔗等傳統農作物,一天到頭,面朝土地背朝天地辛苦勞作,頂多也只是勉強混個溫飽,難以致富。
雖然農業發展頗為不易,但潛經村本身擁有著豐富的旅游資源——潛經村是具有300多年歷史的回民古聚居村莊,回族古建筑、清真寺、白氏宗祠、漓江蜿蜒穿過是全村的特色景點,但由于基礎設施的缺失,這些景致并沒有引來大量游客。
因為村里又窮又破,房屋低矮,在20世紀90年代,潛經村村中水塘周圍遍布垃圾,人未走近已聞惡臭連天,讓人說起潛經村來就皺眉頭,很多外村姑娘都不愿嫁為潛經媳婦。
再說明村三面環江,一面環山,受《漓江保護管理條例》規定,無法修建過江道路,是桂林唯一至今都沒有通公路的村莊,村民們只能靠渡船出行,但是每年汛期,漓江都會封航,小山村一下子成了座孤島,短則一兩天,長則一個星期,全年累計達半月以上,其間村民完全無法進出村莊。村民自艾自憐地嘆息:我們是一個被遺忘的村莊!
蘭口村村莊較小,人口較少,可用耕地面積也小。如何盤活蘭口村的荒地,是村民數年來的夢想。
潛經村、明村、蘭口村合并成為潛經行政村,拿在第一書記手里的,便是3個燙手山芋。因為地少、洪澇災害易發、交通不便等情況,經濟上不去,村民只得外出務工,解決生計問題。
2015年或許是潛經村命運的轉折點。2015年1月,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趙樂秦提出了沿大圩—草坪—興坪建設漓東百里生態示范帶的戰略構想;2015年3月,投入5000萬元的漓東百里生態長廊漓江慢行綠道建設項目正式啟動;8月,蘭口至大田二級公路啟動建設,建成后將成為草坪連接興陽公路的便捷旅游通道;10月,碧(碧巖閣)草(草坪)公路正式通車,一條寬闊的大道穿過潛經村直通草坪回族鄉政府……這一系列圍繞道路建設的舉措讓潛經村的脫貧前景漸漸清晰了起來。于海躍感到自己前路雖困難重重,但滿懷熱忱與期望,堅信只要目標明確、堅持不懈,一定會看到未來的幸福曙光。
樂土安居
歌曲《我的祖國》里,深情款款地唱道:“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家住在大河旁好不好呢?土壤肥沃,毗鄰水源,耕作性好,但事物的利弊往往是相輔相成的,占盡地利優勢,也難免受其拖累。
潛經自然村7、8、9隊所在田地,名叫“吊里”,這兒土質肥厚,收成上佳,是村民們公認的福地,可最近幾年,那兒到了汛期都會被淹。
吊里約200畝土地,村民種下了蔬菜、砂糖橘,以及桂花等名貴樹種,原本費了幾個月工夫,起早貪黑地小心看護著、照顧著,無奈“水龍”爬上岸,蔬菜絕產、砂糖橘大量減產,經水淹劫難的桂花樹勉強活下來,也是一副病懨懨無精打采的樣子。
于海躍去吊里仔細勘察,原來是消水洞出了問題,由于雜木、落石等混雜其中,水流裹挾它們滔滔而下,容量有限的路口漸漸被堵死,造成地面反復被淹。
在鄉黨委、政府的支持和幫助下,在村“兩委”干部的積極配合下,于海躍開始向上面積極爭取資金,先是緊急疏通了消水洞,接著修建了潛經排洪渠,徹底解決了每逢汛期吊里田地必被水淹的命運。村民之前飽受水患之苦,如今有了新的排洪渠,總算吁口長氣,放下了心頭大石。
潛經村從2011年起,就不斷向上打報告,提出他們的飲水問題,可直到2015年,于海躍上任第一書記,歷史遺留問題尚未得到解決。于是,他立即著手開展飲水設計測量,2017年進行潛經人口飲水升級改造工程,投資達55萬元。
于海躍剛擔任第一書記時,年僅25歲,有村民小聲嘀咕:“這小伙也太年輕了吧,恐怕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看到于書記為大家消堵修渠干實事,質疑他“太年輕”的聲音也漸漸消失了。截至2020年,潛經村累計維修和新建排洪渠、灌溉渠8條,總長6000米,投入資金40萬元,每一個項目,每一筆資金,于海躍都能講出背后長長的故事,為了給老百姓謀福利,他將“不容易”三個字藏進心底,臉上永遠掛著云淡風輕的和善微笑。
回顧這幾年第一書記的“跑程”,于海躍私車公用,一輛車竟然跑出了16萬公里里程。其中有一天,他從潛山村到雁山區,跑了5個來回,就是為了跑項目討資金,折返了600公里。
明村至今只有水路與外界通行,可村民們使用的是頗有歷史感的舊碼頭,狹小而濕滑,稍不留神,就會重重摔跤。村里孩子每天上下學,都得依靠一艘小渡船或竹筏通行,即便不是雨天,碼頭的青石板上也生長著滑膩膩的青苔,十分不便于行走。于海躍和村“兩委”商量,要給明村修新碼頭,村“兩委”嘆口氣:“早就想修了,但就是缺資金啊。”
于海躍開始積極地跑項目、跑資金,那段時間,他連做夢都是明村碼頭舊貌換新顏。
2016年底,明村平整了岸邊一塊荒地,修建了水碼頭,方便村民安全出行。不僅修了新碼頭,后來還花了22萬元投入到人口飲水升級改造工程上,解決了此前管道老化淤堵的問題。
淤堵到底有多鬧心呢?于海躍走進蘭口村時,遇到一個本村村民,粗著喉嚨問他,水龍頭都快擰斷了,水就是放不出來,到底找哪個解決?于海躍趕緊應允,一查,原因還是出在“淤堵”二字上。蘭口村是將山泉水直接抽到水塔,再運向各家各戶的管道中,遇上汛期,山上的雜木樹枝、淤泥碎土,都與泉水一道,裹挾而下,堵塞管道,自然屢屢造成停水危機。于海躍又開始打報告、立項目、找資金,爭取到了8萬元,為蘭口村修建了飲水用的沉淀池,解決了淤塞問題。2019年投資8萬元,進行了蘭口人口飲水沉淀池建設,更加提升了村民的飲水質量。
潛經村、明村、蘭口村等3個自然村的村民,在和別村村民拉呱時,有了一個新談資:咱村的生活污水處理站真牛!人家問到底哪里牛,潛經行政村的村民回答:“咱第一書記在生活污水處理點的出水口那兒,就是檢測池嘛,養大了幾條鯽魚,經過凈化的水,再也不會污染漓江水源了。”這事找于海躍證實,他嘻嘻笑著點頭承認,說養鯽魚是為做實驗,檢測污水經層層處理后水質真的達標,養大的鯽魚,肉質不錯,湯汁鮮美,證明這樣的水能養出好魚來。他說:“全村進行改廚改廁130余戶,并建了污水處理站,全部污水都流入化糞池,再經過管網進入村里的污水處理站統一處理,防止污水直排污染漓江。”
住在潛經村碧巖閣的吳東貴對此特別有感觸:“以前的廚房都是燒柴火,黑乎乎的,廁所里老是臭氣熏天,現在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2017年,吳東貴的廚房和廁所被納入改廚改廁工程,灶臺貼起了白色瓷磚,做飯用起了液化氣,接了自來水,衛生廁所干凈整潔,真是居所巨變。
安居才能樂業,于海躍帶頭做的一樁樁事,也許算不得什么宏大偉績,但每件事都和老百姓的利益切身相關,他樸實地認為,只有將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環境治理好了,才可暢談未來的發展前景,否則,破敗的人居環境,又如何談及產業落地、鄉村振興?
截至2020年,于海躍帶領村“兩委”,共爭取資金800萬元,修建停車場、光伏發電場、太陽能路燈、水渠、飲水安全工程、房屋立面改造、改廚改廁、民族廣場、明村碼頭、黨建廣場、池塘整治等18項基礎設施建設,極大改善了潛經村的生產、生活和旅游環境。
回想2015年,于海躍初到潛經村時,集體經濟是大寫的零。幾年來,潛經村集體經濟收入從2015年0元增長至2020年的20萬元,實現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強的可喜轉變。
產業芬芳
2015年以來,隨著漓東百里生態長廊建設大力推進,潛經村抓住機遇,開始著手打造漓江首條慢行綠道。
工期時間緊張,施工隊為了按期按質完成任務,采用輪班施工、24小時不停工的做法。施工人員雖然能倒班,但不分晝夜地趕工著實辛苦,大家的弦都繃得緊緊的,于海躍和村“兩委”等村干部為了慰勞施工人員,夜里12點之后,凌晨2點之前,他們在村里用大鍋燒了兩三桶紅糖姜湯,用電動三輪運送到施工現場。
一只裝湯的大桶,大約30斤重,于海躍白天累了一整天,晚上仍然不得閑,他堅持和村“兩委”干部去送姜湯,將熱乎乎的湯和暖融融的話一起送到施工人員面前。那是桂林一年之中最冷的季節,從漓江江面刮過來的風,簡直像一把小刀,在臉上旋啊旋,像要旋去一層皮。身上穿得再厚,風都能找到縫隙偷襲。
那段時間,于海躍常常凌晨2點后回去睡覺,早上6點又要爬起來,開始處理新一天的諸多事宜。累、冷和疲憊,他統統不在意,也許身體已經很疲勞了,精神勁兒卻一直很好,他將重心放在這里:一定要讓慢行綠道如期保質完工,這樣才可有效提升潛經村的旅游素質。
潛經村的旅游業慢慢發展起來了,白元林有著切身體會。
今年50歲的白元林,是個十足的苦孩子出身。10歲時,父親去世,他與寡母相依為命,家中生計都成問題,十幾歲時,他便去磚廠、水泥廠下苦力。
2012年,白元林千辛萬苦地考到了筏工證,可一條竹筏近萬元,他沒那個經濟實力自己來置辦,只能租別人的竹筏開,當時潛經村的旅游業還沒發展起來,做了幾個月,除去租金,并沒賺到兩個錢。
那時,白元林家里經濟很緊張,90歲的老母親不慎摔了一跤,癱到床上,兩個女兒都在念書,為了減輕家庭負擔,白元林只能告別妻兒老小,遠赴福建、海南等地,在建筑工地當零工。
2015年,白元林成為精準識別的建檔貧困戶,對于生性要強的白元林來說,反而覺得沮喪丟臉,但妻子語氣興奮地告訴他:“咱潛經村今后要發展旅游業啦!”
如同一道亮光閃過腦際,白元林回村了。一開始他也是循的老路,租了別人的竹筏來開,一個月頂多賺1000元。夫妻倆種了2畝地的蔬菜、5畝地的果樹,因為符合扶貧政策,領到了貧困戶的產業扶持獎勵金。
白元林領了獎勵,還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于海躍和他談心,了解情況,經過仔細調查,發現在潛經村里會撐竹筏的巧工還不止白元林一個,他們同樣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
2017年,雁山區對轄區內的漓江排筏進行徹底整頓,成立營運公司,全稱是“桂林草坪東岸漓江小鎮旅游投資有限公司”,買下上百只排筏,旅投公司統一定價,透明消費,客人更愿意乘坐旅投公司的竹筏。
于海躍動起了旅投公司的想法。他和旅投公司管理者經過數次深度交談,雙方達成協議:為貧困戶爭取到票務、安保、保潔、筏工等50多個工作崗位,并依據政策,建立了就業扶貧車間,白元林便是車間的一名筏工。
自從和村里另一位貧困戶一道,兩人共同負責一條竹筏,白元林感覺“從沒這么好過”,他平時在家做農活,有客人要租船了,公司電話通知,接到電話后他騎電動車,很快趕到碧巖閣驛站,領客人去竹筏。他不用再苦巴巴地守株待兔,平均算下來,每個月開竹筏也有2000元的收入,而且不會耽誤他干農活。
因為白元林積極上進,干活認真,為人本分,2020年,他又多了一個村中公益性保潔崗位,他像握著一把鋒利刀刃,切蛋糕一般將時間有條不紊地切成好幾塊。
說起如今的好生活,白元林眼眉都含著笑:“現在,我家的年收入至少在3.5萬元以上。”他一條條列了出來:“開竹筏至少有2萬元吧,賣蔬菜水果凈賺7000元左右,公益性崗位有6000元,現在他頂上了家里的主要勞動力,解放了妻子,妻子也能在附近打點小零工,再不濟,一年2000元總賺得到吧……”
白元林已經靠著自己的努力以及政府的扶持,順利脫貧,他感慨地說:“政府的政策這么好,人只要勤快一點,不會餓飯的。”
像白元林這樣有志氣的貧困戶,他們會一時淪為貧困,或因為家人生病、孩子念書,或因為自己的身體出了狀況,而絕非是為人懶怠。于海躍非常了解他們的特性,也發自內心地尊重他們,他總結說:“扶貧先扶志,要把貧困戶脫貧,轉變成我要脫貧,才能形成良好的脫貧致富氛圍,同時打造堅實的產業后盾和就業支撐,才能實現真脫貧、脫真貧,才能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
明村黃皮果產業,便是于海躍排除萬難,堅持要推下去的拳頭產業。
2017年、2018年,對于明村的黃皮果種植大戶吳橋保來說,堪稱災難之年。
2017年汛期,遇強降雨天氣,黃皮果沐浴在連天雨水中,泡水嚴重,引發了爆果后果。福無雙至禍不單行,2017年年底,明村又遇特大霜凍,導致黃皮果顆粒無收。吳橋保氣得靠在樹身,大口喘氣。
吳橋保種這7畝地的黃皮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從1995年開始,他便被確診為強直性脊柱炎。
吳橋保知道自己這一輩子都治不好身上的頑癥,他只能與之同生共存,但他不甘心因為病痛,就此放棄所有,不再努力進取。他是村里較早種植黃皮果的農戶,是村人公認的專家。
黃皮果接連遭受極端天氣的厄運摧殘,吳橋保難過到了極點,于海躍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膀:“保哥,別傷心了,黃皮果怕霜凍,我們可以嘗試大棚保暖防霜;至于無核黃皮果成熟時期遇降雨會爆果的情況,我也研究了很久,聽說欽州有一種‘黑皮黃皮果,耐水淹,不怕暴雨,而且口感更甜,你要不跟我一道去考察考察?”吳橋保猛然抬起頭來,眼眸里的精光,又一點一點地凝聚起來。
如今,吳橋保已經嘗試種植了數棵黑皮黃皮果,他對產業的前景發展充滿信心。
發展產業,是不折不扣的富民之路。2016~2020年,潛經村累計發放產業獎補200余萬元,每年根據農戶的種養殖情況,聯系專家舉辦現場培訓不少于兩場,產業獎補資金的發放增強了貧困戶發展產業的信心和動力,逐步形成了潛經村以甜竹、柑橘,蘭口村以蔬菜、水果,明村以無核黃皮果等為主導產業的一村一品格局,增強了產品競爭力、增加了農民收入。
在發展產業的路上,于海躍和村民同風同雨一道前進,村民早就當“小于”是自己人。
潛經村的白真石老人,經常給于海躍打電話,一通話就半抱怨半撒嬌道:“小于,土雞長大了,鴨子也養肥了,你咋還不來家吃飯?你喜歡吃辣口,到時我給你做子姜炒鴨吃,味道絕對正宗。”
于海躍的回答永遠是:“白大爺,你好好養著雞鴨吧,等我有時間的時候肯定要去你家拿。”白真石抱怨得更厲害了:“說了好幾年,從來不過來吃一口,我看你們共產黨啊,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這個革命傳統幾十年如一日,就沒變個樣!”
于海躍大笑著又詢問了白真石的身體狀況,老人說最近感覺挺不錯的,醫生開的藥也有,快吃完了曉得打電話給他,請他捎著自己去醫院開藥。于海躍便夸白大爺覺悟高,終于將老人逗笑了,不再“追究”他一次又一次地推托,不來吃雞鴨的過。
白真石患了直腸癌晚期,并擴散到肺部,以前做過手術,如今又擴散了,醫生建議不要再開刀,再度手術沒有太大意義,他自覺生命是一支燃燒得短短的燭,搖曳風中,說不定哪天就會忽然熄滅,但白真石十分樂觀,他接受了這樣的事實。
白真石的老伴已走了多年,他原本和兒子一家人生活,后來兒子、媳婦外出打工,家里就只剩老人一個,他舍不得離開山清水秀的村莊,覺得外面盡是高樓大廈,看得眼睛發暈,他便一人在家,養了好幾十只雞鴨,每年靠著養雞鴨,都有一份不錯的收入。白真石雖然被識別為貧困戶,他也從不愿歇著,不愿抱著“等靠要”的思想,眼巴巴等著政府幫扶,哪怕得知自己的直腸癌已走到晚期并已擴散,他依舊頑強地生活。于海躍到家里,將自己電話號碼一字一字地錄入白真石手機,對他說:“白大爺,我手機是24小時開機的,不管啥時候,你身體要是感覺不對,趕緊打給我,我就住在村里,過來接你送你去醫院,這樣比喊車更快些。”
存在白真石手機里的“小于”,不是書記于海躍,而是白真石自家子侄一般的存在。于海躍關心白大爺的身體,白大爺也不時“敲打”他:“你一忙起來就忘記吃飯,這咋行?年輕人也要小心愛護身體才是,你好久過來,我燉只土雞,炒只鴨子給你補補嘛。”
白大爺“批評”得沒錯,一旦忙起工作來,于海躍真是完全忘了時間,問他上一頓飯是什么時候吃的,他要偏著腦袋皺著眉頭,冥思苦想好久。大概兩年前,他不時感到頭暈、惡心,去醫院拍片,醫生嚴肅地告訴他,他的頸椎問題十分嚴重,已壓迫頸動脈和右側神經根,需住院開刀,好好治療。于海躍估算了一下手頭工作,實在是丟不開千頭萬緒的事來病床上躺著,便婉拒了醫生的意見。
就在那一年,有次于海躍從區里開會回來,正開著車,猛然感到腦袋暈眩得厲害,他一下沒剎住方向盤,車頭狠狠撞向路桿,車前蓋都撞凹一塊,幸好人沒有大礙,更沒有撞著行人,釀成大錯。但這事令于海躍心驚不已,思忖再三,決定采用中醫按摩的治療方法。
首次治療,醫生用手按著他變形的頸椎,這個面對痛苦向來云淡風輕的昂藏男兒,竟疼得止不住眼淚。從治療床上爬起來,他虛脫一般,還和醫生眼淚花花地開玩笑:“大夫,您這手絕活,怕就是武俠小說里寫的‘分筋錯骨手吧?”
于海躍需要長期戴頸托牽引器治療,但他依然堅持下村走訪貧困戶,指導發展產業。
頸椎稍微才好一點,腰椎又出了毛病,因為長期的加班和高負荷的工作,他患上了腰間盤突出,壓迫右側神經,疼得半宿難以入睡。于海躍揉著腰去看醫生,虛心詢問他是否需要多運動來強健體魄,醫生一張張翻看他的體檢記錄,遺憾地說,因為他還有髖關節、膝關節囊腫,所以最好靜養,不要走太多的路。
于海躍的苦心和努力沒有白費,潛經行政村于2018年脫貧摘帽,貧困發生率降至1.43%,2019年全村實現貧困戶全部脫貧。潛經村村民的收入,如同芝麻開花節節高,從2015年的人均收入2000多元,到2019年統計的人均8000余元;從2015年整個潛經村只有一家小賣店、一家農家樂,到了現在,能吃飯的農家樂達到5家,供住宿的農家樂有7家,小賣店發展到6家,在彎彎村道中,還藏著一間現代感、小資味十足的奶茶店。
如今,潛經村已是具備十級抗打擊力的實力派行政村,面對2020年突發的新冠疫情,在鄉黨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海躍與村“兩委”、駐村隊員積極開展線上、線下多種銷售模式,對貧困戶滯銷農產品進行銷售,2~4月,累計銷售砂糖橘、沃柑5萬余,解決了農戶的燃眉之急。
說一千道一萬,第一書記撲下身子拼命干,為的都是老百姓的日子能一天更比一天好,村民的經濟收入增長,精神生活豐富,好日子更有奔頭,臉上笑容更稠密。于海躍的名字,諧音“魚海躍”,海闊憑魚躍,父母當年給襁褓中的嬰孩命名,是希望他能胸懷天下,志在四方,游弋寬闊海域,父母相信孩子長大后,他不管去往哪里,都同樣會持一顆真摯純善的心,盡自己最大努力去拼搏、去奮斗、去奉獻,讓青春無怨無悔、發光發熱,讓歲月書寫精彩從不虛度。
責任編輯/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