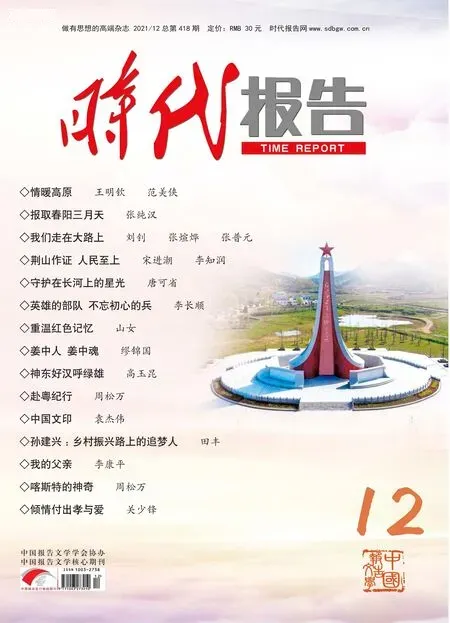我的父親



此時此刻,父親就那樣靜靜地、靜靜地躺在病床上,神態安詳得像進入熟睡的夢鄉一樣。父親一定是在做一個甜蜜的夢,在美麗的夢境中,父親決然義無反顧地去往那個無憂無慮、無病無痛的天界仙境了。父親終于把一切都放下了,放下他一生為之奮斗的崇高事業,放下他一生為之操勞的幸福家庭,放下他一生相濡以沫的恩愛妻子,放下他一生摯親摯愛的骨肉兒女。從此天地相隔兩茫茫,不堪思量永難忘。我知道,父親此別是再也回不來了。頓時,我淚如泉涌,用心銘記下這一痛心的時刻:公元2021年10月13日(農歷辛丑年九月初八)17時36分,父親在北京香山醫院溘然長逝,享年98歲。
革命一生不忘初心
父親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1924年農歷三月初三,陜北黃土高原已是冬去春來日暖花開的時節,父親出生在陜西米脂縣郭興莊鎮李興莊村一戶普通農民家庭。爺爺奶奶育有四子兩女,父親為長子,按李姓輩分排為錦字輩,四子取名最后一個字分別為榮、華、富、貴,因此,爺爺給父親取名為李錦榮。父親長大參加革命后,覺得榮華富貴僅僅是農民的個人愿望,而革命人的志向應當更遠大、更理想。于是父親便自己改名為李景云。《淮南子·天文訓》曰:“虎嘯而谷風生,龍舉而景云屬。”景與錦諧音,輩分不改。景云則為祥瑞之云,但父親是取革命者壯志凌云之意。
父親從小就讀于久負盛名的陜西米脂中學。米脂中學是1927年4月由著名愛國人士、教育家杜斌丞先生和地方賢達共同贊助創建的,已有90多年的辦學歷史。創建之初名為三民二中,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建立革命根據地之后,更名為陜甘寧邊區米脂中學。米脂中學建校90多年來,培養出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級領導干部和著名科學家,可謂桃李滿天下,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父親在米脂中學就讀時,受到了革命的啟蒙教育,也打下了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底蘊。
1944年6月,20歲的父親從米脂中學畢業后立刻投身革命,在陜甘寧邊區政府志丹縣二區工作。志丹縣原名保安縣,1936年6月,為紀念紅軍東征戰役英勇犧牲的民族英雄劉志丹將軍,更名為志丹縣。1936年7月,中華蘇維埃中央人民政府奠都志丹縣,黨中央、毛主席曾經在這里戰斗生活了6個多月,被譽為“中國革命的紅都”。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抗戰的中心,也是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的指揮中樞所在地和總后方。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邊區軍民一邊要開展武裝斗爭,一邊還要搞好經濟生產和文化建設。父親參加工作之后,充滿革命的熱情和活力,積極投入到轟轟烈烈的軍民大生產運動中,積極下鄉組織農村農業生產,以實際行動支援抗戰前線。由于父親好學上進,工作積極勤奮,只工作了半年,就被黨組織推薦到以革命圣地延安命名的延安大學繼續深造。
延安大學最早是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兩次會議討論,將1940年5月成立的澤東青年干校、1939年7月成立的中國女子大學、1937年10月成立的陜北公學院三校合并組建的。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被譽為中國共產黨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為延安大學首任校長。父親在延安大學就讀時,中共中央西北局已于1944年4月將行政學院并入延安大學,周揚為延安大學校長。父親是在延安大學行政學院教育系,系統地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教育學習,在圣地延安革命搖籃的熏陶下,提高了理論素養,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更加堅定了革命的理想信念。
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爆發全面內戰,對解放區大舉瘋狂進攻。為了粉碎國民黨軍對陜甘寧解放區的重點進攻,黨中央、毛主席開始了轉戰陜北的偉大歷程。1946年8月,父親從延安大學畢業回到米脂縣人民革命政府,立刻投身到轉戰陜北的備戰工作中去。1948年4月,在全國解放戰爭勝利在望的時候,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懷抱。父親在米脂縣又積極參加了習仲勛同志領導的陜甘寧邊區土改工作。當年,習仲勛同志堅決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土地問題的《五四指示》精神,力排土地改革中“左”傾思想的影響,通過調查研究和整頓黨的領導,結合邊區現狀,探索出一條適合陜甘寧邊區實際的土改路線,為其他各解放區和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這年8月,父親在土改工作一線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給了偉大的革命事業。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隨著大批陜北干部南下,先后擔任陜西戶縣永定區區長、戶縣城關區委書記、咸陽地委干事、鎮坪縣團委書記、縣委組織干事、安康地委辦公室秘書、安康行政專員公署辦公室主任。我看到1963年12月安康專署辦公室給父親的一份組織鑒定說:“1.對黨一貫忠誠,政治立場堅定,在工作中能正確地貫徹黨的政策,堅持原則,按政策辦事。2.工作一貫認真負責,如認真地細致地審閱和修改公文,并經常親自動手起草。對領導布置的工作,認真地貫徹執行,積極去辦,按時完成。3.民主作風好,遇事能和大家商量,如自己寫的材料和修改后的公文,總是征求同志們的意見。4.吃苦精神好。如經常主動提出要求下鄉,下鄉工作常常到困難的地區去,并及時寫報告,反映情況。5.個人學習抓得緊,學習中能聯系實際。6.關心同志生活,主動幫助解決同志們生活困難……”
這份組織鑒定是對父親在專署辦公室工作的肯定,又何嘗不是對他一生革命工作的肯定呢!
文革后期,安康地委、專署“靠邊站”的老干部分批從“五七”干校下放到農村勞動。父親從“五七”干校下放到紫陽縣蒿坪河區農村勞動,當時我在安康縣嵐河區知青點插隊,我便步行50多里山路去看望下放勞動的父親。我去的那天父親正在地里勞動,農民聽說我找父親,先把我領到父親的住處,然后下地去叫我父親回來。父親住在一間農民的房子里,屋子的一角鋪著父親的木板床,支了一張木桌,屋子另一角柴火堆上架著陜南農村常見的鐵吊鍋,燒水做飯都是用吊鍋,屋子被柴火熏得黑乎乎的。原以為老干部下放勞動都是被人看管得很嚴,可是父親下地并沒有人看管,一個人很自由地就回來了,只是父親全身上下整個就是農民模樣,全然融入到下放農村勞動生活中了。父親看到我來非常高興,立刻架起柴火給我做飯。父親本不會做飯,下到農村竟然自己也學會做一些簡單的飯菜了。記得那天父親給我做的是拌湯,水燒開了,把拌好的面疙瘩往吊鍋里一攪和,煮開了再倒進炒好的酸菜,一鍋酸菜拌湯就做成了。酸菜拌湯是陜南人最愛吃也經常吃的飯食,在生活困難時期忙時吃干,閑時吃稀,拌湯是當主食幾乎天天要吃的。但是父親那天做的那鍋酸菜拌湯很稠,做好后還給我碗里滴了幾滴香油,在我的味覺記憶中,那是我吃過的最香最好吃的拌湯了,我連吃了三大碗,直到吃得鍋光碗凈,才突然發現,父親早就放下碗在一旁開心地看著我吃完。
1970年,“靠邊站”的老干部有限地分批恢復工作,父親被下放到陜西省旬陽縣,先后擔任神河區任區委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相當于區長一職)、旬陽縣文教局長。1975年再次落實干部政策,父親調任安康地區衛生學校黨委書記。
文革時期,學校是受沖擊最嚴重的重災區之一。父親到任前,安康衛校幾經搬遷,甚至一度停辦,學校發展十分緩慢。1977年9月,全國恢復高考制度以后,父親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帶領教職員工堅持艱苦奮斗,勤儉辦校,學校逐步走向正軌,教學質量不斷提高。1982年、1983年連續兩年在全省中等衛校畢業統考中獲得第二名的好成績,1984年再獲第一名,受到了陜西省衛生廳、安康地委、行署的表彰。1986年,父親以副廳級職級離休,2014年,獲批享受副省部長級醫療待遇。1995年、2005年和2015年,連續3次獲得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向抗戰老戰士老同志頒發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50、60和70周年紀念章,表彰父輩的歷史功勛,彰顯他們的榮譽地位。
20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父親又獲黨中央首次向黨齡50年以上老黨員頒發的“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而這年,父親實際已經光榮在黨73年了。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父親一生牢記使命,畢生都努力踐行為崇高革命理想而奮斗終生的鋼鐵誓言。
學習一生孜孜不倦
父親一生酷愛讀書學習,這與父親從小就讀于治學嚴謹、人才輩出的米脂中學有關。在米脂中學,父親在接受革命教育的同時,如饑似渴地飽讀詩書,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直到他96歲高齡住進醫院時,還常跟醫護人員大段地背誦唐詩宋詞古文佳句。
在父親的書桌案頭上,總是擺滿了俯案時比人頭還高的一摞摞書籍卷冊。讀書人惜書如珍。父親的書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全部看不到書籍原來的封面裝幀設計,幾乎清一色都用畫報紙,沒有畫報紙就用報紙包上一層書皮,然后在書的封面和書脊位置寫上書名。
父親讀書的興趣很廣泛,除了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著作之外,最喜愛的書便是《魯迅全集》了。1973年,人民文學社出版了20卷本的《魯迅全集》,當時印量有限,父親非常喜歡,立刻托書店的朋友幫助購買一套回來,連夜捧讀。讀過之后,父親還是有點遺憾,他說,也許是因為特殊年代出版,所以這套全集并不能全面展現魯迅的作品。因此,當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出版《魯迅全集》,父親又全套購買回來收藏閱讀,直說這個版本收得全,出得好。
父親還喜歡讀《史記》《資治通鑒》《春秋》《東周列國志》《紅樓夢》《古文觀止》《聊齋》等中國古典名著以及雨果、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高爾基、契訶夫等外國著名作家的作品,常常用書中的故事來教育我們。一本《聊齋》上面真是紅筆圈來藍筆點,顯然讀過不止一遍。有次父親給我講述了雨果《悲慘世界》主人公冉阿讓的故事,給我以強烈的震動。父親給我講,書中的主人公冉阿讓為了養活孩子偷了一塊面包被判5年苦役,卻在監獄里蹲了19年。冉阿讓出獄后心懷報復社會的扭曲心理,又偷竊收留他的主教的銀器再次被警察抓住。而主教體諒了冉阿讓的生活困境,沒有指證冉阿讓的偷竊行為,反而再贈送他一些銀器以解生活之憂。正是因為主教善良的以德報怨之舉,給冉阿讓心靈上帶來巨大震動和感化,從此他棄惡揚善,痛改前非,為社會做出貢獻。書中所展現的正是人性善良博愛的偉大光輝。
父親講述冉阿讓的故事,讓我深刻感受到了善良與道德力量的偉大所在,吸引我不但立刻找來此書仔細閱讀,還常常把書中冉阿讓的故事講給我的孩子聽,教育孩子與人為善、以德報怨成為家庭的一種道德傳承。
小時候,我對父親書架里大部頭的理論書籍不感興趣,但是意外地發現書架里竟然還有幾本蘇聯科幻小說強烈地吸引了我。書中長長的外國人名字難讀難記,可是有一本講述宇宙、星球、太空和21世紀一群來自不同國家的科學家乘坐火箭飛船到太空去旅行,地球人也大批移民到外層空間,住進環繞地球軌道的美麗太空城市的故事,卻給了我無限的遐思和向住。父親還有一本《科學家談21世紀》的科普書,也激起我對科學知識的極大興趣和豐富想象。當年最流行的少兒科普讀物《十萬個為什么》,記得父親最先買的是第三冊,講的就是天文學知識上的為什么。與其說這本書是父親給我買的,倒不如說是父親引導我和他共同閱讀。書中我讀不懂的地方,父親就把他知道的天文學知識用通俗的語言講解給我聽。從父親的講述中,我從小就懂得了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開啟科學智慧大門的金鑰匙,這也正是我從父親讀書生活中汲取到的最大能量。
父親80多歲的時候,突然詢問我電腦方面的知識,原來,他從報紙上不斷地讀到有關互聯網的消息,說網上世界包羅萬象,無所不有,讀書、看報、聊天更加方便。因此,父親要學習電腦,要用電腦學習上網沖浪。于是,我趕緊給父親配置了一臺電腦,教父親怎么聯機,怎么上網,怎么點擊打開鏈接等。父親著實過了一把“網癮”,但還是因為多年的閱讀習慣難改,最終還是棄網,重新拾起散發著油墨香的紙質書報閱讀。
2010年,父親陪伴母親來京治病,母親病愈之后,我挽留父母在北京單獨居住在我的另一處住所。父母也非常樂意,常說老了之后和子女同城不同屋居住最好,互不干擾。這樣,我和在北京的姐姐李冰、二弟康力全家每逢周末便買些營養品和水果去看望父母。一大家人四世同堂團聚北京,共享天倫之樂,是父母晚年最大的欣慰。我知道父親有酷愛讀書學習的嗜好,每次去看望父母的時候,都要將一周來的各類報紙帶給父親看。父親每每從報上看到有新書出版的消息,凡是他感興趣的,都開列一個書單給我,讓我下次再來的時候買了給他。有一次,父親讓我買一本《時間簡史》,我吃驚的是我只聽說過這本書是英國物理學家霍金所作,卻從沒有讀過。于是趕緊上網查了一下,原來霍金的這本書講述的是關于宇宙本性的最前沿知識,包括我們的宇宙圖像、空間和時間、膨脹的宇宙、不確定性原理、黑洞、宇宙的起源和命運等內容,深入淺出地介紹了遙遠星系、黑洞、粒子、反物質等知識,并對宇宙的起源、空間和時間以及相對論等古老命題進行了闡述。霍金在書里探究了已有宇宙理論中存在的未解決的沖突,并指出把量子力學、熱動力學和廣義相對論統一起來存在的問題。該書的定位是讓那些對宇宙學有興趣的普通讀者了解他的理論和其中的數學原理。當時,父親已經是90多歲的高齡,竟然要讀如此高深的科學專著,令我自愧不如!還有一次,父親問我區塊鏈的科學原理,同樣把我問得目瞪口呆,趕緊找來有關資料惡補區塊鏈的知識,然后再給父親介紹。
當年,父親兩手空空拎個小包就來了北京,一住10多年,如今,父親在北京的書房里又是滿滿當當的滿書柜、一書桌的書,墻角上堆著的紙箱子里都是看過的報紙和雜志,也總舍不得當廢紙賣掉。
父親看報學習還有個習慣,就是看到報紙上好的文章,就剪下來,分門別類用心貼在舊書或舊雜志上,重新編輯成書交給我說:“這便是我編給你的書,好好地讀吧,寫的都是做人做事的至理名言!”
我驚喜地雙手接過父親的“書”,其實是一本筆記本,用舊報紙包的書皮,書名是用重筆描寫幾個粗黑大字《留給康平的書》。翻開里面一看,原來都是父親讀報剪貼下來好的文章匯集而成,旁邊批寫著父親的讀后感。有的短文父親工整地抄寫下來。名人名言勵志人生,凡人瑣事感人心懷,篇篇精品,字字珠璣,讀來愛不釋手,受益匪淺。
好人一生平平安安
正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樣:“好人一生平安……”父親就是這樣一個好人,一生都平平安安!
1965年,父親到安康縣恒口區千工人民公社蹲點參加社教運動,也叫“四清”運動,是當時黨在農村開展的以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和清組織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校放暑假的時候,父親帶我和弟弟到他蹲點的地方,和他一起吃住都在農民家里,要我們從小感受農村農民的生活。一天,我拉開父親晚上寫材料的桌子抽屜,發現抽屜里有兩沓全是一角的紙幣和半斤的糧票,便問父親這么多零錢干什么用的,父親說這是每天給農民的飯錢。那時干部下農村都是吃派飯,今天派在這家吃,明天派在那家吃,每頓飯父親都把事先準備好的零錢和糧票交給農戶。父親說,給農民大票如果找不開零錢就不收飯錢了,可是農民生活不易,白吃不給錢那怎么能行!從這件小事可見父親下鄉很能體恤農民。
十年動亂開始不久,許多老干部被打倒了。父親也不例外,頂著一頂“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帽子靠邊站了。那時,大街上和專署大院到處都貼著批判“走資派”的大字報,引來“革命群眾”爭相觀看。我們住在大院里的孩子誰要是看到有批判自己父親的大字報,頓時臉上無光,抬不起頭來。可是我們很少看到有批判父親的大字報貼出來,有天我竟然好奇地問父親為什么,不等父親回答,母親便說:“還不是因為你爸是個好人,造反派就不批判了唄,好人還是有好報啊!”那段時期,批判父親的大字報從來沒有上過街,專署大院即使貼有批判父親的大字報,也是輕描淡寫地作樣子寫幾句,很快就被人以貼新的大字報為由給覆蓋了。后來我才知道,這都是因為父親為人善良,贏得了群眾的尊重、敬重,他們暗中在保護父親。其中有一個在專署機關燒開水的鍋爐工,誰要是說父親一個“不”字,他就上前跟誰極力辯論,非要爭贏不可。原來有一次,父親去醫院排隊掛號看病,聽到一個中年婦女抱怨說,她丈夫在專署機關忙得不顧家,孩子病了也不回來看看,她手里這點錢也不知道夠不夠孩子看病的,真是難死人了。父親聽到她講的情況,大致猜到她丈夫是誰了。便從自己身上掏出錢來給那婦女,先給孩子看病要緊。那婦女回家給丈夫說今天遇到一個大好人,丈夫問妻子怎么回事,妻子告訴他今天帶孩子看病可能錢不夠,一旁有個操陜北口音的大個子陌生人,沒留姓名就掏錢給孩子看病。這個婦女的丈夫正是專署機關的鍋爐工,他立刻猜到給妻子錢的是我父親,對父親感激不盡,逢人便說父親是個好人!
1967年8月19日夜,安康發生了文革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武斗,一派攻打另一派占據的地委、專署機關大院。事后才知道,這次武斗打傷地委、專署機關干部百余人,砸毀了辦公設施,抄了檔案室部分檔案。武斗還在激烈地進行中,突然有人急促地敲我家的門。父親開門一看,原來是專署機關的一個干部,曾經他還給父親寫過大字報,可是眼下他正被武斗人員追打,情急之下跑來家屬院求救。父親不計前嫌,趕緊把他讓進屋,叫他藏在床底下躲避,并遞給他一些水和餅干。這時,武斗人員已經追到家屬院挨家挨戶地搜查。等搜到我家時,父親把我叫到前面開門。因為父親已經是“靠邊站”的當權派,而我就算掛個名,也還算是“紅衛兵”,興許還能抵擋一陣兒。碰巧敲門搜查的人我正好認識,是我初二同班同學的哥哥、初三年級學生,這才沒進我家搜查,父親也沒有因窩藏“武斗人員”而遭禍殃。聽說當晚被抓走的安康地委、專署干部被一派押解到軍分區向軍方施壓,又被另一派“營救”出來轉移農村,幾經折騰,傷人無數。后來我有點想不通,便問父親,為什么要救給他寫過大字報的人,父親淡淡一笑說,他也是身不由己,如果不救,我們能眼看著他被抓被打嗎?
果然父親的好心得到了好報。安康武斗愈演愈烈,為躲避武斗槍炮,我們從武斗前沿專署大院遷到安康老城東關,有好心人收留我們;父親和城內一批老干部被“劫持”到城外,父親沒有遭到“劫持”人員的打罵;又有好心人護送我們出城和父親團聚。據史料記載,1967年8月31日至1968年5月,安康縣兩大派造反組織連續發動的大規模武斗造成734人死亡,燒毀大街小巷11條,炸毀防洪堤8357立方米,安康城內第一座自來水廠的水塔被炸毀,縣委檔案大樓被焚,53所機關、學校成為廢墟,3800多間房屋化為灰燼。慘重的教訓成為我們這一代人心里永遠抹不去的傷痛。而我們一直處于派性武斗的戰火中心卻毫發未損,也應歸因于父親好人好報的造化。
父親參加革命就離開家鄉,長年在陜南工作,但是家鄉建設發展卻一直掛在父親的心上。每次父親回老家,都要在前莊后村轉轉看看,給家鄉建設出謀劃策。從李興莊村到村前的公路要過一條無定河的小支流,別看小河溝平常水淺蹚著就能過去,可是遇到雨季洪水來襲,小河溝立刻水漫金山,攔住村里人出不去。父親從小就夢想著將來能在小河溝上修座橋那該多好啊!有一年,父親聽說村里終于籌錢要在這條河溝上修橋了,父親立刻捐錢助力修橋。橋建成之后,村里人在橋頭立碑,感念捐助者,父親的名字赫然其中。
2020年3月,父親因病住進北京香山醫院。父親此時97歲高齡,已經臥床不起,照料父親的護工是一位中年婦女,她不怕勞累不怕臟,悉心照料父親飲食和大小便,令父親非常感動,連連稱贊護工這樣的好人難找。當父親聽說護工收入并不高,而且家在山西農村生活困難時,便將我們看望他帶去的水果、點心拿給護工囑咐一起吃,還讓我們每月給護工一些零用錢貼補家用。護工很感動,連說照料父親也是遇到了好人。
父親一生為善,皆因信念使然。父親常用三國時劉備告誡其子劉禪遺詔中的話來告誡我們:“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這句話講的便是做人的道理,切記: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
慈愛一生恩重如山
父親一生心懷愛心,充滿大愛。父親對他的父親、我們的爺爺敬愛,對弟弟妹妹、我們的叔叔姑姑關愛,對妻子、我們的母親恩愛,對我們兒女更是倍加慈愛,恩重如山。
父親15歲那年,奶奶剛生下三叔還沒滿月,軍閥胡宗南的匪兵進到村子搶東西,奶奶踩著梯子正在把家里一點值錢的東西藏起來,聽到匪兵槍響,奶奶一慌張從梯子上摔了下來,從此落下重疾臥床不起,很快撒手人寰。父親是長子,很有擔當地幫助爺爺分擔起家庭的生活重擔,每天放學回家,父親放下書包就下地幫爺爺干農活,照料幾個年幼的叔叔姑姑。有一次,父親下地幫爺爺干農活回來晚了,看到幾個弟弟妹妹蹲在自家窯洞門口,正眼巴巴地望著別人家孩子端著碗在院子吃飯,一個餓得忍不住哭出聲來,其他幾個也都跟著大聲地哭起來。父親從小就性格剛強,看到弟弟妹妹看人家吃飯就哭,氣得給他們每人頭上一巴掌,攆回家訓斥說:“人窮要有志氣,看著人家吃飯就哭,就是沒出息的樣子,今后誰也不許這樣!”說完便趕緊自己動手給弟弟妹妹做飯。
新中國成立以后,父親從陜北南下工作,離家遠了,但他仍然時刻惦記著在家的爺爺和叔叔姑姑們。每個月發工資的當天,父親便到郵局給爺爺寄去15元作為贍養爺爺的生活費。20世紀60年代,15元錢在當時的農村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接近當年城鎮平均工資的一半,最低生活費的3倍。二叔長大成人以后,父親給二叔在安康安排了工作,辦了婚事成了家。三叔參加工作以后又想當兵,征求父親意見,父親全力支持,三叔上了對印自衛反擊戰前線,在火線入黨提干,父親為三叔感到自豪,說,真是一人當兵,全家光榮。兩個姑姑出嫁以后,父親每次回老家探親都要去探望,關心她們的生活。有次父親探望二姑回來,充滿感情地對三叔說:“你二姐長得跟咱媽一模一樣!”這句話表達了父親對母親、我們的奶奶深藏在心底的無限思念。
父親一生對妻子、我們的母親非常恩愛,工作再忙,只要回到家里總要幫著母親多干點家務活,關愛體貼之情非常感人。有時父親干家務活有點笨拙,出了力反而不討好,甚至幫了倒忙,父親和母親也爭吵,吵著吵著又一笑了之,和好如初。
陜南冬天家家都要腌鹽菜準備過冬。有一年,母親將要腌制的大青菜洗凈晾著,還沒等晾干,父親就主動幫母親把青菜切碎了。切菜是個力氣活,父親也是好心幫母親。誰知道母親看了卻數落父親切菜切得塊太大了腌不透,也不好看,青菜也還沒完全晾干,這樣腌出來的鹽菜水分大,容易壞。一點小小的分歧,竟然釀成一場爭吵。父親心里好委屈,卻也不再言語,默默地拿起菜刀重新將大塊的青菜細細地剁碎,母親便也默不作聲幫著一道拌鹽裝壇腌菜。那壇鹽菜是我們那年冬天的主打菜,每次母親切了蔥、姜、蒜,過油炒了,父親也總在碗里挑塊大的吃,還自嘲地笑著說“大塊的有嚼頭”,母親聽了也不好意思地笑出聲來。大塊的鹽菜里就這樣透出父母的千般恩愛。
父親對兒女不善于情感表達,我們幾乎從來沒聽過父親對我們說過愛啊、想念啊這類動情感人的話,父親是把對兒女的慈愛深藏在內心里,表現出來的總是一副不茍言笑的嚴父形象。特殊時期學校停課,父親對我們的教育從未停過,經常給我們上課。上課時,讓我們立正站在他面前,眼睛望著父親聽他講課。父親給我們講春秋戰國五霸七雄相爭的智慧故事,講唐詩宋詞的唯美詩句,講中華傳統美德禮儀規矩,記得父親反復告誡我們一定不要抽煙時,給我們算了一筆賬:按一天平均抽一包煙計算,那時最普遍抽的“寶成”香煙兩角錢一包,抽一個月的煙就把一個人一個月的生活費抽沒了,或者一條新褲子、兩支新鋼筆就抽沒了。沒煙抽又沒錢買的時候,在地上撿煙頭的樣子是喪失尊嚴、非常狼狽的。父親一邊說,一邊給我們學人在地上撿煙頭湊到嘴邊抽的可笑樣子,我們忍不住笑起來。父親卻嚴厲地瞪著我們,嚇得我們趕緊止住笑望著父親,眼睛再不敢朝別處望一眼。正是因為父親的諄諄教導,我們兄弟三個這輩子都像父親一樣不嗜煙酒。
因武斗全家被困在安康城內時,城內居民每人每月只能供應兩三斤口糧。沒有吃的,供銷社便把庫存的黃花、木耳、葛根粉都拿來定量賣給城里的居民,每每用黃花、木耳煮一鍋湯,然后倒進調好的葛根粉煮成濃稠的湯來充饑。這時,父親和地委、行署的一些老干部都被派性組織控制起來,集中在原安康科委的院里辦“學習班”,雖然學習班的食堂也管吃,但也沒有正經的米面做飯,常常把黃豆用水泡脹了再油炸了當飯吃。就是這份按頓定量的油炸黃豆父親也舍不得吃,常常拿回家來給我和弟弟吃。當時只覺得這是天下最好最香的吃食,此時再回味起來,才能體會到那都是滿滿的父愛的味道。
清廉一生明志修身
作為黨員領導干部,清廉一身正氣,勤儉兩袖清風,正是父親一生工作和生活的真實寫照。
父親在陜甘寧邊區參加革命工作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南下的時候,干部一律都實行供給制,由單位給干部個人供給生活所需,吃在食堂,住在宿舍,春秋兩季發放換季衣服,每月還發給幾元到十幾元不等的零用津貼,用于購買肥皂、牙膏等個人生活用品。因此,在參加革命后很長一段時間里,父親根本沒有個人家庭財產的概念,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父親在安康行政專員公署任辦公室主任,同時分管專署機關后勤服務工作,我們一家還住在父親的一間不到12平方米的辦公室里。房間的一角是父母的床,靠床安放著父親的辦公桌,另一角支一張單人床再加一塊不到一尺寬的木板,是我和二弟的床。我們出生后先是住在保姆家里,上幼兒園是在全托班,上小學是在食宿班,只有周六和寒暑假回來和父母一起在辦公室住,在專署機關大食堂吃飯。父親沒有家務負擔,把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直到三弟出生,辦公室實在住不下一家五口人,父親在與專署機關大院相通的小家屬院找了一間15平方米大的房間,一家人這才搬離了父親的辦公室。
20世紀50年代初,供給制改為工資制以后,父親的工資定為113元,這在當時屬于高工資,高出當時安康城鎮職工平均工資3倍多,再加上母親的工資,我們一家人應當是生活無憂了,但是那時的日子依然過得非常節儉。小時候家里的家具除了機關公用桌椅和木板床之外,便是父親買來的3個樟木箱子,說是準備將來給3個兒子一人一個,另外就是父親用釘子釘幾塊木板自己做的一個兩層的碗柜,放在一張桌子上。做飯用的炭爐和柴火灶都是父親用碎磚塊和黃泥糊的,父親糊爐灶的時候我們在旁邊看,父親一邊糊,一邊告訴我們爐膛要大,收口要小,便于聚焦火力。父親教會我們以后,再糊爐灶就由我們自己動手了。炭爐燒的是當地產的大塊石炭,父母和我們自己用鐵錘砸成小塊填到爐內燒,碎炭末再和上黃泥做成炭岜子掰成小塊再燒,一點都不浪費。文革期間,專署機關食堂停辦,小家屬院幾家人做飯都在自家門口,一家炒菜,各家聞香,倒也其樂融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食品供應緊張,父親騎著自行車到鄉下農村去買蘿卜、白菜回來以“瓜菜代”填飽肚子。為了讓我們能吃飽一點,父親也多買一點,結果回來的路上還重重地摔了一跤,自行車胎也漏了氣,父親推著自行車走了好幾里路。父親下放到旬陽縣神河區當區委書記的時候,有一次,神河街上的食堂殺了豬,特意留了一些醬豬頭肉問父親要不要,父親沒舍得買醬豬頭肉,只買了兩個醬豬蹄拿回來給我和二弟一人一個。當我們確認父親不是讓我們當菜就飯吃,而是就這樣吃掉時,又是驚訝,又是驚喜,很快就狼吞虎咽地吃個一干二凈。我們吃的時候,父親就一直在一旁看著我們,自己卻沒舍得多買一個一起吃。這只醬豬蹄是我人生第一次奢侈大餐,醬豬蹄也成了我喜愛吃的食物,但是,從此再也沒吃到父親當年給我們買的那只醬豬蹄一樣的美味來。
20世紀70年代末,一時興起比家里的家具有多少條腿,比如說桌子、椅子、柜子都是4條腿等,據說最多的要達到72條腿。當時我們家的家具不管多少條腿也都是公家的,自家沒有置辦一個像樣的家具。于是,我們攛掇父親也給家里添置一點像樣的家具。父親不屑地說,比家具腿有意義嗎?多幾條、少幾條不都是一樣過日子嘛!把工作干好了比什么都有用,都有意義!但是經不住我們一再纏磨,父親最終還是同意添置一個大衣柜。但是為了省錢,父親沒有去家具店買現成的漂亮家具,而是去木材廠買了半立方木材,請了木匠來家里做衣柜,然后自己買了一種叫哈巴粉的棕色顏料和清漆,自己打磨染色上漆,說這樣能省不少錢。父親總是這樣生活節儉得過且過,從不追求時尚購買大件物品。家里后來添置的第一對沙發是我自己動手做好拿回家的,第一臺電風扇是我給父母買的,第一臺單門電冰箱是弟弟家換下來的,一臺顯像管彩電看得色彩還原都失真了還舍不得換新的,后來還是長孫李樂從北京回老家給爺爺奶奶買了一臺液晶彩電。2010年,父親陪伴母親來北京看病,病愈后我挽留父母:留在北京不回安康了。父母說,來的時候都沒帶什么換洗衣服,我和在京的姐姐李冰、二弟康力便爭相給父母買衣服。父親趕緊叫停,說現在的衣服質量好,怎么穿都穿不爛,有兩件能換夠穿就可以了,買多了也是浪費。父親對這樣儉樸的生活非常滿足,常說,過去皇帝也沒看過彩電,沒用過這么多的家用電器,要懂得知足常樂,知足常樂啊!
父親長期擔任領導干部,少不了有人來請父親幫忙解決實際問題,事后也有人拿來禮品登門感謝。但是幫助解決實際困難父親往往一口答應,事后感謝父親就一概謝絕,拿來了也拒收,怎么拿來的還怎么拿回去。有時弄得對方很尷尬,父親也不管不顧。有一次,以前一個在專署的下屬對父親一直心存感激,他知道父親的脾氣,因此來家里敲開門一句話也沒說,放下禮品就走,父親叫也不回頭,追也沒追上。于是,父親和母親商量,找一個過節的日子,買了同等價值的禮物也到他家去看望。那位下屬見父親親自來看望他,更加感動,又找了機會再次到家里來登門感謝,父親再以同等價值的禮物回敬對方,這樣你來我往一直持續了好幾年。父親以此為例告訴我們:“來而不往非禮也!這是《禮記》的經典名句,一定切記。”還專門告誡說:“不義之財君莫取,這是古訓,也是做人的底線。為官一任,造福四方。黨員領導干部修身養性,絕不可貪取不義之財。”
新時代黨內深化反腐敗斗爭,父親非常關注,每看到打倒一只“老虎”,或者拍到一只“蒼蠅”,父親都拍手稱快,痛斥他們這是咎由自取,活該。但也每每告誡我們千萬要引以為戒,防微杜漸,做共產黨員就要像共產黨員的樣子。每次聽到我們說在外面和朋友吃飯了,父親都要詢問有沒有吃公款,有沒有收禮送禮,聽我們說沒有,父親才放心地笑了。
親愛的父親啊!作為黨員領導干部,您高風亮節,堪為典范;作為我們母親的恩愛伴侶,您無私奉獻,真情陪伴;作為子女慈祥父親,您哺育情深,父愛如山。如今,您雖然離我們遠行,但是您的大愛依然潤澤子孫,您的大德永遠啟迪后昆。我們此生無法回報,來生我們還做您的子女,再報您的大恩!
作者簡介:
李康平,中國作協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中國鐵路作協會員。自1980年開始發表小說、散文、報告文學等文學作品200余萬字,散見于報刊雜志并獲多種獎勵。撰稿、編導《京九鐵路》《寫在雪域高原的忠誠》《拉林鐵路》等多部電視專題片;編劇電影《U57次謎案》在央視播出;著有報告文學集《中國高鐵時代的新生活》(中國鐵道出版社出版),長篇報告文學《風雪新天路》獲2019年第二屆全國工業題材文學作品大賽網絡人氣獎,與他人合著長篇報告文學《開拓者之歌》(中國鐵道出版社出版中),2018年起,在《中國報告文學》雜志開辟專欄《來自拉林鐵路建設一線的報告》,連續兩年多刊發系列報告文學30余篇共35萬余字。
責任編輯/盧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