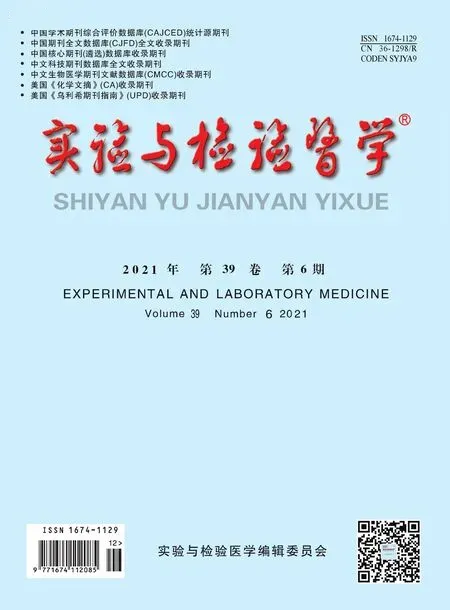非酒精性肝病患者血清中G-CSF、sTREM1、TNF-α水平和腸道菌群分布變化的關聯性分析
鄒輝鑫
(南陽市中心醫院檢驗科,河南 南陽 473000)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一種與脂代謝、胰島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等相關的臨床綜合征[1],主要病理特征為彌漫性肝細胞脂肪沉積和肝實質細胞變性,但NAFLD的發病機制目前仍未完全明確,同時其發病率近年來不斷攀升,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重要問題[2]。有報道指出[3],NAFLD與代謝綜合征有緊密聯系;近年來的研究認為不同糖代謝的NAFLD患者腸道菌群變化較為顯著[4];腫瘤壞死因子-α(Tumour necrosis factor-α,TNF-α)能促進炎性因子釋放加重肝細胞損傷;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macrophage colony factor,GM-CSF)是一種造血因子,其在血管內皮細胞受損時大量釋放,進而調控機體免疫;可溶性髓樣細胞觸發受體(Soluble triggering receptors expressedon myeloid cells,sTREM-1)則是近些年發現的感染預測因子,預測敗血癥等方面效果頗佳[5]。目前NAFLD的血清學指標與腸道菌群均有相關研究[6-7],但涉及上述指標的較為少見,基于此,本研究分析NAFLD患者血清GM-CSF、和sTREM-1、TNF-α水平和腸道菌群變化關聯性,為探明NAFLD的發病機制提供較好的理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19年6月至2021年7月于本院收治的72例NAFLD患者為病例組,并根據不同預后情況將病例組分為預后不佳組和預后良好組,另外征集同期于本院體檢健康者30例作為對照組,病例組男45例、女27例,平均年齡(48.57±10.38)歲,體質指數(24.02±3.45)kg/m2;對照組男19例、女11例,平均年齡(49.12±9.79)歲,體質指數(23.34±2.76)kg/m2。兩組組間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獲得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
納入標準:⑴符合臨床對NAFLD的診斷標準[8],經影像學檢測,肝臟近場回聲增強,遠場回聲減弱,且肝臟管道結構顯示模糊;⑵患者對研究了解知情。排除標準:⑴酒精性脂肪性肝病;⑵合并心、肺、腎等臟器患嚴重疾病;⑶近期服用腸動力藥、微生物制劑;⑷因病毒性肝炎、腎功能不全、血液疾病等導致脂肪肝;⑸妊娠、孕期婦女;⑹既往有胃腸道病史。
1.2 方法 ⑴血清標本檢測:入組后清晨采集所有受試者的靜脈血標本,靜置1 h,使用低速離心機(中科中佳,SC-3616)于室溫中1500 r/min離心20min,取上清裝于EP管,送至低溫冰箱封存,融凍一天后樣本未出現溶血、絮狀現象,外觀無異常,進行下一步檢測。采用酶聯免疫法檢測血清GM-CSF、sTREM-1、TNF-α水平,試劑盒購自北京中杉金橋生物公司,檢測步驟按照說明書進行操作。同時使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測定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PG),空腹胰島素(Fasting insulin,FINS),另外用胰島素抵抗指數(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HOMA-IR)表示胰島素敏感性和IR程度,根據計算公式HOMA-IR=FPG×FINS/22.5;⑵腸道菌群檢測:入組后采集所有受試者的糞便0.5 g,制成標本送檢,用連續稀釋法稀釋成10~1至10~7后,依照各菌種的正常菌數范圍進行細菌培養,厭氧型置入厭氧盒內在恒溫箱培育72 h,需氧型置入有氧環境中,在恒溫箱培育24 h,統計培養基上的菌落數,檢測雙歧桿菌、酵母菌、腸桿菌、腸球菌的菌群數量,轉化成對數值(LgCFU/g),來定量表示腸道菌群的水平,并計算雙歧桿菌/腸桿菌比值(B/E);⑶腸道菌群Alpha多樣性指數:所有受試者入組后行腸鏡檢測,在距肛門20 cm處提取1塊黏膜組織進行檢測,使用細菌基因組DNA試劑盒(上海恒遠生物科技公司),應用Novaseq PE250(美國Illumina公司)進行上機質檢、測序,根據說明書操作步驟,提取黏膜組織DNA,使用Uparse軟件對測序得到的有效序列進行分類[9],得到分類單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OTU),使用Alpha分析對腸道菌群多樣性進行觀察,包括Chao1、Shannon、Simpson指數,Chao1指數估計樣本所含OTU的總數,Shannon指數和Simpson指數估計微生物樣本群落的多樣性。
1.3 統計學方法 應用IBM SPSSStatistics 24.0軟件行統計學分析,對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采用獨立t檢驗;計數資料使用率(%)表示,行χ2檢驗,采用Spearman法分析腸道菌群水平與血清GM-CSF、sTREM-1、TNF-α水平的相關性,采用ROC曲線分析血清GM-CSF、sTREM-1、TNF-α對NAFLD預后的評估效能,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腸道菌群變化比較 結果顯示,病例組的雙歧桿菌、酵母菌數目和B/E值顯著低于對照組,腸桿菌、腸球菌數目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兩組腸道菌群變化比較(LgCFU/g,±s)

表1 兩組腸道菌群變化比較(LgCFU/g,±s)
?
2.2 兩組腸道菌群多樣性比較 結果顯示,兩組的Chao1指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病例組的Shannon指數低于對照組,而Simpson指數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腸道菌群多樣性比較(±s)

表2 兩組腸道菌群多樣性比較(±s)
?
2.3 兩組血清GM-CSF、sTREM-1、TNF-α水平比較 結果顯示,病例組的GM-CSF、sTREM-1以及TNF-α水平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兩組血清GM-CSF、sTREM-1、TNF-α水平比較(±s)

表3 兩組血清GM-CSF、sTREM-1、TNF-α水平比較(±s)
?
2.4 兩組其他生化指標比較 結果顯示,病例組的FPG、FINS以及HOMA-IR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兩組其他生化指標比較(±s)

表4 兩組其他生化指標比較(±s)
?
2.5 NAFLD患者GM-CSF、sTREM-1、TNF-α水平與B/E相關性分析結果 采用Spearman法分析腸道菌群水平與血清GM-CSF、sTREM-1、TNF-α水平的相關性,結果顯示,GM-CSF、sTREM-1、TNFα、HOMA-IR與B/E呈負相關(P<0.05),見表5。

表5 NAFLD患者GM-CSF、sTREM-1、TNF-α水平與B/E相關性分析結果
2.6 不同預后情況NAFLD患者GM-CSF、sTREM-1、TNF-α水平比較 結果顯示,預后不佳組的GM-CSF、sTREM-1以及TNF-α水平均高于預后良好組(P<0.05),見表6。
表6 不同預后情況NAFLD患者GM-CSF、sTREM-1、TNF-α水平比較(±s)

表6 不同預后情況NAFLD患者GM-CSF、sTREM-1、TNF-α水平比較(±s)
?
2.7 GM-CSF、sTREM-1、TNF-α水平對NAFLD患者預后的評估價值 結果顯示,采用ROC曲線分析GM-CSF、sTREM-1、TNF-α對大腸癌圍術期感染患者預后的評估價值,GM-CSF、sTREM-1、TNF-α評估NAFLD患者預后的AUC為0.811(95%CI:0.701~0.894)、0.800(95%CI:0.689~0.885)、0.808(95%CI:0.699~0.892),TNF-α敏感度最好為75.00%,GM-CSF特異度較高為86.36%,見表7、圖1。

表7 GM-CSF、sTREM-1、TNF-α水平對NAFLD患者預后的評估價值

圖1 GM-CSF、sTREM-1、TNF-α評估NAFLD患者預后的ROC曲線
3 討論
NAFLD被認為是一種與IR、遺傳易感性等關系緊密的應激性肝受損,較早前已成為歐洲國家較常見的肝病原因,近年來發病率更是顯示上升的趨勢。NAFLD的臨床危險因素也呈現多樣化的特點[10],如肥胖、高血壓、糖尿病和代謝綜合征等,部分NAFLD患者可能發展成為肝硬化,然而由于NAFLD臨床癥狀無明顯特點,大多數患者易忽視進而造成漏診、誤診。同時由于該病與代謝綜合征等關聯緊密,導致患者機體代謝紊亂,造成全身性危害,許多患者發展為肝硬化之前可能已病死于心血管疾病[11]。目前臨床診斷NAFLD的金標準仍然是肝組織病理活檢,可囿于其創傷性,無法全面推廣,而近些年的無創評估NAFLD病情的工具,均無法取代病理活檢來檢測患者肝纖維化程度,尋找評估NAFLD的血清、生化指標已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點[12]。本研究基于此背景進行研究,發現NAFLD患者腸道菌群變化和血清細胞因子GM-CSF、sTREM-1、TNF-α水平存在較好相關性,且三者水平變化與腸道菌群失衡共同作用,可能導致NAFLD的產生,這一發現在近年來NAFLD的相關研究中并不多見,可為研究創新之處,現報告如下。
腸道菌群棲息在人體腸道內的微生物群落,種類多、數量大。人體腸道內含有大量細菌,而不同階段和環境,腸道菌群數量都有不同的變化,但對于健康機體而言,腸道菌群始終保持著動態平衡。本研究結果顯示,病例組的雙歧桿菌、酵母菌數目和B/E值顯著低于對照組,腸桿菌、腸球菌數目顯著高于對照組,提示相比常人,NAFLD患者的腸道菌群明顯失調。分析原因,可能是NAFLD患者因肝病變和膽汁異常分泌,腸道內pH失調,結合型膽汁酸抑制腸道外細菌的作用降低,繼而導致體內腸道菌群失衡[13];另外由于NAFLD與代謝綜合征的密切關系,可能引發患者消化道功能異常,胃腸道動力不足、蠕動減少,腸道清除功能降低,導致大量細菌過度繁殖,也可能造成菌群失衡。另一方面,研究結果還發現病例組的Shannon指數低于對照組,而Simpson指數高于對照組。Shannon指數代表菌群多樣性,Simpson指數代表菌群豐富度,Shannon指數值越大,表示多樣性越好,Simpson指數越大,種類越單一,本結果提示NAFLD患者的腸道菌群多樣性較常人明顯減少。聯系上述腸道菌群數目的結果來看,NAFLD的腸道菌群失衡、多樣性減少可能與NAFLD的發病有重要關聯[14]。
此外,結果顯示,病例組的GM-CSF、sTREM-1、TNF-α水平和FPG、FINS、HOMA-IR均高于對照組,說明NAFLD患者相比常人,體內炎癥反應較明顯,并已出現血糖代謝紊亂和IR現象。造成這一現象,推測原因可能是腸道菌群失調,導致腸道通透性增加,促進細菌移動,激活細胞免疫反應,從而加重炎癥反應。另一方面,研究結果表明GM-CSF、sTREM-1、TNF-α、HOMA-IR與B/E值均呈負相關,B/E值代表厭氧菌抑制致病菌定值腸道的能力,可全面地反映腸道菌群變化情況,因而上述結果提示腸道菌群的失調可能與GM-CSF、TNF-α的水平高低和HOMA-IR相關,考慮到GM-CSF和TNF-α的功能,分析可能是肝細胞受損時促進GM-CSF大量釋放,激活免疫反應,加重肝臟病變,而TNF-α的上升代表體內炎癥反應嚴重,細胞浸潤較深,破壞腸黏膜屏障,進而腸道菌群失衡,同樣導致肝臟病變發生,形成惡性循環[15]。至于sTREM-1與腸道菌群失衡的關系,推測是sTREM-1誘導級聯式的炎癥反應導致腸黏膜受損,引發菌群失衡,具體作用機制尚需要更深入地研究予以闡明。
最后,研究發現,預后不佳組患者的GM-CSF、sTREM-1、TNF-α水平高于預后良好組,同時ROC曲線分析顯示GM-CSF、sTREM-1、TNF-α評估NAFLD患者預后的AUC為0.811、0.800、0.808,提示GM-CSF、sTREM-1、TNF-α具 有 較 好 評 估NAFLD預后的效能;亦有研究表明[16-17],NAFLD的預后存在多種危險因子,其中包括遺傳因素、基礎疾病、手術等,這些因素皆有可能對血清標志物GM-CSF、sTREM-1、TNF-α的評估效能造成一定影響,因此若臨床將該指標納入評估指標中,仍需聯系實際因素綜合進行考慮。
綜上,NAFLD患者腸道菌群失衡較為明顯,且GM-CSF、sTREM-1、TNF-α水平異常上調,腸道菌群變化與GM-CSF、sTREM-1、TNF-α水平有重要相關,可能共同作用導致NAFLD的發生,另外GM-CSF、sTREM-1、TNF-α能有效評估NAFLD預后。同時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樣本偏少,并且未對NAFLD病情有效分類以分析不同病情患者的腸道菌群和血清學指標的聯系,這些有待于之后擴大樣本量,行全面性的研究,予以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