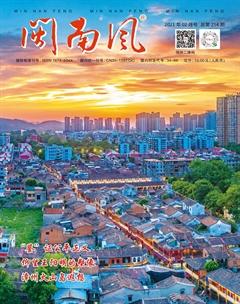初讀《林繼中文集》
陳尚君
認識林繼中教授逾三十年,許多專著都讀過,佩服他是一位兼做文獻與鑒賞,講究理論與實踐的優秀學者。這次《林繼中文集》結集出版,煌煌八冊,內容豐富,多半為首次見到,對林先生的學術成就又有許多新的認識。
記得認識林先生后不久,他約我為他的新著《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寫書評,且讀到與此書相關的一些文獻,知道該書是他在蕭滌非先生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初覺這樣的學位論文很特別,不是個人的專著,而是宋人一部殘佚杜詩注本的覆原,論述部分僅書首部分數萬字。沉下心來讀,可以體會此一工作意義重大。宋人注杜,由九家而百家、千家,雖存宋本多種,然個人注本幾無所見。趙次公年輩甚早,是最初作杜詩全解的幾家之一,后集注本行而單注本廢,學人看不到宋人注杜起點的面貌。不幸之幸是,趙注原本之丁、戊、己三帙,即后半部,居然有二殘本保存,一為明前期鈔本,存北京圖書館;二為前本之傳鈔本,存成都杜甫草堂。最早介紹趙書有存的是四川師院雷履平先生,林先生繼起而校輯覆原,既據二鈔本殘帙精心校訂,又據宋以后注杜群書輯錄不存之前三帙。這一工作極其繁復,學術要求很高,其學術史意義絕不亞于任何專著。因趙書之刊布,我們可以看清宋人注杜的起點水平就很高,趙次公居功至偉。趙書沒有受書商的影響,故引征豐富,解說詳盡。以殘帙存趙注與九家注以后各家引趙注比較,雖精華有存,但解詩精彩及獨見處,也刪刈過甚。林輯校訂精審,貢獻巨大,學界多有好評,我當時也認為此書工作具有學術示范意義,許多失傳的古籍如果條件具備,可以因此而起死還生。
林先生是杜詩學大師蕭滌非先生的學術傳人,所著《杜詩學論藪》收錄了他研讀杜詩的一批力作。宏觀研究杜詩者,如《論杜甫“集大成”的情感本體》,指出杜詩能保持人性的本真,古人叫真性情,今人強調心理本體,情感本體,“真性情就是能體現人性本真的性情”,抓住了杜詩成就的關鍵。《杜甫——由雅入俗的拓荒者》也極其有識,揭示杜詩從高華雅逸的貴族氣派中走出,表達平易近人的世俗風度,這一轉變直接影響了中唐詩人的審美趣味,成為唐宋轉型的分水嶺。《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是杜詩單篇研究的難得力作。錢謙益注此篇,借他人之語自譽“鑿開鴻蒙,手洗日月,當大書特書,昭揭萬世”,林文則以兩萬多字的篇幅,先討論此詩之作年在干元元年春,再結合此時朝廷內外的政治角力與軍事進退,從新的語境中探討杜詩的意旨,并對仇兆鰲、浦起龍的發揮一并加以討論,其中涉及玄、肅父子間的矛盾,由此而引出玄宗舊臣與靈武新貴的沖突,說明錢注之識見與發明,也指出他的偏見與誤失,更從全部杜詩考察的立場,說明寫此詩時是杜甫對肅宗期望值最高的節點,其后一路下跌。以詳盡的文獻解讀為起點,從歷史人事的大背景,結合詩人的經歷,運用西方各種現代手段,對錢說既不盲從,也不輕棄,客觀冷靜地理清謎團,為學術論文之優勝之作。我對《詩心驅史筆——杜甫<八哀詩>討論》一篇也很有興趣,因為本師朱東潤先生早年從傳記文學立場,表彰過此組詩之價值。林文從創格、傷時、繁簡、詩史、詩心等角度,全面討論此組詩的價值,對前人之誤失多有討論,頗有新見。
《文集》中所收《文化建構文學史綱》一書,陳伯海先生與趙昌平先生作序推薦,出版時影響很大。承林先生賜書,當時就有機會讀到。此書以中唐至北宋文學研究為中心,用西方文化建構學理論重新考察文學之種種變化,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如以中唐劃分魏晉至北宋文學發展為兩大塊,中唐后雅俗文學的交流態勢,魏晉至盛唐文人心路歷程的文化因素,以詩意化追求與詩性思維兩個層次來考察情志與語言的轉換機制。與上世紀八十年代受西潮影響空泛的探討新方法之諸論著有很大不同,此著既以文學為本位,又充分吸取文史各界的研究成果,涉及士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兩稅法與市井文化、黨爭與士人的生存空間、以詩取士與世俗地主的知識化等復雜問題,也關注雅俗之爭的社會背景、雅俗回旋的文學表現、儒學轉向與倫理入主文學等前沿課題。由于飽讀文本,兼涉文史,視野獨特,體會深切,這部著作確實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無論贊同與否,都無法回避此書提出的問題。我特別贊同趙昌平先生序中所說,本書顯示作者不隨波逐流的學術品格,表達獨立特行的學術追求。趙序居然寫到對哪些論述他不贊成,恰好印證了彼此的純粹與真誠。
《文集》所收幾種選本,我是第一次見到。其中《中晚唐小品文選》,似乎前此并沒有同類選本。其中特別以韓柳為界,可以作韓柳同時或以后的古文發展史來讀。許多作者前人未有論列,更遑論選注,非通檢通讀《全唐文》,仔細審讀體會,難以臻此。有關杜詩的兩種選本,篇目有些重合,是因不同需求而分別編選不可避免的事。仔細閱讀,則解說與批注之輕重繁略各有異同,簡明中能得其要旨,解說能傳達精神。我最贊賞的是《杜詩菁華》中所選的每一首詩,在解題說明寫作的時間、地點與詩旨,注釋釋讀疑難,研析點評技巧與詩心,更為每首詩作了語譯。語譯不是改寫為白話文,而是每首詩都寫成語體的現代詩。這樣做很不討巧,很容易出錯,要傳達杜詩的精氣神更難。抽讀了一些,居然都做得很妥帖,真不容易。舉一首為例。杜甫《題壁畫馬歌》: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騮,欻見騏驎出東壁。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林譯: “韋侯遠行來別我,知我最愛其畫世無敵。戲拈禿筆一揮就,剎時駿馬出東壁。一匹吃草一匹嘶,立看千里蹄下失。當此亂世哪得此,能與我輩共生死。”喜歡杜詩且有較好閱讀能力的人可能覺得譯詩不如原作,這自難免,就如同翻譯西方名著很難傳達西方語言中機趣與精神。但對中等文化程度的讀者來說,林譯很有助于理解杜詩。今譯僅增加兩個字,且非逐字對譯,而是傳達真意,如譯“有所適”為“將遠行”,理解 “驊騮”“ 騏驎”皆指駿馬,省出字來將“掃”字譯成“一揮就”,末兩句的翻譯尤見恰當。難譯的是“坐看千里當霜蹄”,以“坐看”譯為“立看”,當然很好,但“千里當霜蹄”,原意是說有此好馬,千里之遙不難到達,批注說清楚與“所向無空闊”意同,但限定字數之文白對譯,雖還有些文言余味,但似乎又只能如此譯。書中有多首長篇排律之今譯,精彩紛呈,這里無法展開討論。
初讀《林繼中文集》,最大的感慨是時間推移,光陰如流,中國社會轉型后走上學術道路的一批學者,現在也到了總結成就的時候。林先生較我年長許多,但因特殊原因,我與林先生還能算同一代人。我們的師長大多誕生在清末民初,經歷了內外戰爭的顛沛流離,經歷了鼎革與變動,始終堅持學術與教育,取得杰出的成就,讓傳統學術之火在經歷千年未遇之大變后還能夠延傳下來。與前一代相比,如林先生在大學畢業后有很長時間遠離學術,如我,還未完成啟蒙就曾務農八年。當我們有機會重新回到學校,特別珍惜人生的機遇,特別勤奮地追趕前輩,希冀追回失去的歲月。我從林先生的著作中,能夠體會到他的學術思考的宏大深刻,也能體會從事學術研究的急迫感和責任感。煌煌八冊擺在面前,還應該加上前面說到的《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那就是十多冊,在長期擔任行政職務之余,能有如此成就,實在不容易。一代有一代的學術,我很不贊成大師遠去、再無來者的說法,但也承認我們這一代具有過渡傳承的特點。就此種意義來說,我們尊重前輩,也不妄自菲薄,我們很好地接續了前輩的托付,并使之發揚光大,取得各自的成就。林先生是這一代學者中的杰出代表,值得我們學習。
(作者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