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獲得茅盾文學獎后首部長篇問世 梁曉聲:我愛生活 我愛生命
王雅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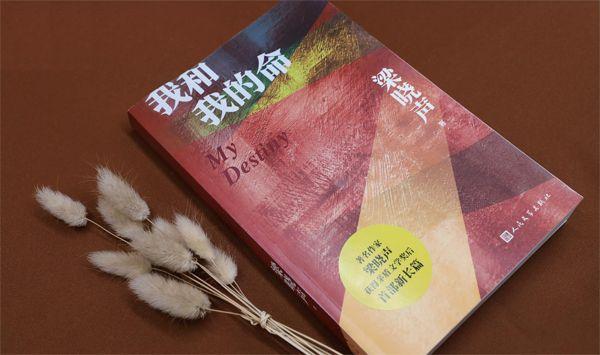
梁曉聲
當代著名作家,“知青文學”的代表人物。曾任北京電影制片廠編輯、編劇,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教授。2012年6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親》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今夜有暴風雪》獲全國中篇小說獎并收入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經典作品文庫;《雪城》收入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部優秀長篇小說典藏。長篇小說《人世間》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我愛生活,我愛生命。
我平凡,我普通,我做得最成功的事就一件——我使臺灣高山茶在貴州神仙頂漫山遍嶺地生長著——“高貴紅”和“高貴綠”已打開了國際市場,頗受歡迎。
我不想否認我是一個不幸者,還不到四十歲就已做三次癌切除手術了,這當然是不幸啰。但我卻一直否認我患癌癥是被氣的——也許這符合病理學,并且符合一部分事實。然而我更愿承認是我的宿命如此。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還是從自身找原因對頭。這么想更能使自己心平氣和地面對現實,也有益于我再一次戰勝癌癥。
我不至于死在手術臺上這一點可以肯定。
術后我又能活多久?這個問題我已不再去想。當我不再去想,一不小心又成了“抗癌明星”;這是我年近四十唯一獲得的“榮譽”。我對這頂“桂冠”并不真的感到光榮,對人能否“抗癌”心存懷疑;無非就是別陷入自哀自憐的壞情緒的泥沼而已。我的體會是——當人真的能心平氣和地面對“壞命運”,連命運之神也會刮目相看。果有命運之神的話,她或他的工作不過就是電腦般的工作,是某種神秘程序的自動鎖定。即使那程序是他們參與編制的,估計也無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簽結果”。所以,對于命運之神的“工作”,我也采取“理解萬歲”的態度。可我既已是“明星”,我便也做了些“明星”該做的事——我在滬深兩地組建了癌病友網站,還主編了一份民間的刊物《與癌共舞》,頗受癌病友喜歡。
紫外燈還沒開亮,醫生護士在為手術做最后的準備。他們的動作輕得近乎無聲。誰偶爾看我一眼,眼睛便會瞇起。如果沒有口罩遮住,我會看到友愛的笑臉。我在他們心目中不太一般,他們尊敬我。
趁那短暫的時刻,我又開始思想。被全身麻醉的人其實就是“死去”,倘沒醒來,那種死法不啻是一種幸運。在大手術臺上思考,如同在生死交界處與自己對話——我思故我在嘛。不是誰都有多次這樣的機會,我珍惜。
我認為我也是幸運的。
我的養父母和我的丈夫都是享受思考的人,受他們影響我也以思考為樂。我愛思考甚于其他女人愛時裝和化妝。
我愿以后之中國,多數孩子都有我養母那樣的母親——不是指有她那種家族背景,那怎么可能?亦非指像她那樣是地方名流,這也等于是天方夜譚;而是指像她那么心地善良。這做起來易如呼吸,但是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壞人變老了”當然也意味著有人在年輕時就變壞了。
那么——孩子呢?魯迅的話“救救孩子”,亦或可改為先救父母?
我愿以后之中國,年輕人不必像我一樣,沒有當過市長的父親和是名流的母親,人生也照樣可以有安全感保駕護航。
我愿以后之中國,李娟多起來,再多起來。
中國仍有一小半人口在農村,他們正是月收入千元左右的那些同胞。已經成為城鎮人口的人中,不少昨天或前天還生活在農村——這使絕大多數中國人之“社會關系之和”復雜而不單純。
我發自內心地擁護對農村的全面扶貧。我見證了許許多多同胞的“社會關系之和”在向好的方面發生量變和質變。我見證了“青山綠水也是金山銀山”正逐步成為事實;神仙頂是那事實的一部分。我不信世上會有君子國,這使我活得不矯情;我反對“他人皆地獄”之說,這使我活得不狡猾。
我平凡,我普通,我認真做人,我足夠堅忍。我有幸福的國情、溫暖的親情、真摯的友情——人生主要的三福氣我占全了,夫復何求?我復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