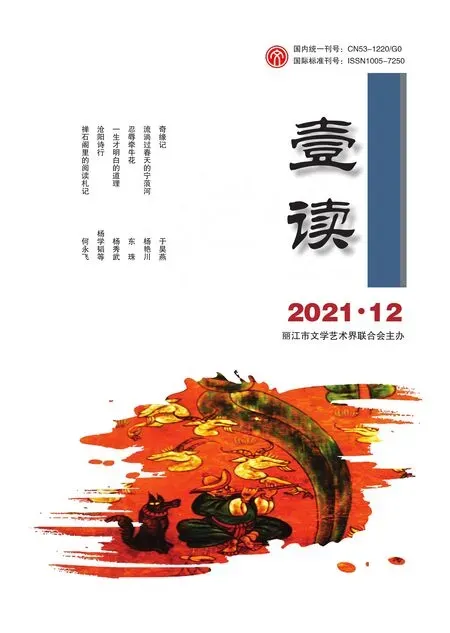一生才明白的道理(組詩)
◆楊秀武
父老鄉親圍著鋁盤爐烤火
半空中的寒冷
一年一度,包圍著故鄉
我看到父老鄉親
從衣袖里抽出寒冷的雙手
相聚,圍著鋁盤桌
親熱是宇宙的一個圓
他們說,住在高山
個個都是有地位的人
我聽到的是,春風
在他們嘴上發出聲音
像柴禾的手指
火焰很深,像眼珠和指頭
朝白色的發熱體一望
溫度就開始發芽,拔節
爐心暖著人心
人心暖著人間
我居住在城市的小區
灰白色的圓
鋼筋圍欄,是一根根
無血無肉的手指
指頭是一把把
尖利的匕首,我突然感到
另一種寒冷
山巔的儀式
重陽節那天,葉子著火
我們登上山頂
一個較真,一個恐懼
加上兩部手機
就是一個儀式
燃燒那么美,那么遠
我們走得很近
但她,總感到站在門外
顯然擔足了心
無明火把自己烤成一棵紅楓
我好像同樣站在門外
私宅里的衛生沒有打掃
陳舊的東西沒有丟掉
就像歷史沒必要保留什么
再清除什么
甚至再美化什么
我也想燃燒自己,但忍住了
人生沒必要害怕
被人戳到軟肋
我把私宅的鑰匙當作監控
安裝在她的指尖
就像一把卷尺掏空了心
一生才明白的道理
記得小時候放學
一根趕狗棍是我的同伴
一路上,打著草回家
母親正在山上割豬草
或陽光下,或月光里
母親的手變得比草柔軟
她以柔軟愛著草
就像以柔軟疼著我
我看見,母親在莊稼地里
對草一反常態
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可同樣是草啊
母親90多歲,我快70
她說我一生最大的錯誤
長在田里的時間多了
還說我很多時間
沒把自己當成草
今夜,我在老家
盛夏的老家,夜很涼
母親找出父親的一件秋衣
要我穿上,母親說
你的皺紋,嗓音,越來越像了
我感覺血,骨頭,脾氣
也越來越像父親了
我第一次,穿上父親的衣服
在母親眼里,我就是父親
我的身體里有他最好的遺址
我推開木格窗,一輪彎月
像一把槍瞄準我
母親站在我身后,仿佛
把槍搶到手里
向自己扣動扳機
手指亮起來暗下去
早上,我去探望幺叔
他正在洗臉,刷牙,反復洗手
低聲地咳嗽,自問自答
徑直走到我為他栽的幾株月季前
幺叔生怕把月季弄痛,弄臟
他的手像舌頭
手指有節奏地亮起來暗下去
花壇邊的一座山坡上
一只羊正下崽
羊模仿幺叔,用舌頭
把羊羔毛上的水慢慢舔干
瞳仁的閃亮隱藏在手指上
他一生享受的都是黑暗
誰是靠得住的人
水洗的陽光
從一棵杜鵑樹落下來
像一地鵝卵石
一個人蹲在杜鵑樹下
在鵝卵石上,刻一個人的名字
刻著刻著,鵝卵石跑了
在另一棵樹下
另外一個人也刻著名字
刻著刻著,地上寫的是同一個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