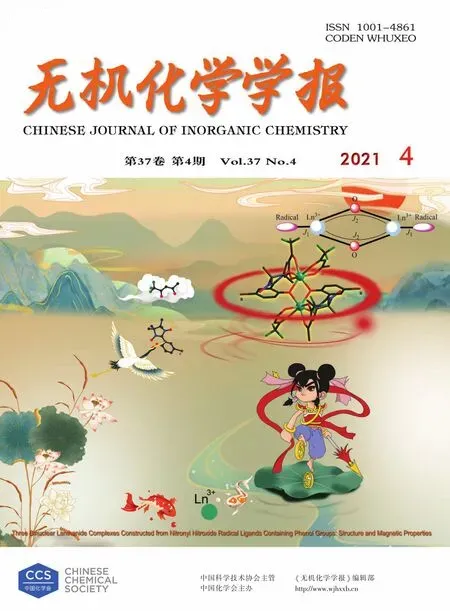MIL-53(Al)催化甲基氯硅烷的歧化機理
徐文媛 李素穎 汪 焱 程永兵 沈蒙莎 胡 林 郭贊如 廖夢垠 彭家喜 陳 曦
(華東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南昌 330013)
0 引 言
硅樹脂材料結合了無機材料和有機材料基本特性,如低表面張力、低粘度系數、高壓縮性和高透氣性,還具有優良的性能,如高低溫電阻、電氣絕緣、電阻氧化穩定性和生理惰性等[1-2],從而廣泛應用于電子、航空、紡織、建筑、醫藥等領域[3-5]。其中有機硅單體二甲基二氯硅烷(M2)是制備各種有機硅材料最重要的單體之一[6]。目前制備M2方法有很多,最常用的直接法制備M2會產生大量的副產物,如一甲基三氯硅烷(M1)和三甲基一氯硅烷(M3),而運用歧化法則能夠將M1和M3在催化劑的作用下生成M2,這樣既能提高M2的產率,也能改善環境質量[7]。
前期的實驗結果表明[8-10],ZSM-5以及經典的γ-Al2O3、η-Al2O3都在M1和M3歧化為M2的反應中表現出不錯的催化性能。深入的理論研究表明:ZSM-5的不同反應團簇(如:3T、5T、8T、7T和24T)[11-12]以及γ-Al2O3中能產生歧化活性的共同原因在于具備Al—O—H鍵,而其中的H則是關鍵[13-16]。M1和M3歧化制備M2的反應都限域在催化劑表面的這個位點發生。
金屬有機框架(MOFs)具有多孔配位聚合物結構,表面積大,因其孔徑、形態和網絡拓撲結構等特性從而具有特殊的表面功能[17]。其中MIL-53(Al)系化合物是通過無限一維的對苯二甲酸酯連接在一起形成了菱形通道,其結構是由一個單一的傳統單元組成大孔相的周期模型,這些周期模型適當的孤立群模型,具有封閉的殼層系統[15,18],并通過其三維納米尺寸通道可提供潛在的催化位點,此外還具有特定的氧化鋁團簇以及內部羥基[19]。有研究[20]指出MIL-53的催化性能強烈依賴于金屬中心,該中心可以對甲基氯硅烷中Si—Cl鍵及Si—C鍵進行解離[21]。同時本課題組研究發現MIL-53(Al)也具有Al—O—H的特征結構,與前述歧化反應的活性位結構類似,更有趣的是其關鍵的羥基—OH也是連接在MIL-53的金屬中心Al上,MIL-53(Al)的拓撲結構如圖1所示[22]。鑒于此,課題組采用密度泛函理論(DFT)中的B3LYP方法對MIL-53(Al)歧化M1和M3以制備M2的反應進行了理論研究,以此來論證類似結構具備類似催化活性的推測,并為拓展MOFs材料的催化性能提供基礎性數據,同時為后期實驗室制備真實高效的歧化催化劑提供理論支持。

圖1 MIL-53(Al)結構示意圖:(a)MIL-53(Al)孔道結構圖;(b)MIL-53(Al)基本結構圖Fig.1 Schematic drawing of MIL-53(Al):(a)pore structure of MIL-53(Al);(b)basic structural unit of MIL-53(Al)
1 計算方法
利用 DFT 中 B3LYP/6-311++G(3df,2pd)方法對反應體系進行了全優化計算[23-25]并在此基組水平上考慮了各個反應物、產物和過渡態標準生成焓和電子能量的零點能校正[26-28]。零點校正能(ZPE,kJ·mol-1)的計算公式[29]如式1所示:

其中p是分子中的鍵數,Ni是i型鍵的數目,BCi是i型鍵對零點能(ZPE)的貢獻。將M1或M3與催化劑或中間體同時建模組成反應物超分子,同時將M2、副產物(四甲基硅烷和四氯硅烷)與中間體或催化劑同時建模組成產物超分子,進行了全優化計算。所有反應物和產物超分子均找到了計算結果中的能量最小值點,同時找到了從反應物走向產物超分子結構的具有可信度的過渡態。利用振動分析確認了能量極小值點和鞍點,結果表明能量極小值點的振動頻率都為正值,鞍點的振動頻率有且僅有一個負值。最后對過渡態進行了內稟反應坐標(IRC)的計算,確定每個過渡態都能把其對應的反應物和產物連接在勢能面,進一步確認了過渡態的真實性,并推測了反應途徑的準確性[30-31]。全部計算工作均采用Gaussian09程序進行[30]。
2 結果與討論
2.1 催化劑結構
由于MIL-53(Al)真實材料的原子數目巨大,以目前的計算機模擬能力無法全部計算,通常采用量子化學方法對其局部的重復單元進行模擬。根據文獻以及劍橋晶體數據庫的數據[32-33]找到含Al的MOF材料MIL-53(Al)的結構,其晶胞大小為a=0.660 8(1)nm,b=1.667 5(3)nm,c=1.281 3(2)nm,從中截取MIL-53(Al)基礎結構模型,截斷模型時產生的懸斷鍵可用H原子飽和[34]。H原子用于飽和O原子,使MIL-53(Al)結構模型具有包含橋接羥基酸位點的棒狀結構,羥基上的H原子具有明顯的Br?nsted酸(B酸)特征(圖2)。
計算得到了Al—O的鍵長在0.173 9~0.193 6 nm范圍內,其中3個關鍵活性位的鍵長數據見圖2所示,所有鍵長數據與文獻中的實驗數據0.18~0.20 nm[35]相匹配。通過對MIL-53(Al)模型的頻率計算得到了1、2和3號位點各自的O—H伸縮振動頻率分別為3 679、3 699和3 686 cm-1,而實驗結果為3 630 cm-1[36],該計算得到的理論數據與實驗結果的相對誤差僅為1.3%~1.9%,在可接受誤差范圍內,從而證實了圖2所示模型適用于模擬具有酸性位點的MIL-53(Al)催化劑且具有催化功能結構的可信度[37-38]。通過實驗研究表明[17],由于Al元素是典型的兩性氧化物,其氧橋上的H原子確實是酸供體,進一步驗證了圖2中MIL-53(Al)模型結構的可信度。

圖2 MIL-53(Al)催化劑結構及關鍵原子之間的鍵長(nm)和鍵角(°)Fig.2 Structure of MIL-53(Al)catalyst,bond lengths(nm)and bond angles(°)among key atoms
2.2 反應通道
反應分為主、副2個通道,如圖3和4所示。以位點1為例,在主反應(Channel 1)中,MIL-53(Al)催化劑先與M3反應。由于Si—C鍵裂解的能量最低[21],此時催化劑上Al—O—H中的O1—H1鍵斷裂,H1進攻Si1—C1鍵中的C1生成CH4,其中的O1進攻Si1生成中間體Ⅰ,此為經過渡態TS1的步驟;產生的中間體Ⅰ與M3反應,M1中Si2—Cl1鍵斷裂,Si2替代Si1連接到O1上形成中間體Ⅱ,同時Si1—O1鍵解離,Si1與M1中Cl1靠攏并成鍵形成主產物M2,此為經過渡態TS2的步驟;中間體Ⅱ很容易捕捉游離在大量催化劑床層中的CH4,Ⅱ中的O1進攻甲烷中的H1,兩者最后成鍵使得催化劑得以還原,同時C1與Si2逐漸靠攏成鍵并生成主產物M2,此為經過渡態TS3的步驟。在副反應(Channel 2)中,催化劑上Al—O—H中的O1—H1鍵斷裂,H1進攻C2生成CH4,O1進攻Si2生成中間體Ⅲ,此為經過渡態TS4的步驟;Ⅲ與M3反應,M3中Si1—Cl2斷裂,Si1替代Si2連接到O1上形成中間體Ⅳ,同時Ⅲ中的Si2—O1鍵解離,Si2與Cl2靠攏并成鍵形成副產物SiCl4,此為經過渡態TS5的步驟;最后,Ⅳ與CH4反應,O1進攻H1,同時C2與Si1成鍵并生成副產物Si(CH3)4和還原的催化劑,此為經過渡態TS6的步驟。其他2個位點的反應流程和關鍵原子編號和位點1類似。由圖4可知,參與反應的活性中心為Al—O—H鍵上提供的H,是明顯的B酸催化活性中心。

圖3 MIL-53(Al)催化歧化甲基氯硅烷的反應方程式Fig.3 Reaction equation for methylchlorosilanes disproportionation catalyzed by MIL-53(Al)

圖4 MIL-53(Al)(位點1)催化反應流程圖及關鍵原子編號Fig.4 Reaction flow chart and key atomic numbers of MIL-53(Al)(Site 1)
2.3 振動分析
MIL-53(Al)催化劑的1、2和3號位中各步反應的過渡態來自Ox(x=1~3,分別對應1~3號活性位點,下同)、Hx(x=1~3)、Si1、Si2、Cl1、Cl2、C1和C2這8個原子之間的鍵長伸縮變化。在催化反應過程中,斷鍵與成鍵都伴隨新物質的生成,足以證明其是高度一致的。為證實計算找到的過渡態TSn(n=1~6)結構的準確性,運用虛頻振動模式計算。過渡態形成是要具有適當空隙空間尺寸,MIL-53(Al)催化劑為三維通道,不提供氧化位點,有利于穩定反應的過渡態[35,39],計算所得反應物以及生成物的虛頻皆為正值[40],而過渡態的虛頻有且只有一個負值。
根據圖5,以TS1過程為例:MIL-53(Al)催化劑與三甲基氯硅烷反應時(藍色箭頭所示),M3中的Si1—C1鍵與催化劑1號位點中O1—H1鍵逐漸斷裂,質子酸性強的H1原子漸漸靠近M3中的C1原子并鍵合,形成甲烷;而O1原子則與Si1原子裸露出來并逐漸靠近成鍵,最終生成產物P1。再看TS1中關鍵原子的另一個振動方向(褐色箭頭所示),C1原子逐漸靠近Si1原子并與之鍵合;O1原子與H1原子相互靠近并鍵連,形成反應物R1。關鍵原子之間的縱向或徑向拉伸振動是等效的,證明了計算得到的過渡態結構是正確的。從圖亦可知催化活性中心為B酸H中心,H首先參與歧化反應過程,生成對應的中間體和產物,最后經反應通道Channel 1和Channel 2最終回到了催化劑,既實現了催化劑的復原,又實現了主產物和副產物的生成,和前述反應路徑是對應的,證明了反應機理的可靠性。

圖5 過渡態虛振模式圖Fig.5 Virtual vibration modes of transition states
2.4 IRC計算
為了進一步驗證過渡態結構的準確度,確定反應機理的可信度,對反應各階段過渡態進行了Forward和Reverse兩個方向的IRC計算。MIL-53(Al)(1、2和3號活性位)催化劑每一個步驟反應關鍵原子沿IRC的變化趨勢圖如圖6所示。其中橫坐標S為IRC的量度,單位為amu1/2·Bohr,且橫坐標S的正值與負值分別代表了產物和反應物區域。這表示在S=0處時為過渡狀態。TS1和TS4中催化劑Ox—Hx(x=1~3)鍵斷裂,用于提供B酸H參與反應,在TS3和TS6中該鍵又形成,使得催化劑還原。在TS1和TS4中,硅烷Si1—C1、Si2—C2鍵均斷裂,提供了Si基團接枝到催化劑中,甲基被H暫時保護。在TS2和TS5中,反應物硅烷Si2—Cl1、Si1—Cl2鍵斷裂,用于提供Cl并接枝到中間體的Si原子上以生成主副產物;TS2和TS5中的2組Si—Cl鍵,一組斷鍵一組成鍵,即表明了硅烷反應物中的Cl基團在此時通過催化劑形成的中間體進行了互換。所有的Si—O鍵中Si來自于反應物硅烷,O來自于催化劑,在TS1和TS4中均為成鍵趨勢,說明催化劑活化了硅烷,并接枝上了Si基團;而在TS2和TS5中均有2組Si—O鍵,一組斷鍵一組成鍵,即表明了硅烷反應物中的Si基團在此時通過催化劑形成的中間體進行了互換,與前述Cl互換對應。最后在TS3和TS6中上述Si—O鍵斷裂,同時Ox、Hx以及Si、C重新各自成鍵,催化劑還原并使Si基團與保護的甲基結合回歸主副產物中。說明催化劑(1、2和3號位)的Ox—Hx鍵能提供B酸H并轉移Si基團,使得歧化反應最終得以實現。通過分析數據和趨勢,反應各階段從反應物開始經由過渡態到產物,關鍵原子間距變化趨勢與振動頻率分析是一致的。IRC計算的結果進一步證明了反應物、過渡態和產物結構是可靠的,反應機理是可信的。

圖6 關鍵原子沿IRC變化趨勢Fig.6 Variation trends of key atoms along IRC
2.5 反應的活化能
MIL-53(Al)催化的歧化反應能線圖如圖7所示。1~3號活性位發生的主反應速控步(RDS)的活化能分別為 157.15、155.31 和 123.44 kJ·mol-1,各活性位點副反應速控步的活化能分別為206.48、214.87和166.07 kJ·mol-1。所有反應位點發生主反應的活化能均比副反應活化能更低,說明在對應活性位點反應中,主反應的競爭力更強,使反應均能向生成M2的方向進行,催化效果良好。這與前述反應機理的推測是一致的,生成M2的Channel 1確實是主反應通道,再次證明了反應機理的可靠性。

圖7 MIL-53(Al)催化劑反應能線圖Fig.7 Reaction energy diagram of MIL-53(Al)catalyst
對催化劑不同活性位點主、副反應速控步的活化能分析見圖8。雖然所有位點均具有良好的催化能力,但由圖表中數據可以看出,3個位點催化發生主反應的可能性排序為3>1>2。3號活性位主反應速控步活化能對比其他位點的主反應速控步活化能,數值最低,因此該位點發生主反應的競爭優勢最大,反應更容易進行。3個位點的活性差異也可能來源于MIL-53(Al)原始結構[15]中不同的配位環境,其中1和2號活性位為二配位,3號活性位為三配位。

圖8 不同活性位點主、副反應速控步的活化能(kJ·mol-1)Fig.8 Activation energy(kJ·mol-1)of RDS in main and side reactions at different active sites
3 結 論
采用 DFT 在 B3LYP/6-311++G(3df,2pd)水平上計算了MIL-53(Al)催化歧化一甲基三氯硅烷和三甲基一氯硅烷以制備二甲基二氯硅烷的反應,得到結論如下:
(1)MIL-53(Al)上有3個活性位點,其催化中心為Al—O—H中的B酸H。
(2)歧化反應分為2個通道進行,3個活性位點的Channel 1主反應通道速控步的活化能分別為157.15、155.31和123.44 kJ·mol-1,Channel 2副反應速控步的活化能分別為206.48、214.87和166.07 kJ·mol-1。3個位點因配位環境的差異帶來的催化活性排序為3>1>2。
(3)催化劑結構和反應機理是可信的,反應通道討論、能量分析、過渡態虛振模式、IRC計算、關鍵原子間距的變化等結果均與機理相符。
- 無機化學學報的其它文章
- Lamellar-Smectic Polyoxometalate Liquid Crystal Encapsulated by Branched Bola-Form Amphiphiles
- Synthesis,Structure and Catalytic Properties of Mn(Ⅱ)Coordination Polymer through in Situ Ligand Reaction
- Synthesis,Structure,Magnetic and Photocatalytic Properties of Nickel(Ⅱ)Coordination Polymer Based on 1-(3,5-Dicarboxybenzyl)-1H-pyrazole-3,5-dicarboxylic Acid Ligand
- Flexible Bis(imidazole)-Based Ligands Oriented Co(Ⅱ)-Glutarate Metal-Organic Frameworks:Syntheses,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 以四乙基氫氧化銨為模板并通過轉晶法合成高硅鋁比的SSZ-13沸石分子篩
- Fe物種改性海膽狀Nb2O5光催化降解類吩噻嗪染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