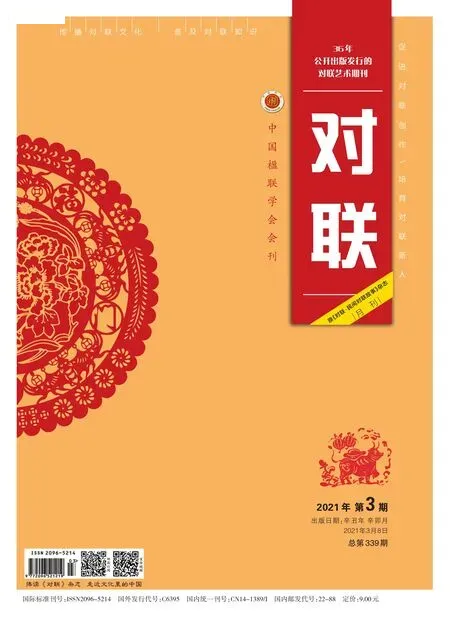論李白對古代詩詞月意象『思鄉(xiāng)懷人』內(nèi)涵的模塑
□李詩白
李白詩抒情意象極為豐富,而尤以『月』意象為最多。郁賢皓《李太白全集校注》收錄詩人傳世之詩一千余首,吟月、詠月,攸關(guān)明月的就有近四百首。詩人與月水乳交融,『月』這一萬古長青的意象自始至終貫穿于他的生命,如燈塔一般指引著詩人的人生,照亮詩人之詩,乃至整座中國古代詩歌的殿堂。明月即是詩人李白的化身,也是『詩仙』神作的精魄。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荀子·樂論》)詩亦如此。⑴月意象至于李白,才真正有了(特定的)情感,附著魂魄。至于李白之詩,才更加善人心,感人深,移風易俗,起到化人、治生之象。『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王建《十五夜望月》)歷代詩詞中的月意象,以『思鄉(xiāng)懷人』最為典型。這不僅與『中秋』這一歷史傳統(tǒng)有關(guān),而且與詩歌的抒情性和模塑作用不可分割。漢魏以后,這種悠久的心理體驗,與時間一道沉積,直至大唐李白以『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等句,直指『思鄉(xiāng)懷人』。將『暗示』性象征意義的面紗徹底揭開,成為人人熟知的公知象征。這種意義從此全面貫穿于整個中國文學史。
一、中國古代詩詞中的月意象
《莊子·天道》曰:『語之所貴者,意也。』⑵作為古中國首創(chuàng)的一個審美概念和詩學理論的一大重要范疇,『意象』的源出最早可追溯到《周易·系辭》。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曰:『圣人立象以盡意。』⑶因此,意象:古義應為『表意之象』。最早以文藝視角提及意象的是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神思》篇,唐代『意象』已較多地進入各家詩學理論,在兩宋得以廣泛使用。
月意象是中國古典詩歌最常用常見的物象之一,煌煌照亮了歷代詩者的『窮途墨路』《說文》解『月』為『大(太)陰之象』。⑷古代廣有月的傳說,在蔚為大觀的古詩文中,也保留著大量關(guān)于月的神話。如屈原、李白、杜甫、李商隱、蘇軾、《淮南子·覽冥訓》《酉陽雜俎》等皆有所作所載。明月以其神奇美好、浪漫純貞,及富于陰晴圓缺變幻的特質(zhì)予以詩者無窮無盡的憧憬與理想。在亙古長存的月亮身上,歷代文人騷客都曾寄托了無數(shù)天馬行空的藝術(shù)聯(lián)想。時至今日,詩人與明月互贈的佳麗詞句,存量之豐富,內(nèi)涵之深廣,無法言喻。早在《詩經(jīng)》時代,明月已經(jīng)走進詩人的視閾,《詩經(jīng)·月出》篇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等秀美之辭。可以說,這一輪明月照徹了古今詩壇,成為中國詩詞恒久的感情源泉與藝術(shù)化身,古往今來,其比喻造句之巧,運用者之眾,使用頻率之高,橫槊歷史之久,涵蓋層面之廣,涉及領(lǐng)域之多,表情達意之深,象征內(nèi)涵之富,皆其它山水風云、花鳥蟲魚等景物無可比擬。
在中國文學發(fā)展途中,明月帶給文學史的佳作多如牛毛,數(shù)不勝數(shù)。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曹植《七哀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李白《靜夜思》)『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杜甫《月夜憶舍弟》)『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蘇軾《水調(diào)歌頭》等等,皆為后世廣為流傳、效仿之作。在古代,詩人眼中的月有著深厚多樣的文化傳統(tǒng)和人文色彩。月意象的所指,既是詩人文思體物的凝結(jié),又是物象本身的延伸、拓寬與升華。在不同的意象組合中,月意象往往呈現(xiàn)出別樣的風韻,寄寓隨物賦形的情義。
這里,我們對李白詩歌中的月意象進行一番梳理。
二、『思鄉(xiāng)』內(nèi)涵的模塑
劉勰《文心雕龍·知音》曰:『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fā)。』⑸靜寂之夜,皓月當空,常常引起游子的思鄉(xiāng)之情,喚起詩人的懷遠之念。無論旅愁、鄉(xiāng)思,詩人們愁腸百結(jié),纖緒萬端,剪不斷,理還亂。常于月夜下徘徊蹀躞,無從排遣。月亮在愁眉緊鎖的詩人眼中,成色蒼白,清光慘淡,步履遲遲,言外之意甚豐,仿佛在作超負荷運行。尤其在唐詩中的『愁月』,一貫顯得情味豐富,細膩多姿。
李白以一首近乎白話的樂府詩《靜夜思》,道出望月思鄉(xiāng)之深情,『神人以和』。(《尚書·堯典》)郁賢皓注曰:『中國古代詩歌向有月夜思鄉(xiāng)思親友的傳統(tǒng)。』《靜夜思》『完美地表現(xiàn)了旅人思鄉(xiāng)的普遍性主題』,『此詩永遠激動人心』。⑹而評論之間的一『直』一『率』,直接沖破了《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曹植《雜詩二首》的『月』與『思鄉(xiāng)』之間的隔膜。詩人在無意識之間,對中國古代詩詞中的『月意象』的『思鄉(xiāng)』內(nèi)涵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的定義。有學者評析云,『李白有一類作品,信口而成,看似不求工卻無不工者』,《靜夜思》便如是。『游子因﹁看﹂而生﹁疑﹂,又因﹁疑﹂而﹁舉頭﹂,最終以﹁舉頭﹂所見之月,而生鄉(xiāng)思之情』。⑺另一曲《關(guān)山月》:『明月出天山,……思歸多苦顏』亦是如此,這種直指,深刻影響著后世遷客騷人對月意象的使用。
如杜甫的『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白居易的『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xiāng)心五處同』,溫庭筠的『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王安石的『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床』等,無一不是詩人的萬千思鄉(xiāng)念人之緒。『在中國文學傳統(tǒng)中,抒情傳統(tǒng)是一個歷史的存在』。⑻思鄉(xiāng)者們,離家千里,天各一方,共當明月之時,明月當然是抒情的最佳對象,也是最好的故鄉(xiāng)記憶。滿腔相思之情直接溢于文辭之間。在這些騷人的筆下,已難以分清究竟是月有濃情還是人有深情。而月到中秋分外明,月在此時必然要擔起思歸望遠的天職。每當詩人舉頭望月,鄉(xiāng)思之情在詩的經(jīng)驗中冉冉升起。因此,無論此時詩人是在浪跡天涯、漂泊江湖,還是客居異鄉(xiāng)、寄人籬下,明月返照『鄉(xiāng)思』成詩的過程,突破了詩人與讀者之間因生命背景各異、生活經(jīng)驗差異而產(chǎn)生的感情隔膜。在詩人的詩中,月亮已不再是純客觀的物象,當各種各樣的情緒統(tǒng)統(tǒng)堆積在『月』肩上時,月已是不折不扣的『人』。面對普天之下的蕓蕓眾生,月同樣只能以偉大的寬容博愛之。
三、『懷人』內(nèi)涵的模塑
『詩心入天地,朋友即故鄉(xiāng)。』思鄉(xiāng)往往與懷人密切關(guān)聯(lián)。古時山水阻隔,通訊不便,魚雁傳書迢遙無期,月亮成了寄托情誼、傳情達思的對象,詩人取其『與人萬里長相隨』(李白《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的特質(zhì),巧妙抒發(fā)『海內(nèi)存知己』的人間摯情,即月光抵達的地方,就有友人等候。
南朝樂府民歌『仰頭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等寫思婦懷遠之作,已初見借『月』『懷人』之端倪。
至于李白,借『月』『懷人』之法得以真正確立,為后世廣泛效仿。詩人先后作《峨眉山月歌》《子夜吳歌》《長相思》《月下獨酌》《渡荊門送別》等『思鄉(xiāng)懷人』之詩,特別以《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中『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一句最具代表性,沈祖棻先生評曰:『兩句之間則又有三層意思。一是自己心中充滿了愁思,無可告訴,無人理解,只有將這種愁心托之于明月;二是說唯有明月分照兩地,自己和朋友都能看見她;三是說因此,也只有依靠她才能將愁心寄與,另無他法。』⑼詩人將思君之愁寄予明月,伴君長駐夜郎西,將明月更高程度地擬人化,對好友王昌齡寄予切切關(guān)懷與思念。嚴羽點評曰:『無情生情,其情遠。』『(日)近藤元粹《李太白詩醇》卷三引潘稼堂云:﹁心寄與月,月又隨風,幻甚。﹂』甚直,甚真。『詩人在許多詩中把明月看作通人心多情物,也只有明月才能同時照亮詩人和友人』⑼的情誼。云云評論,此處尤其以『直』字最為重要。如《靜夜思》對『月意象』的『思鄉(xiāng)』內(nèi)涵進行的定義一樣。詩人李白對『月意象』的『懷人』內(nèi)涵進行又一次歷史性的定義。
如杜甫『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夢李白》),白居易『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雖同人別離』(《江樓月》),韋應物『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寄李儋》),蘇軾『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水調(diào)歌頭·丙辰中秋》)等等,舉不勝舉。對于這些詩人,鄉(xiāng)思之『愁』有濃淡;懷人之『憂』有大小,千差萬別,卻能于一個月亮意象中準確無誤地表達出來,使人不得不佩服中國古詩藝術(shù)的高妙。在遠離故鄉(xiāng),遠離親人的宦游人眼里,月亮已然是寄托戀人間苦相思的最貞潔的物象,也是傳達對故鄉(xiāng)和親朋無限思念的最為純粹的使徒。在浩瀚的詠月古詩詞中,確以『思鄉(xiāng)懷人』這一類為最多,又以李白最具文學史意義。
此外,李白對月意象內(nèi)涵還有進一步的豐富與詩意的升華。除了『思鄉(xiāng)懷人』,月還有如愛情堅貞、志行高尚、吊古傷今、悲歡離合等諸多象征義。這在李太白的詩中亦是各顯其色、展露無遺,得以前無古人的升華。其得月之作往往『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陸機《文賦》)⑽『略舉較著,令恍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王充《論衡·藝增》)⑽
四、結(jié)語
在中國歷代文人中,把月寫得最美,用得最生動的,非李白莫屬。李白『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篇第八》)⑾『他的流暢簡樸風格使其作品有著持久的魅力』,⑿總其一生,詩人至死把明月視為知己,有形態(tài),有風度,有性情,能說會聽。在詩人豪放不羈、飄逸灑脫的想象中,詩人可引月而來,乘月而去,步月而歸,行月逸情,泛月增趣,度月如仙。偉大的李白以明凈縹緲的心境去探索世界萬物,體驗自然之盛,以氣吞萬象的宇宙意識締造超脫物外的境界。『月』是李白詩情的神魂,也是詩人精神的皈依。在美酒作陪、明月伴行的一生中,明月給予『詩仙』浪漫、豐滿和光明,源源不斷地贈予詩人不朽之作。
李白的明月歷時邈遠,匯聚著歷史的煙塵,汲取了民族文化之精髓,融合了古代哲學和藝術(shù)思索,詩人以《靜夜思》《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等大成之作徹底揭除月意象有『隔』⒀的『思鄉(xiāng)懷人』內(nèi)涵(象征義)的歷史面紗,使『思鄉(xiāng)懷人』成為月意象明確的象征義和文學傳統(tǒng),具有歷史性的模塑意義。并以《把酒問月》《關(guān)山月》等眾多詩作對月意象其他多種象征義進行了更高級的提煉和升華。為中國文學史植入了一個偉大的示范,影響著中晚唐以降歷朝歷代文人墨客的文藝創(chuàng)作。可謂『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⑽承前而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