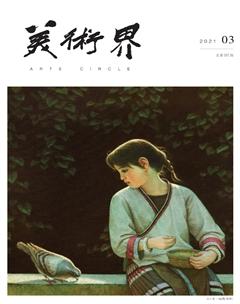明清徽商與新安畫派關系考論
吳楊
【摘要】新安畫派是中國繪畫藝術史上一個極具創造性的藝術流派,它是明末清初活躍于徽州的繪畫流派,它的誕生與社會環境中的諸多因素有著必然的聯系,其中經濟對它的影響舉足輕重。明末清初,正值封建社會的晚期,資本主義經濟開始在社會中萌芽,“賈而好儒”的徽商與當時文人畫家往來密切,他們收藏書畫、資助書院、頻辦雅集,對新安畫派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徽州商賈與新安畫家兩個團體的相互交融也為“儒商”的身份增加了書卷氣。
【關鍵詞】徽商;新安畫派;相互影響和發展
新安畫派是中國美術史上重要的繪畫流派,它的形成和發展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環境等都密不可分,尤其是在經濟方面,新安畫派與當時崛起的徽商具有直接關系,且在各自發展的過程中相互影響。本文從徽商的資本積累、新安繪畫群體的形成和徽商、新安畫派在經濟與文化上的融合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賈而好儒的徽商資本積累
明代中后期至清代,正值封建社會的晚期階段,封建制度日趨衰落。政治上,朝代更迭、社會動蕩加速了新制度的孕育——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內部產生并迅速增長。在這社會轉型時期,山西、安徽等地興起了各個商幫,一支來自安徽的商幫——徽商,在明清時期的江南甚至在當時的整個社會經濟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徽州地處黃山南麓,素有“黃山南大門”之稱,它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它是徽商的重要聚居地和徽文化主要發祥地之一。徽州因屬邊緣地帶,山高林密,田地較少,人口眾多,故徽州人外出經商,自謀生路,所以有“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積蓄,則十一在內,十九在外”①之說。徽州因多山,所以茶葉、木材、紙張產量較多,在唐代,祁門茶市便十分興盛;到了南宋,一些徽商通過貿易,富甲一方,資本雄厚,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合稱“程十萬”;宋朝初年,徽商不僅經營瓷土和生漆等產品,同時還經營筆、墨、紙、硯文房四寶,商路遠到山西;明朝成化年間,徽商開始經營鹽業,于是徽商以鹽業為中心,在當時的江南乃至成化年間的商界占據半壁江山。因此才有“鉆天洞庭遍地徽”和“無徽不成鎮”之說。明代《安徽地志》所說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府志》載:“徽州保界山谷……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②明代戲曲家湯顯祖道:“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明代后期至清乾隆末年,是徽商發展的全盛時期,這一時期的徽商,營業人數多、活動范圍廣、經營行業與資本雄厚,在當時各商幫中舉足輕重。
徽商在清初又被稱為“儒商”,這一稱呼的轉變與徽州歷史上崇儒尚教,學風盛行密不可分。新安境內,上至府縣學、書院,下至民間私塾、會館,都極為昌盛。許多徽商在從商之前皆是儒生,他們幼時便熟讀四書五經,研究儒學文化,精通筆墨丹青,如明代休寧商人汪貴,自幼奇偉不群,讀小學、四書,輒能領其要。卻因生活所迫,只好“棄儒從賈”,即“先儒后賈”“以儒服賈”。這些儒生雖然轉而從商,但是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賈而好儒”。所以,當徽商們積累了一定的資本之后,便開始廣泛結交文人雅士、書畫名家,尤其是與當時新安地區一批清高孤傲、閑淡古樸的畫家交往甚密,徽商喜愛丹青,廣建園林,舉辦雅集,營造出一個有利于當地書畫藝術發展的良好環境,在文化和藝術上的致力與投資有效地促進了新安畫派的發展。
二、偏居新安的繪畫群體形成
明末清初之際,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經濟上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同時,思想文化領域卻是集大成之際,隨著清王朝政權逐漸穩固,徽州地域一批遺民畫家重視氣節,拒絕與清廷合作,他們選擇歸隱山林,借筆墨表達自己心中的逸氣。他們之中,以漸江為首,以查士標、程邃為代表,第一個提出新安畫派名稱的學者張庚,道:“新安自漸師以云林法見長,人多趨之……”以汪之瑞、雪莊、梅清、姚送、祝山嘲、汪梅鼎等為代表的新安畫家們,一反以“四王”為代表的正統派的繪畫風格,寄情山水,師從造化;在繪畫內容上,新安畫家們將黃山境內高古秀逸、平淡雅致的山水風光生動地表現在尺幅之間;在繪畫技法上,他們推陳出新,改變了“清初四王”的傳統繪畫布局定式,取法高古,效仿倪云林的幽秀曠逸,筆簡意遠,以秀逸高古、清新雅致的風格傳承山水畫的精髓,他們的繪畫風格整體相近,趨于蕭散疏離,講求無我之境,天人合一,繪畫筆法重意輕形,突顯出鮮明的士人逸品格調。他們久居徽州,以寫黃山風貌為主,故又常以“新安畫派”稱之。由于這批畫家的地緣關系、人生信念與畫風都具有同一性質,所以時人稱他們為“新安畫派”。最早提出“新安畫派”名稱的是清朝康熙年間的藝術理論家張庚,張庚之后,人多沿用,“新安畫派”遂成定稱。新安畫派成員眾多,力量雄厚。畫藝可觀者近80人,其中卓然自成一家者約有20人。
新安派山水畫之所以在明清之際達到了發展的鼎盛時期,與明清時期高速發展的徽商文化以及財富迅速積累的徽商有很大的關系。在明清之際徽商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迅速擴大,連清朝乾隆帝在下江南時,看到徽商的財富實力時也忍不住發出感慨:“富哉商乎,朕不及也。”在徽商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他們也熱衷于藝術文化發展的投資,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徽商文化的發展,當然這其中也包括了對新安畫派山水畫的影響。
可以說,新安畫派之所以在明清之際達到了發展的鼎盛時期,與當時坐賈行商的徽州商幫密不可分。反之,徽商與文人的密切交往又為徽州“儒商”之名加以佐證,經濟與文化的交融為明清之際徽州的發展添加了催化劑。
三、徽商與新安畫派在經濟與文化上的融合
“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徽商累積了充足的資本,但是在明末清初,當時社會在思想上仍然保留著“四民分業,士農工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觀念。所以,新安之地的徽商們雖然生活富足,但社會地位不高。在積累了一定的資本之后,徽商們便“賈而好儒”,他們喜交畫家墨客,往來文人雅士,廣建書院、興辦學堂、崇儒尚教、贈送筆墨、頻設雅集,支持書畫家們進行藝術活動,徽商的賈而好儒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新安畫派的發展和壯大,反之,新安畫派的成熟也為“儒商”的身份轉變增添了書卷氣。
(一)購買書畫作品
明清之際,新安之隅的文人畫家們志氣高潔,不愿仕清,遂隱居山林,寄情山水,他們身上具有鮮明的士人逸品格調。但這些文人畫家們雖然性格孤傲清高,經濟上卻并不寬裕,以新安四家之一的查士標為例,據《徽州府志》中記載:“查二瞻以書法名世,畫尤工,然不肯輕下筆,家人告罌中無粟,乃握管,計一紙可易數日糧輒又擱筆。”③查士標常常家境貧寒,卻又熱愛書畫藝術,因生活所迫無法安心作畫,在這種經濟狀況下,碰到賞識自己的徽商,實在是一種幸運。徽商們在經濟上對新安畫派的資助是新安畫派發展的重要保障。徽商對新安畫家的一個重要贊助行為就是出資買畫,徽商作為藝術交易的直接參與者,無形中也成為了新安畫派的推動者。徽商大賈馬日璐博覽群書,沈酣深造,廣結畫師,尤喜新安畫派,他著有《南齋集》,馬日璐在小玲瓏山館中,藏有漸江的《梅花古屋圖》,徽商對藝術交易市場的推動可見一斑。徽商收藏畫作,不僅在物質上資助了新安畫家,并且提升了新安整體的審美風格。以漸江為例,作為新安畫派的創始人,漸江的繪畫風格和審美直接奠定了新安畫派的格調,漸江家境寒微,所以漸江不得不登門拜訪徽商。漸江與徽商往來密切,經濟上的拮據和藝術上的豐富,使得漸江與徽商往來時經常贈畫以回報贊助之恩,徽商吳不炎在揚州經商時,漸江畫《曉江風便圖》以贈行,可知漸江與吳不炎交往的密切。
徽商購買畫作在物質上,無疑于雪中送炭,解了新安畫家的燃眉之急,讓他們可以更好地創作作品。同時,徽商對藝術與文化的熱衷也促使他們在藝術市場中占據先機,帶動了藝術市場的繁榮。可以說,正是因為徽商的贊助,更多的新安畫家們才得以生存,藝術道路才能走得更遠。徽商對藝術的贊助,不僅僅是“賈而好儒”,他們為新安畫派的發展之路奠定了物質的基石,也進一步推動了藝術市場的發展與壯大。
(二)組織書畫雅集
雅集,是專指文人雅士吟詩詠文、書文作畫、崇論宏議的一種集會形式。文人雅集本是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以詩文創作為目的的一種傳統文化交往活動。新安之地的徽商中不乏飽學之士、風雅之輩,比如馬日館、馬日璐這樣的大賈。徽商們為了與文人畫家們游園賞景、吟詩作畫、切磋研究、探討畫理,都熱衷于召集文人結社集會,結交文人畫家。尤其在新安地,徽商們便時常在私人園林官邸中舉辦雅集活動,這也是新安畫家們提高繪畫技法、整合繪畫風格的重要方式之一。他們在徽州境內和揚州頻設雅集,也為新安畫家探討技法和創作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李斗的《揚州畫舫錄》中曾記載:“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為最盛。”④記載中雖未提到徽州,但揚州的畫家半數來自徽州,新安四家均在廣陵游玩過,其中,查士標則久居揚州。阮元的《廣陵詩事》中記載道:“嘗居北鄉呂祖壇。壇去城三余里,有老柏修篳清溪繞之。二瞻書‘偶落人間四字額。”由此可見,徽商對于新安畫家的贊助和支持。
徽商與新安地的文人墨客往來密切,在雅集活動中,新安畫家受益良多,有這樣一個與眾畫家交流心得、切磋技巧的集會,很大程度上激發了他們的創作靈感,提高了畫家們的繪畫技法,使得新安畫家的人品和氣節相投,繪畫風格趨于枯淡幽冷,具有鮮明的士人逸品格調,為新安畫派繪畫風格上日趨成熟提供了舞臺。
(三)廣建私家園林
徽商因為資本積累和自身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所以喜結文人雅士,新安畫家自然成了徽商宅中的座上賓,正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那么,徽商對于新安畫派另一種贊助的方式便是廣建園林,為他們交談畫技構建場地。
歙縣西郊的鮑家園林便是清乾隆、嘉慶年間著名徽商鮑啟運建的私家花園,鮑啟運原為清乾隆、嘉慶年間著名徽商、鹽法道員,他自幼便在私塾中報讀詩書,對于筆墨丹青甚是喜愛,更愛與當時的書畫家探討畫理、研究古籍,遂修建了私家園林。鮑家花園是典型的古徽派園林與徽派盆景相結合的私家園林,堪比蘇州拙政園、獅子林,目前是中國最大的私家園林和盆景觀賞地,可想而知,當時徽商資本的雄厚和對藝術家的敬仰。
徽商當時的商路之廣不可估量,由于在他們中有較多的人從事鹽業,在揚州地區販賣,所以在當地也建了相當多的園林,最著名的便是清代著名藏書家馬日琯、馬日璐的“小玲瓏山館”。馬氏兄弟雖為鹽商,富甲一方,卻酷嗜典籍,閑暇時與書畫名家或吟詠切磋,或借書抄讀,見古本秘籍必重價購之,或世人所未見者,不惜千金付梓,曾以數萬金購得傳是樓、曝書亭藏書,所藏達十余萬卷,其書皆精裝,聘善手數人寫書腦,終歲不得輟。“小玲瓏山館”雖建在廣陵,但當時新安一批畫家久留揚州,他們與“揚州八怪”曾是馬氏兄弟的堂上客,時常在一起吟詩作畫,可以說,“小玲瓏山館”的存在間接推動了新安畫派的發展。
(四)興辦學堂書院
徽商對于新安畫派的贊助方式之四便是修建書院,新安之地的書院之多早有記載,道光《徽州府志》卷三《營建志·學校》記載:“歙在山谷間,墾田蓋寡,處者以學,行者以商。學之地自府縣學外,多聚于書院。書院凡數十,以紫陽為大。”⑤宋元以來,徽州是當時所修建書院最多的一個地方,徽州“一家一村,亦各有書屋。書屋者,即古所謂家塾也”。徽州書院都設山長,主持書院工作,大都聘請飽學之士和有名學者作主講,以研究和學習儒家經典為主,亦議論書畫之技。其中,不乏當時的書畫名家,其中就有“華亭畫派”的代表董其昌和新安四家之一的查士標。董氏晚年曾在黃山一帶游歷作畫,并在休寧古城書院等處講學,傳授畫技,且留下不少書畫墨跡。在新安游歷期間,常在書院與新安畫家們交流心得,其中,與“新安四家”之一查士標的交往最為密切,族中叔伯父兄,如查應光、查維寅、查維鼎等對詩、詞、書、畫及古物的研究已蔚然成風,查士標就在這樣的環境中攻讀詩書,研習“舉業”,20多歲時,他中了秀才,里人常把他喊作“查文學”。
書院的建設,提高了新安之地的文化素養,同時,書院的文人講學也為新安畫派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畫藝高超的人才。
結語
徽商的贊助為新安畫派提供了物質基礎,新安畫家高潔孤傲的思想也給徽商極大地影響。新安畫派與徽商是息息相關的,徽商在完成資本積累富甲一方的時候也正是新安畫派風格形成發展鼎盛的階段,他們在經濟和藝術上的不同訴求,商人與畫家之間的互補使兩者推動了明清徽州經濟和藝術的發展。
注釋:
①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人民出版社,2007,第38頁。
②趙吉士等合著:《徽州府志》,黃山書社,2010,第389頁。
③趙吉士等合著:《徽州府志》,黃山書社,2010,第792頁。
④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八《城西錄》,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84,第180頁。
⑤趙吉士等合著:《徽州府志》,黃山書社,2010,第5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