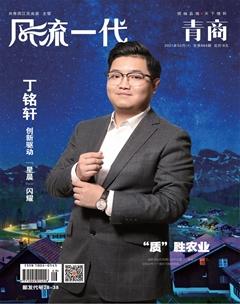“996”工作模式下的養育難題
宦菁
“父母努力賺錢”與“孩子需要陪伴”似乎天生就是一對矛盾,無論選擇哪一邊,另一邊就得放棄。
閨蜜安洛是一位全職媽媽。幾年前,她也是職場上的“拼命三郎”。雖然工作是“996”模式,但她也相應地擁有極其體面的薪水。孩子出生后,她的生活平衡被打破——一邊是忙碌的工作,一邊是需要陪伴的孩子,而孩子的父親同樣也是“996”工作模式的大廠員工。在掙扎了近一年后,安洛遞上了辭職信,從職場人變為家庭主婦。
陪伴孩子成長的這幾年,雖然有過想重返職場的掙扎,但看著孩子在自己的精心愛護下長大,安洛職業上的缺憾似乎也就被撫平了。她笑稱自己是“喪偶式帶娃”——爸爸忙到不著家,偶爾空閑了才能陪上孩子一會兒。“你看,我要是重返職場,這孩子只能丟給老人,可不就是現實版的留守兒童嗎?”
無獨有偶,豆瓣上一條“父母都是‘996,孩子誰來管?”的問題引發了互聯網上熱烈的討論。“祖父輩來管”成為大多數“社畜”的答案。當人們還在討論農村留守兒童的議題時,城市中的新留守兒童在“996”工作制下漸漸浮現。
清早,在孩子還未醒來的時候已經踏上上班的公車;夜里下班回家時,孩子已經入睡。這就是“996”工作模式下的父母的家庭生活——與孩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卻彼此分隔,猶如平行時空,本該親近的家人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是要職業發展,還是要孩子成長路上的陪伴?這對于父母而言,都是極其艱難的抉擇。父母選擇“996”工作模式不僅是為了自己的職業發展,也關乎整個家庭的生活質量。即便是像安洛這樣下定決心放棄高薪,回歸家庭,背后還是有一個為了家庭繼續“996”工作模式的父親。“父母努力賺錢”與“孩子需要陪伴”似乎天生就是一對矛盾,無論選擇哪一邊,另一邊就得放棄。
從現實的角度考慮,大多數家庭選擇了前者。而孩子則成了物質上衣食無缺、精神上缺少親子陪伴的城市隱形留守兒童。曾經堂前萱草、圍爐夜話的溫暖的家,曾經嚴父庭訓、慈母燈下縫紉寒衣的那個充滿煙火氣的家,因為父母的“996”工作模式而變得清冷起來。
在“996”工作模式下,原本溫暖的家已經是回不去的過去式,所幸,依然有人希望能夠盡量解決這個難題。關注人口問題的攜程創始人梁建章很早就注意到工作和家庭的兩難,想以一種“兩全”的方式在公司建立親子園,讓員工能夠安心地把孩子帶到公司。這塊原本讓他引以為傲的試驗田,因為管理上的缺失,發生了令人震驚的虐童事件,最終成了反面教材。前車之鑒,不少原本也存著為員工解決養育問題想法的企業都打了退堂鼓。
去年年底的一則新聞,讓“社畜”家長又看到了希望:林州法院為解決節假日和加班時部分干警家庭未成年子女無人照看的困擾,設立了“干警子女托管中心”,為孩子們開辟歡樂的天地,讓干警們可以更安心地工作。“要是公司也能有這樣貼心的托管中心就好了!”這句話說出了不少家長的心聲。
孩子無法獲得父母的陪伴,若干年后或許會產生諸多社會問題。沉迷手機、網絡,“空心化”的孩子,叛逆的青春期,抗挫折能力降低……近年來,孩子的心理問題層出不窮,究其原因,家長在陪伴中缺位是無法忽視的。
來自武漢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缺少父母陪伴的留守兒童,70%存在抑郁、焦慮、孤獨等心理問題,有些孩子甚至產生過自殺的想法。現在,如果“996”現象不引起人們的重視,發生在留守兒童身上的心理問題,將逐漸蔓延至缺少父母陪伴的加班族家庭里。
逐夢得拼搏,成功須奮斗。我們鼓勵奮斗,我們也熱愛奮斗創造的幸福生活,但讓勞動者超時工作,從家庭生活中抽離,是對奮斗精神的背離。正如新華社時評所說的那樣:讓追夢人健康地奔跑,讓企業發展更有溫度,才是奮斗該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