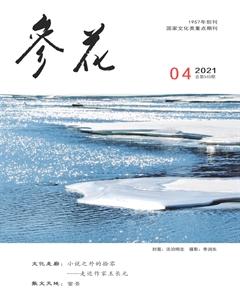語言學詩學研究
摘要:作為俄國形式主義和布拉格學派的奠基人,20世紀最偉大的語言學家之一,雅各布森語言功能觀提出的“六因素六功能學說”開展了當代文學語境下的跨學科研究,其突出特征就是語言學與詩學聯(lián)姻。在很大程度上,語言學詩學就成了雅各布森文論思想的核心觀點,而語言學詩學的理解,指的就是處于語言學范式下的文學研究。本文從雅各布森語言功能觀出發(fā),在語言學詩學的表現(xiàn)方式和結(jié)構(gòu)機制的兩個層次上,就其對以語言學為大背景下的當代文學研究作一學理分析。
關(guān)鍵詞:雅各布森 語言學詩學 詩學功能
羅曼·雅各布森(以下將其簡稱為雅氏)作為俄國形式主義的領(lǐng)袖人物,布拉格學派和紐約小組的奠基人,20世紀最著名的語言學家之一,其學術(shù)影響力在現(xiàn)代語言學、符號學、現(xiàn)代人類學、精神分析學、詩學等一眾學科的發(fā)展上發(fā)揮著積極的作用。很大程度上,雅氏的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理論解開了當代眾多人文學科發(fā)展的桎梏,打開了新視野,而在這其中,他在語言學和詩學領(lǐng)域里取得的創(chuàng)新性成果最是格外醒目。
雅氏對語言學詩學的認識下了一個定義:“語言學里將詩學功能置于其他語言功能的關(guān)系中進行研究的那部分。或者說,詩學就是在以語言學為大背景,詩歌為小背景的前提下,對詩學功能開展的語言學研究。”[1]在雅氏這里,語言學是把言語材料到語言藝術(shù)的轉(zhuǎn)變作為研究的主要目的,他選擇從詩歌的言語材料出發(fā),從語言功能的角度來分析“文學性”。為此,詩學功能(亦稱美學功能)就成為他語言交際六功能里的重中之重,同時也回答了何謂“文學性”這一棘手問題。正如他在1958年的那篇著名的演講《結(jié)束語:語言學與詩學》中提道:“當信息作為信息,詞語作為詞語本身,而不是作為他物的替代與表達,詩性功能就體現(xiàn)出來。”[2]為此,本文在總結(jié)雅氏“六因素六功能學說”的基礎(chǔ)上,重點闡述他的語言學詩學功能,就語言學詩學表現(xiàn)方式和結(jié)構(gòu)機制的兩方面作一學理分析,希望能夠在以語言學為大背景的當代文學跨學科研究領(lǐng)域里稍做啟發(fā)。
一、等級序列:語言學詩學的表現(xiàn)方式
雅氏在總結(jié)出語言交際的“六因素六功能學說”之時,具體闡釋了六功能的表現(xiàn)方式。在他看來,情感功能是為了直接表達說話人對聽話人的態(tài)度,是自我情緒的有力釋放。意動功能在句法上可以表現(xiàn)說話人對意動用法的運用如命令式和祈使句等,實施的是對聽話人的定位和要求。語言的寒暄功能就體現(xiàn)在建立起同發(fā)話人和聽話人之間的一條交流通道上,其目的是為了實現(xiàn)說話人和聽話人在順暢的語言環(huán)境中進行交流。指涉功能體現(xiàn)的則是語言的指代或?qū)φf話人和聽話人之間認知能力的一個檢測。元語言功能集中在說話人和聽話人之間的代碼上,它體現(xiàn)的是雙方對同一代碼的解讀能力。當說話人和聽話人之間的交流活動趨向于信息本身時,語言的詩學功能就凸顯出來。之后,雅氏又在基于自身定義的語言功能觀體現(xiàn)出的各自特點上,提出了各功能間的“等級序列”觀,他認為在語言學詩學研究中是以詩學功能為主導(dǎo)的文學研究。“等級序列”觀決定了話語交際六功能在不同條件下的位置劃分:當某一個功能占據(jù)主導(dǎo)位置時,其他功能就會暫時“消退”,而這一主導(dǎo)功能就成為判斷話語交際功能屬性的標志。如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句詩歌“桂林山水甲天下”,要是傾向于信息的說話人,則可以凸顯情感,表明說話人陶醉于桂林山水美景的愉悅心情。指涉功能占據(jù)支配地位時是對具體語境的一個寫實描述,向說話人和聽話人共同傳達桂林山水的美景、美物的具體環(huán)境情況。若強調(diào)的是聽話人,意動功能就占據(jù)支配地位,充滿對聽話人的誘惑之意,暗示對方可以到此一游。若強調(diào)的是交際功能,則可以體現(xiàn)在像火車上旅客彼此間一句簡單的相互問候,寒暄之語,只是為了打開彼此間的對話渠道。如若是一些不明其意的小孩子也學做表達這句話,這七個字在他們這里都是一個極其陌生的符碼,呼喚的是父母幫助他們進行詮釋,體現(xiàn)的是元語言功能。如若強調(diào)詩性功能,此處凸顯的正是文字本身,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羅青意可參”,這句有名的詩正是出自南宋王正功,詩歌語言美在言語本身,因而體現(xiàn)的是詩性之美。
很顯然,雅氏這里的主導(dǎo)功能并非意味著言語交際諸多功能中的某一種壟斷,強調(diào)的正是一種不同功能間的等級序列。在等級序列中的主導(dǎo)功能就顯得格外重要,任何言語交際行為的六功能都是同時存在的,當語言系統(tǒng)內(nèi)部的功能“等級序列”位置變化時,主導(dǎo)功能自然也隨之改變。雅氏的語言學詩學關(guān)注的就是在等級序列中以詩學功能為主導(dǎo)的詩學研究,他認為:“一部詩作應(yīng)該界定為其美學功能是它的主導(dǎo)的一種文字信息,”[3]換句話說,詩歌語言應(yīng)當是以自指的詩學功能為主,而后才是提供信息的功能。對于這一點,雅氏也早有明言:“當語詞作為語詞被感知,而非作為被命名客體的再現(xiàn)或一種情感的宣泄,當語詞及其組合、意義、內(nèi)外形式都獲得了自身的分量和價值,而非對現(xiàn)實冷漠的指代,詩性就到場了”。[4]正是由于文學作品自身獨特的言語結(jié)構(gòu)和詩學功能等區(qū)別性特征,體現(xiàn)了雅氏語言功能觀的“文學性”,文學語言是以自身言語的審美為主,而信息的自指同時賦予了形式本身以意義,從而將文學語言和其他語言研究區(qū)分開來,這也是詩之為詩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就算詩學功能在詩歌的功能等級序列里占據(jù)了主要位置,但由于語言交際六功能的普遍存在,詩歌類型也會因為其他功能的排序位置不同而改變。如一首感人至深的愛情詩,情感功能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視。說教詩,意動功能居于詩學功能之后。而史詩強調(diào)的是敘事的第三人稱,就把指涉功能放在其次的位置。
二、雙軸現(xiàn)象:語言學詩學的結(jié)構(gòu)機制
雅氏對語言學詩學的研究結(jié)合了共時與歷時狀態(tài),在他看來,不管是語言學還是詩學研究,不但要關(guān)注共時狀態(tài)下那些永恒的、連續(xù)的靜態(tài)因素,還需要注意歷時研究中的變化規(guī)律。雅氏也從此延伸出了詩性功能的語言學實現(xiàn)路徑,即如何從中體現(xiàn)詩之為詩的區(qū)別性特征,表明了詩歌中選擇和組合相結(jié)合的“雙軸現(xiàn)象”,在這其中,選擇基于對等原則,各要素之間具有同義、反義、相似或相近等關(guān)系,但是它們之間的位置對等,在文本中往往不易發(fā)覺,組合則源于臨近,形成序列。而所謂的“雙軸現(xiàn)象”,就是指對等原則從選擇軸投射到了組合軸上,這樣一來,原本在選擇軸上不易發(fā)覺的對等原則在組合軸上得到凸顯,從而體現(xiàn)了詩性功能里的結(jié)構(gòu)機制。雅氏語言學詩學的結(jié)構(gòu)機制正是語言功能觀中“文學性”這一區(qū)別性特征得以表現(xiàn)的內(nèi)在規(guī)律。具體而言,就可以表現(xiàn)在一首詩內(nèi)部不同音節(jié)的規(guī)律、詞性、長短等方面。如馬致遠的那首《天凈沙·秋思》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來說明雅氏“雙軸現(xiàn)象”的體現(xiàn):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在這首詩中,“枯藤”“老樹”“昏鴉”就是典型的對等結(jié)構(gòu),最容易發(fā)覺的是這三個詞都有消極的含義,皆為落寞之景。一般而言,只要選擇其中的一個詞語就可以代表整個的含義。但是這樣的對等結(jié)構(gòu)放在了同一水平線上進行組合,就將對等原則從選擇軸投射到了組合軸,這首詩的詩學功能便表現(xiàn)出來。還有“小橋”“流水”“人家”以及“古道”“西風”“瘦馬”各自三個意象與第一句都有著相同的結(jié)構(gòu)與組合,這三句之間相同的選擇項從而形成了更大范圍的組合。此外,這首詩的對等結(jié)構(gòu)還體現(xiàn)在語詞韻律配合上。如“鴉”“家”“馬”“下”和“涯”是作者明顯有意的尾韻配合。實際上,這種將對等原則從選擇軸投射到組合軸的“雙軸現(xiàn)象”在古今中外的詩歌中無處不在。而也正是這些獨具匠心的詩人通過對“雙軸現(xiàn)象”的嫻熟應(yīng)用,詩歌語言不再強調(diào)傳統(tǒng)般的描述性,相反,語詞在內(nèi)部的“投射”中,充分進行它們的游戲,不再指涉社會文化的宏大背景,而是讓讀者感知到的只是語詞本身,從而展現(xiàn)詩歌語言的詩性美。
雅氏通過“雙軸現(xiàn)象”的分析還對失語癥病理的本質(zhì)做過一番解釋:一個患失語癥的人,不是負責選擇和替換的功能出了問題,就是負責組織和結(jié)構(gòu)的功能出了問題。前者的癥狀就表現(xiàn)為言不由衷,如患者頭疼,他不會說頭疼,而只能指著頭部部位。后者就表現(xiàn)出語言組合的混亂現(xiàn)象,如“我吃飯想”或是“吃飯想我”,總之就是無法表達出一句連貫且完整的“我想吃飯”。在雅氏看來,詩人恰恰就像患了失語癥的病人一樣,有的在選擇關(guān)系中失語,有的在組合關(guān)系中錯亂。但詩人恰恰由于能夠沉醉于“言語錯亂”的語篇里,詩學功能才得以表現(xiàn)出來。詩學功能憑借著“錯亂”的言語特征將讀者的目光聚焦語詞本身,普遍的社會文化意義才不復(fù)存在,唯有詩性之美。
三、結(jié)語
對雅氏而言,文學研究要關(guān)注作品本身,關(guān)注作品的構(gòu)成形式,而他通過語言學詩學概念的提出就將文學研究從外部轉(zhuǎn)向了內(nèi)部,不再像傳統(tǒng)文學批評去關(guān)注作品的存在起因,而是關(guān)注文學作品本身的存在形式,即在文學作品研究走向“語言學轉(zhuǎn)向”的同時,確定了文學語篇是以詩學功能為主導(dǎo)的文學研究對象,定義了雅氏語言功能觀視角下的“文學性”。本文在以總結(jié)雅氏語言功能觀的基礎(chǔ)上,就語言學詩學的表現(xiàn)形式和結(jié)構(gòu)機制做了一次學理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語言學與詩學聯(lián)姻后的研究前景是一種“詩學科學的探索”。正如雅氏看來,這種“語言學轉(zhuǎn)向”是對文學研究的一次正本清源。最后,對雅氏語言學詩學概念認識的重要性,可以引用他在《語言學與詩學》一文結(jié)束時的一段話:“我們所有人必須意識到,一個對語言的詩性功能充耳不聞的語言學家和一個對語言問題漠不關(guān)心,對語言方法知之甚少的文學家同樣都是十足的時代落伍者。”[5]
參考文獻:
[1]Jonathan Culler.Structuralist Poetics:Strcturalism,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Ithaca: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75:65.
[2]Roman Jakobson.“Closing Statement:Linguistics and Poetic”,in Thomas A.Sebeok ed.Style in Language.Cambridge:The M.I.T.Press,1960:356.
[3]張杰,汪介之.20世紀俄羅斯文學批評史[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310.
[4]Roman Jakonson.“What is Poetry?”in Krystyna Pomorska and Stephen Rudy,eds.Language in litera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378.
[5]Jakobson.R.Linguistics and poetics.In K.Pomorska and S.Rudy(ed).Language in Literature.London:The Belknap Press,1987:62-94.
(作者簡介:楊達,男,碩士研究生在讀,天津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
(責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