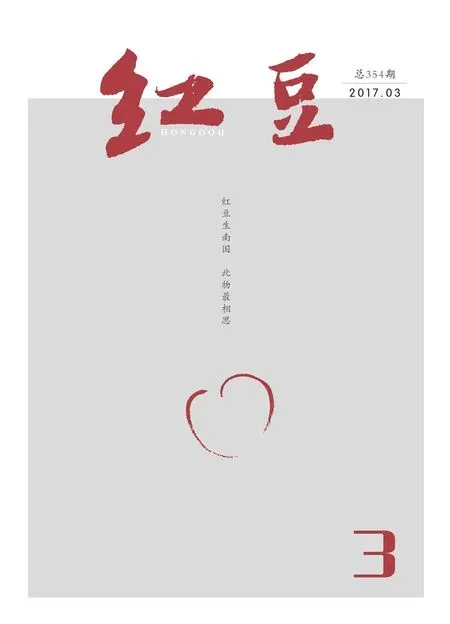大地珍饈
胡笑蘭
不管是大街小巷,你都會與粉相遇,這就是南寧。無論你走進哪家粉店,里面總是坐滿食客,他們不緊不慢地品嘗南寧的美食。
南寧一家苗族酒店,裝修精致,婉約苗族風情,一些穿著民族服裝的小伙子、姑娘進進出出,不時聽見悅耳的苗歌。一行人落座,妹妹的客戶方先生拿起菜譜點菜,似有大吃一頓之狀。
油茶、老友粉一定不能少。方夫人細致地補充,這是個善解人意的女人。朋友來了有好酒,但也要有老友粉。夫妻倆一遞一答,心有靈犀。
菜一道道地上,老友粉終于出場。考究的青花大瓷盤,滿滿的一盤,白、黃、紅、綠,間雜著星星點點的赤褐色,騰騰地冒著熱氣,我聞到了淡淡的清香。
那些配菜,兩種看似并不相干的東西,彼此都做些改變,有時甚至是痛苦的,但往往可以組合出一種神奇。紅的椒、亮黑的豆豉、黃爽爽的筍干、細碎的肉末、瑩白的米粉,豐滿的顏色,瞧它水生生、紅彤彤的樣兒,饞蟲爬到了嘴邊。眼睛是兩塊毛玻璃,欲望在玻璃后面蠕動,欲望似原子分裂,在無限大的空間跳扭腰舞。視角與嗅角的雙重沖擊,讓人充滿期待,又不忍心張嘴大嚼,唯恐這滋潤的美瞬間消失。
在某種難以抑制的情緒之下,酸筍之酸爽讓鮮美的肉更加余味綿長,而肉的鮮甜入筍,不僅削減了酸筍凌厲的酸味,更讓酸筍于酸爽中又夾帶了鮮甜。酸與辣本來就是打不散的冤家,酸借辣而飛揚,辣因酸而幽深,像一個未透紅的蘋果,苦澀的酸味中含有些許止渴劑。有了酸和辣的交融,粉立刻變得霸蠻起來,有了一種橫掃萬千味蕾、直擊心靈深處的強勁力量。
明天我帶你們去一個地方,專門去吃老友粉。方先生瞧我們吃得香甜,興致更高了。
第二天,方先生帶我們走進一條小巷。小巷的盡頭,我看見了老友粉的招牌。進店后,老板娘見方先生進來,放下手頭的活計迎上前來,滿眼顧盼生輝,顯然他們很熟。在我們等待的間隙,方先生充滿回憶的旋律在這個簡單的小店回響,忽高忽低,把我們帶到了三十年前。
方先生說,一九九〇年他考取了南寧市醫藥學校。從沒有出過門的母親決定送他去報到,他和母親連夜走幾十里山路,到學校的時候,天已經大亮。此時,聽到自己的肚皮一個勁地咕嚕嚕地叫喚。突然聞到了一股香氣,淡遠又執著、頑強地直入鼻息,似乎還不夠,一路直奔攪動他的胃腸。那香氣分明是從學校旁邊的巷子里飄出來的,轉眼看到巷子盡頭老友粉的招牌。他使勁地咽了咽口水。母親是何等的細心,拎起包拉著他就朝巷子里走去。店鋪簡簡單單,食客卻坐得滿滿當當,隔了餐臺的廚房熱氣氤氳,米粉的香味和著年青老板娘的熱情一起傳遞出來。
母親的錢包是手帕,裹了一層又一層,兩張元票夾雜著一小摞角票,角票卷著邊,顯然是存了很久的。母親從里面一張張數,小心地數出八角,遞給笑臉相迎的老板娘。不一會兒,一碗米粉就充滿誘惑地擺在面前。哪還顧得斯文?也顧不得謙讓,呼啦啦地自己吃得滿頭是汗。等抬起埋在碗上的臉,心滿意足咂嘴時,他看見了母親一雙溫柔的眼睛……媽,您怎么不吃一碗?媽不餓,包里還有干糧呢。再說我也不喜歡吃。
方先生說,現在想想,那碗米粉是他這輩子第一次吃到的美味,多少年后才懂得母親的那句不喜歡吃。為此,一直后悔甚至慚愧于當初的不懂事。醫校讀書的這幾年,無數次從這家米粉店經過,那飄出來的香味也一次次誘惑著自己,但那幾年一次也沒有再進去過。后來漲價到一元八角,相對于自己每月十幾元的生活津貼,吃碗粉也算奢侈了。而且每個月還得省下一兩元,替母親分憂。那時就在心里告訴自己,等畢業了、掙錢了,一定要接母親到這里,好好吃一碗老友粉。可現在貌似有出息、有能力請母親吃了,母親卻已經不在了。店鋪還是那個店鋪,模樣一點沒變,人也沒變,口味更是沒變,這也是常來這里的原因吧。
方先生環顧四周,語聲低沉,眼眶紅了,我分明看見了一點晶瑩在閃爍。
方先生年少時家貧,粉是難得的美味。但從那時起,每到逢年過節,方先生的母親總能變戲法似的端上一碗米粉。他母親做的粉總是與眾不同,他至今仍固執地認為母親做的粉是最好吃的。
回憶一段舊時光,按摩著腸胃,撫摸著淡淡的鄉愁,吃著這里的粉,想著小時候母親做的粉。那相似的味道,老是讓他產生錯覺,仿佛他來來往往那么多城市都是同一個地方,一個有母親味道的地方。
最著名的就是老子那句話:“治大國,若烹小鮮。”一個人誰也記不清吃過多少種小吃,品嘗過多少種滋味,但生活中沒有哪一碟、哪一種是多余的,它們是生活所需,更是生存智慧。一碗碗老友粉,串起來就組成了酸、甜、苦、辣、咸的生活,它們都是人生的況味,也寄予著某種時代的故事。
責任編輯? ?劉燕妮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