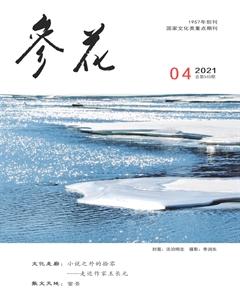奶奶
譚豐華
奶奶姓鄒,她的名字,我至今不曉得,當年,奶奶和許多鄉下女人一樣,一頂花轎抬到夫家,從此一生沒有自己的姓名,死后的墓碑上,鑿上夫姓,德配孺人XX氏的稱呼。這似乎是當地賜予女性一生中最高的榮譽。
奶奶的娘家居我們村三里之外集市的一隅。聽奶奶說,鄒家祖輩是地道的莊戶人。奶奶從小未讀過書,窮人家的女孩子粗茶淡飯,除了學點針線活兒,到了能下地的年齡,須下地干活,因而在崇尚“三寸金蓮”的社會,奶奶的腳并不小。
童年時,我對奶奶充滿著依賴,總喜歡跑到奶奶家黏著她。因為奶奶家的飯菜好吃,晚上依偎在奶奶身旁,數著天上的星星,聽奶奶重復著月亮里的故事。
記得少年時一個晚上,我和幾個孩子藏貓貓,玩到興起,我從家中取來手電筒,剛拿出照幾下,手電筒掉在地上摔壞了。我急得欲哭,左拍右砸仍然不亮,我心慌了。這可是父親攢了許久的錢,才買的心愛之物,我闖禍了。急忙跑到奶奶家尋求庇護。那晚,我蜷縮在被窩里,驚恐讓我久久難以入睡,奶奶躺在我身邊,數落著父親,“孩子小,懂得什么,你要打他,我給你不拉倒。”不知什么時候,我睡著了,第二天我睜開眼,奶奶走了,父親并沒有打我。
在我的心目中, 奶奶就是奶奶,但提起她年輕時的不幸,她只有一串串眼淚。每逢家人團聚,看著兒孫滿堂,奶奶總會感謝上蒼。過了數年,我長大成人,奶奶仍然不忘當年的苦難歲月。據奶奶回憶,伯父尚小,父親還在懷中時,爺爺離開家不知去向。奶奶與倆孩子相依為命。孩子的衣食,土地的耕種,一家人的生計,全落在她肩上。每逢農忙季節,奶奶下地干活手牽一個懷抱一個,過河時一個一個抱過去,黃昏時,再把兄弟倆抱回來,泇河水,成為奶奶一年四季蹚不完的河。兵荒馬亂之年,人如蟲蟻,爺爺一走杳無音信。其間,不少村里人勸奶奶,“老二家里的,想開點,為了孩子,再找一個人家吧,老二這個不要良心的,也不知死哪去了。”奶奶聽到這里總會淚往心中落,她想想這些年,爺爺走后一個字也沒見,人,生死未卜,多少個夜晚,她孤苦無援。她恨爺爺壞了良心,也埋怨自己的命不好。
那些年,鄒家的日子并不寬裕,一年到頭勉強能填飽肚子。舅姥爺念姐弟之情,收養了兩個外甥,到了能割草放牛的年齡,兄弟倆長年吃住在舅姥爺家。
爺爺離鄉后投奔了奉軍。從離開家鄉,到爺爺歸來,時間整整過了十三年。
一九四六年,父親參了軍,隨軍南征北戰,直至全國解放。后來,兩個叔叔也分別投身軍營。臨行前,奶奶免不了落淚,兒子走了,少不了惦念,而奶奶表現出更多的是鎮定與堅強。我們這個家族中,當兵似乎已成為一門家風,也是一種信仰和責任。奶奶門上的光榮牌換了一茬又一茬,直到小叔退伍。
時光匆匆,奶奶看著孩子一個個長大成人,像鳥一樣飛向四方。她也漸入老境。按理說,她辛苦了一輩子,應該熬到“享受”的份上,她沒有這樣做。爺爺去世后這幾年,她依然下地忙活,直至終老。
奶奶活了八十七歲,屬于無疾而終。按照鄉間風俗,奶奶下葬在祖墳墓地,這里有我的曾祖父,曾祖母,還有更多長輩。奶奶的身邊是她一生又愛又恨的爺爺。我不知道奶奶是否對爺爺還耿耿于懷,兒孫們所能做到的,是逢年過節來到墳前,燒一把冥紙,以慰奶奶在天之靈。我想,奶奶在這里并不孤單,因為,我們永遠忘不了她,會時常來探望她。
(責任編輯 王瑞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