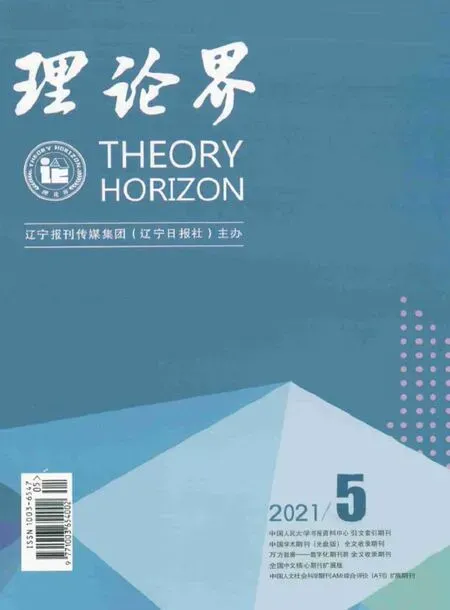重思“一般智力”問題及當代闡釋
唐小梅
1857年7月至1858年10月,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為指導,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馬克思常簡稱為“手稿”,故下文沿用這一說法)中,完成了剩余價值理論的思想實驗。根據1858年11月29日馬克思與恩格斯通信的內容,蘇聯、東歐學者將這一手稿命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1857—1858年》。西方學界統稱《大綱》(以下簡稱《大綱》)。當今世界的發展似乎也已證明,馬克思在《大綱》中,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運作方式,有著無比敏銳的洞察力,這被視為重新研究《大綱》的重要原因。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大綱》都是一個非常難以理解的文本。但是,它也是一個具有巨額回報的文本,因為《大綱》不僅是《資本論》的草稿,而且有馬克思成熟時期方法論的獨特介紹,為馬克思全部著作提供了唯一指南。它的寫作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如1958年11月12日,馬克思致信拉薩爾說“該手稿是歷時十五年研究的成果”。〔1〕具體到“一般智力”問題,如霍布斯鮑姆指出的,《大綱》體現出遠超于19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現狀的洞見和分析。《大綱》也是除《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外,對未來社會作出提示的為數不多的文本之一。總之,《大綱》已經被正確地描述為體現“馬克思思想最豐富的文本”。與其重要性相比,直至1939年(正卷)—1941年(補卷)才在莫斯科出版,再版時間更是晚至1953年。更令人遺憾的是,即使出版后,也未在西方學界引起足夠重視。直至1968年,羅斯多爾斯基首先對這一文本作出系統研究,并出版《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The MakingofMarx'sCapital)一書,這才引起西方學者對《大綱》的重視。就當時的反響來看,它在意大利產生的轟動效應尤為突出。由此,面對如此重要又有如此遭遇的文本,解密馬克思提出“一般智力”問題的出場語境、當代闡釋和真正意涵,就顯得十分重要。
一、“一般智力”的出場語境
在《大綱》第六、第七筆記本,即《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節中,馬克思指出“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會生產力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器官被生產出來”。〔2〕這是馬克思所有著作中,唯一明確使用“一般智力”的地方,但是同樣意思的表達不止此一處,如“勞動資料發展為機器體系,對資本來說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傳統的繼承下來的勞動資料適合于資本要求的歷史性變革。因此,知識和技能的積累,社會智力的一般生產力的積累,就同勞動相對立而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從而表現為資本的屬性,更明確些說,表現為固定資本的屬性,只要后者是作為真正的生產資料加入生產過程”〔3〕等。按常理說,從其出現的次數來看,它似乎并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概念。然而,它卻成為當下對《大綱》關注最多的地方,也是意大利自治馬克思主義者創新性闡發《大綱》的奠基性文本。
在后福特主義時代背景下,生命政治問題日益凸顯,“一般智力”的豐富內容及社會歷史作用,逐漸提升為學術研究的焦點問題。根據《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意大利自治馬克思主義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將這一手稿命名為“機器論片斷”。他們對這一部分內容興趣濃厚,甚至有學者將這篇手稿視為“圣經”,使“機器論片斷”的研究興起,代表人物有哈特、奈格里等。他們對這一問題再度被學界所重視,起到關鍵的作用。為何“一般智力”問題被如此重視?有雙重原因:一是《大綱》分析問題的風格及略帶原創性、論戰性和難以預測的開放性等特點。在這里提出問題,但未能明確說明如何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所以給后人預留了聯想及創作的空間,因而備受歡迎。二是鑒于馬克思被認為是有關資本主義崩潰理論和災難觀點的擁護者,《大綱》被認為是最適合重新闡發的基礎文本。在意大利,《大綱》正是以這樣一種獨特的方式被普遍接受。意大利自治馬克思主義者希望通過“一般智力”這一新的表現形式與資本助推的生命政治的關聯,推斷出馬克思“一般智力”的論述與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不符的結論,形成對馬克思在這一問題上的時髦批評。這引來大量學者沉迷于“一般智力”問題與大機器生產,及有關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預言性陳述。
為更好地理解“一般智力”問題,我們先對《大綱》在馬克思思想中的位置問題做一研究。總體上,學界有兩種觀點:有學者認為《大綱》僅是過渡文本,有其局限性。亦有學者認為《大綱》雖然未公開出版,但已有完整的思想,所以是一部獨立的著作。具體到《大綱》與《資本論》之間的關系問題,又形成三種不同的認識:一是羅斯多爾斯基,作為比較早地認識到《大綱》重要性的作者,在其代表作《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一書中,將《大綱》理解為《資本論》的準備材料。二是從工人運動中脫穎而出的奈格里,在其特別專著《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MarxBeyondMarx:Lessonson theGrundrisse)中對羅斯多爾斯基的觀點進行了嚴厲批評。他不同意羅斯多爾斯基將《大綱》理解為《資本論》的預備材料,認為這兩部著作在一定意義上是相互對立的,對立的焦點在于:《資本論》是“主體性”消亡的文本,而《大綱》則強調了“主體性”。從這一視角出發,奈格里認為《大綱》的方法就是“對立”。三是戴維·麥克萊倫(David Mclellan),作為《大綱》英文譯本的作者(晚于1971年),使讀者相信《大綱》已不限于作為《資本論》的草稿而存在,因為其綜合多種線索的分析,使《大綱》相比于馬克思的其他著作,成為馬克思著作中最完整的一部。〔4〕這也印證了1865年7月31日,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時強調的,無論其著作有何種優缺點,都不影響其作為“藝術的整體”。〔5〕這是符合馬克思本意的,不能因為《大綱》作為一部未出版的著作,就忽略這一文本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但是,麥克萊倫認為《大綱》是馬克思思想中最完整的著作,本文認為有待商榷,應該在更本質的意義上,完整把握從《大綱》到《資本論》的發展,準確定位《大綱》和《資本論》在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同時,應該運用歷史辯證法,揭示出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性邏輯和“主觀”性邏輯,為馬克思有關社會歷史變遷問題提供有益借鑒。這就是“一般智力”問題出場的語境。
二、“一般智力”問題的當代闡釋
馬克思關于“一般智力”問題的論述,引發西方學界持久關注,這與20世紀“技術決定論”的影響密不可分。這一觀點認為技術革命是影響資本主義的內源性因素,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力量。但對作為對資本主義作出最深刻批判的思想家馬克思來說,學界有兩種觀點:一種是指責馬克思在這方面的論述太少。另一種用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經常引來描述科學技術與社會歷史關系問題的經典表述“手工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予以反駁。但部分觀點卻導向另一極端,將馬克思視為“技術決定論”者。除此之外,還有待于我們在馬克思的學術語境中進一步闡發的是“一般智力”問題。馬克思關于“一般智力”與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問題,在當代西方學界引發了思想風暴。
一種觀點是20世紀60年代,哈貝馬斯繼承馬克思對黑格爾理論的批判性繼承,認為人的認識不是絕對精神自我運動的產物,而是斗爭實踐的產物,主體是能從事實踐活動的人。他認為,“在馬克思的闡述中,盡管包含著構成徹底認識批判的一切要素,但馬克思并沒有把它們綜合在一起,構成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哈貝馬斯認識到了“一般智力”問題在資本主義發展問題上的獨特性。從自然科學領域獲取技術作為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形成對自然發展規律的認識,這都是類自我產生的客觀關系。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同時反過來又對社會勞動體系起到反作用,并推動這一體系不斷發展。這一認識決定了社會主體之自我意識產生的過程,決定了社會主體在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形成,并開始控制整個生產過程。為加強對這一社會主體產生過程的論證,哈貝馬斯引用馬克思“一般智力”出場的原句作為例證,強調“一般智力”對于生產力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哈貝馬斯還引用《大綱》中,被稱為“一段不足憑信的論述”〔6〕:“……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消耗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動因的力量……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于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就擺脫了貧困和對抗性的形式。”〔7〕這段論述在《資本論》中同類問題的研究中再也未曾出現。作為研究相關問題時的一個必引的段落,哈貝馬斯在此強調勞動過程轉變為科學過程,再轉化為大機器應用的過程,借助社會勞動概念分析社會形式變遷的趨勢。哈貝馬斯將馬克思這里的論述解讀為技術史觀,是不全面的。但是,他用科技和階級斗爭的雙重維度來理解類自我產生的社會理論,指出只有在這些階級意識顯現的框架內,才能進一步分析生產的自然史,也只有在同階級對抗的客觀聯系中才能發展社會勞動系統,生產力同革命歷史相互影響的觀點是正確的。他看到了階級斗爭最終的結果是新的社會形式的形成的觀點,看到了生產力、生產關系等不同作用在資本主義起源、發展直至滅亡過程中的作用。尤其是看到了階級斗爭在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發展趨勢中的作用。哈貝馬斯的這一解釋是符合馬克思的觀點的,但更多是對馬克思理論的強調,并無太多創意。
另一種觀點,以意大利自治馬克思主義者哈特、奈格里等為代表。他們對“一般智力”與主體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重新闡發,指出《大綱》的重要性在于揭示資本主義導致利潤率降低、生產的關鍵環節由普遍智能主導的趨勢。這是一種不受任何物質束縛的知識,具有瓦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性。在這里,奈格里或許顯得過于積極。研究《大綱》的真實語境發現,馬克思論述機器、勞動以及資本關系時,認為機器是一種固定資本,重點依然是勞資關系。不同于馬克思從固定資本角度研究,奈格里認為它只是一種與活勞動相對立的對象化勞動。簡言之,馬克思基于客觀事實,研究機器與資本之間的關系。通過這一關系揭示出如何超越資本的邏輯。相反,奈格里從主體性視角出發,將機器置于勞動理論之中,以求得解放的渠道。這是二者相區別的關鍵之點。奈格里提出的所謂新革命主體,依然未能擺脫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機器大體系下勞資對抗的邏輯,因為新主體也只是跟隨勞動形態而作出重新調適,依然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之中。概言之,革命主體的生產邏輯和革命主體的重新界定不可分割。當然,如果拋卻革命主體的自我意識,則勢必會走向另一極端,如高茲“告別無產階級”的觀點就是典型。因此,奈格里從政治視角作出的創新性闡發,使馬克思“一般智力”問題,在當代再度被激活。奈格里試圖“超越馬克思”的嘗試,其實并沒有簡單拋棄馬克思。相反,是建立在對馬克思手稿的解讀(準確地說,是對手稿的重構)之上的。所以,最終仍然是“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
由上述兩種闡發可知,雖然“機器論片斷”寫于19世紀50年代,卻是當代西方思想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二者都從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主體生存狀況的揭示出發,看到技術與資本主義活力之間存在的聯系,是正確的。哈貝馬斯從認識論角度出發,得出資本主義社會中,主體、客體都依賴社會歷史的結論。指出馬克思在這里要做的是用自然科學的研究來論證社會發展規律的必然性。而意大利自治馬克思主義者通過“一般智力”范疇,重新激活馬克思勞資關系問題的研究。在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問題上,體現出未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理論的局限性。他們將“一般智力”擴大為“普遍智能”,勞動者已不再只是受命運驅使的生產者,更是一種與資本權力相抗衡的革命主體。對勞動者的這種雙重定位,不同于馬克思基于歷史事實,揭示勞動主體如何解放的可能性問題。在方法論上,與馬克思遵循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相悖。在《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導言”中,奈格里將《大綱》視為對資本主義發展趨勢有著非凡預言的文本。實質上,他們已脫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視角,僅將《大綱》解讀為政治文本。這一解讀的根源在于對“General Intellect”的翻譯。馬克思的“一般智力”是作為一種歷史性存在,而不是西方學者所指的普遍性存在的“普遍智力”。這促使我們回歸馬克思,重思“一般智力”問題。
三、馬克思“一般智力”問題的真正意涵
“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是《大綱》中一個獨特的范疇。依據文本主題,我們從四個維度展開詞源學考察。馬克思“一般智力”問題的研究,哲學維度上,受盧梭、亞里士多德的影響;政治經濟學維度上,受霍吉斯金的影響;工藝學、工藝學史維度上,受拜比吉、尤爾、波佩、貝克曼的影響;理論形成的時代維度上,受馬克思本人現實生活的影響。不同維度的思想資源,凸顯馬克思“一般智力”問題的復雜性和深刻性。具體闡述如下:
哲學維度上,意大利哲學家維爾諾(Virno)認為“一般智力”這個不明來源的英文(《大綱》原文寫作用的是德文)表達,可能是對盧梭“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的回應(Rejoinder),或者是主動努斯(Nous Poinsettias)的唯物主義重復(Echo),這是亞里士多德在《論靈魂》中討論的非個人和獨立的“主動理智”。〔8〕因為馬克思未能解釋其具體出處,維爾諾稱其為“來源不明”是可以理解的。但維爾諾將馬克思對這一問題域與西蒙棟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結合起來,創新性地提出“諸眾理論(Theory of Multitude)”范疇。通過資本主義由“形式吸納”(Formal Subsunmtion)到“實質吸納”(Real Subsumption)的發展歷程,提出“非物質勞動”理論。顯然是窄化了馬克思的“一般智力”在不同社會條件下的作用方式。從政治經濟學維度看,韋塞隆(Carlo Vercellone)發現馬克思在《剩余價值學說》中,認為霍吉斯金言及了“一般智力”的最初形態,指出霍吉斯金關于技能、知識等主觀性因素相比于客觀性因素有其重要性的認識,是馬克思形成“一般智力”問題研究的重要理論資源。〔9〕霍吉斯金在《通俗政治經濟學》(1827年)中確實認識到知識發展等主觀因素對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影響,并對政治經濟學家忽略腦力勞動等主觀因素的理論進行批判,指出“以往有關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書及其理論和基礎,未能對有關知識等主觀因素對生產力的影響進行完整論述”。〔10〕他以社會與個人關系的角度展開對“一般智力”問題的研究,使馬克思認識到社會個人發展的兩個不同方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僅僅作為資本的手段,是炸毀這一基礎的物質條件的本質。這是馬克思研究“一般智力”問題的直接來源。同時,馬克思還進行了工藝學維度的實證考察。從《評李斯特》到《大綱》直至《資本論》中,都可以讀出馬克思深受拜比吉和尤爾觀點的影響,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機器化大生產的重要來源。就“機器論片斷”而言,馬克思更是在開篇就引用拜比吉的《論機器和工廠的節約》(1832年)和尤爾的《工廠哲學》,他們從工藝學視角揭示出科學知識在工廠運用的原理,為馬克思從工藝學研究“一般智力”在機器化大生產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啟發。尤爾指出,“工場手工業以勞動分工為原則,即使每個人有著不同的才能,但在現代工廠制下,資本和科技合謀,使工人所能發揮的作用限于某一生產過程”。〔11〕由此,尤爾將現代工廠視為“由諸多機械的及附帶自我意識的器官構成的巨型自動機”。〔12〕其中“由諸多機械的及附帶自我意識的器官”,尤爾用“Mechanical and Intelectual Organs”表示。在馬克思研究“一般智力”問題時,直接轉引“這種自動機是由許多機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組成的”〔13〕的表述。除拜比吉、尤爾的觀點外,馬克思還摘錄波佩、貝克曼等的著作,他們對工藝學和技術等具體概念的區分,使我們窺探到工藝學和工藝學史對馬克思思想的影響。這一影響也可從馬克思的相關信件中看到。如馬克思寫信告訴恩格斯(1851年10月13日)“近來,我繼續上圖書館,主要鉆研工藝學及其歷史和農學”〔14〕等等。遺憾的是,尤爾和拜比吉也只是站在維護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作出對資本利益的辯護。馬克思與他們有著根本性區別。當然,也就不能把馬克思將研究視角拓展至不同研究的領域、各個具體知識的研究,混為研究方向上的根本轉變。否則,馬克思研究方向的“轉向”未免太多。另外,每一個理論的形成,都不可能脫離其生活的時代背景。如馬克思1851年參觀倫敦第一次世界博覽會之后,受這一經歷的影響開始研究工藝學。上述分析只是基于思想史所進行的一種可能探索,如果停留于哲學維度,就很難理解“一般智力”范疇的深刻意涵。雖然政治經濟學維度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資源,但是“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15〕所以,基于工藝學維度研究“一般智力”問題,是為多維度研究提供實證的依據,深化了馬克思對“一般智力”問題的考察。
在上述多重維度的影響下,馬克思深入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使“一般智力”的真正意涵逐漸明晰。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對這一問題的解答,已不局限于物質形式,還需要深入社會形式。只有兼具物質形式和社會形式,才能揭示機器大工業生產體系作為固定資本所具有的歷史變革意義。哈貝馬斯作為論據的必引段落,也正是強調“一般智力”對于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作用,貌似與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相異。但事實上,馬克思的分析正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從敘述方法看,馬克思是基于機器體系來揭示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其論證思路貌似為:機器體系使得財富的源泉不再僅僅依賴直接勞動,所以商品價值的決定就不僅是生產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使用價值的評價尺度,也就不僅是交換價值,由此推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交換價值的崩潰趨勢。這是當代西方學者的故意誤讀。從研究方法看,馬克思的研究有著完整的論證體系,論證的關鍵是明確機器體系不是自一開始就作為固定資本而存在的,所以對其社會歷史意義的認識,不限于技術史觀的理解。馬克思要揭示的是“由資本的總過程決定的特殊的資本存在方式——固定資本”,〔16〕而不是自動機器體系僅僅作為勞動資料而存在的過程。所以,他不僅是研究作為勞動資料的機器體系,他的重點是作為固定資本形式的存在。正如后來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強調的,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他要揭示的是這一生產方式下作為固定資本的機器體系與勞動者之間的對立關系,這才是在這一節中,理解“一般智力”問題的關鍵所在。
四、結語
馬克思之所以關注“一般智力”問題,除了看到資本主義帶來的生產力發展的偉大歷史功績外,更看到了機器大工業和自然科學在生產領域的應用,是解放社會的前提。但是,馬克思并不是知識或技術決定論者,而是探討“一般智力”對社會生產力的影響,并力圖依據不同的生產力形式推進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馬克思的“一般智力”問題應放置于資本主義社會構建的整體語境中。當意大利自治主義將“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一節命名為“機器論片斷”時恰恰忽視了其中蘊含的社會關系溫度,是不完整的。一方面,技術確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帶給我們的影響已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代;另一方面,在被技術、資本裹挾時,貫穿馬克思理論始終的任務是超越資本,實現真正的解放,這在當代依然有效。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我們絕不能因為機器體系是固定資本的使用價值最適合的形式,就認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就是最適合機器發展的社會關系。相反,我們必須從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出發,考察機器和資本邏輯的發展趨勢。馬克思認識的深刻之處正在于:認識到資本主義恰恰會阻礙機器化大生產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經濟危機,造成生產力浪費。同時,在資本邏輯內部蘊含著自由的邏輯,蘊含著摧毀異化物和物化社會關系、使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獲得解放的力量。
2008年,新自由主義主導之下的資本主義發生金融危機時,民眾運動并未沿奈格里的路線進行。反思重新建構的革命主體路線的同時,哈特、奈格里再度聯手出版新書《集會》(Assembly)(2017年)。囿于他們去組織化、去領導化的路線未能得到充分論證,所以他們對“機器論片斷”的闡發雖有其邏輯,但未能真正觸及資本關系的實質,使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邏輯不能自洽。而且因過于強調主體性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資本主義可能滅亡的客觀歷史基礎,令其理論勢必走向虛空。馬克思深入資本主義的本質,從固定資本與勞動關系出發,解釋社會形式的變遷,依然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框架中。他認為,“一般智力”所帶來的生產力變化,引起生產關系的變更的矛盾,才是最終導致資本主義消亡的邏輯。哈貝馬斯的認識基本符合馬克思的論述,馬克思也正是在主客體相統一的基礎上展開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的,這是我們重思馬克思“一般智力”問題得出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