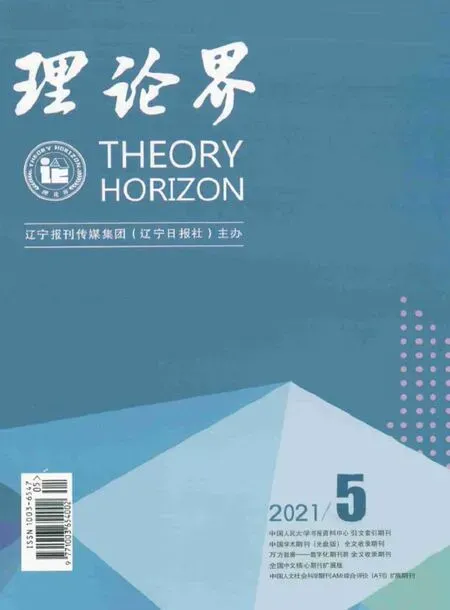走出決定論的困境
——論柏格森的自由觀
鄧 剛
一、引言
1889年出版的《論意識的直接材料》(Essaisurlesdonnéesimmédiatesde laconscience)是柏格森的成名作,英文本書名改為TimeandFreeWill,德文本書名譯作ZeitundFreiheit(時間與自由),中譯本的書名依照英文本譯為《時間與自由意志》。正如書名所示,自由是這本書的核心問題之一,并且自由與時間相關。在柏格森看來,在西方哲學史中,人們之所以常常陷入自由與決定論的二律背反之難題,原因在于人們總是在空間中而非在時間中來理解自由。柏格森對時間、空間都進行了反思,從而提出綿延的概念,并從作為真正的時間的綿延出發來重新把握和反思自由。正如法國學者維亞-巴隆所指出的:“柏格森哲學的起點是一種拒絕:也就是說,科學決定論及其實證主義詮釋,都錯誤地否定了人的自由。”〔1〕柏格森在此書中的目的之一,在于重新肯定自由。這種重新肯定不同于康德。康德將自由視為理性的一個理念,即在經驗的現象界之外的本體界中的理念,并且與“上帝存在”“靈魂不死”一起作為純粹的實踐理性得以可能的三個公設。然而這樣一種自由,卻無法通過經驗加以闡明,因為“自由是這樣一個理念,它的客觀實在性不能以任何方式按照自然法則來闡明,從而也不能在任何可能的經驗中被闡明”。〔2〕不同于康德,柏格森認為可以從經驗來闡明自由,但是不能從自然科學所理解的經驗出發,而是應該從綿延經驗出發。因為只有從綿延出發,才有可能真正地把握時間、自由以及實在本身,而以空間化為基礎的科學經驗實際上只是綿延經驗的一種變體。
二、對物理決定論的批判
柏格森在《論意識的直接材料》一書的第一章、第二章,分別闡述了強度、眾多性、綿延等概念。柏格森指出,通過反思強度這一概念,將會發現強度無法被量化,而是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眾多性,而眾多性又可分為兩種,即可以并排列置的眾多性和互相滲透的眾多性,從而引入了綿延概念,以及空間與綿延之對立。真正的時間應該是一種綿延,但人們的日常思維方式總是習慣于在空間中來理解時間。而在第三章中,柏格森在綿延等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從綿延出發來重新思考自由問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和康德一樣,柏格森的論爭對手,是形形色色的決定論,這些決定論可分為兩大類:物理決定論和心理決定論,而物理決定論最終又可以歸于心理決定論。
柏格森指出,物理決定論就其最嚴格的形式而言,以某種物質理論為前提,這種理論認為物質是無數基本粒子的集合,而這些基本粒子本身有著振動、位移等運動,而感官所能夠觀察到的一切物質現象,如顏色、光、熱等,最終可以歸結為基本粒子的運動,并最終服從嚴格的力學規律。如果將這種觀點擴展到對于人的生命和意識的解釋,可以得出以下推論:人的一切意識狀態,對應于人的神經及大腦皮層的某種變化,最終也可以歸結為物質粒子的運動。這一理論,看似完美而自洽,但遠遠不足以真正地解釋事實,而只是一種科學的假設,本身就已包含某種形而上學的前提。“簡言之,凡在我們能提出機械說明的地方,我們就看出生理現象和心理現象之間有著相當嚴格的平行發生……但把這種平行發生推廣到整個的各系列自身上去就是對于自由這個問題加以先天式的解決。……他們所以肯定在意識狀態和廣度式樣之間有著嚴格的相應關系并不是為了物理上的理由。”〔3〕柏格森認為,在心理和生理之間建立平行關系,乃是出于形而上學的理由。〔4〕正是斯賓諾莎、萊布尼茲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對于這種身心平行論作了最為深刻和最為嚴格的表述,而科學家往往都未曾達到二人的理論高度。物理決定論的最大錯誤,在于將物理主義不合法地擴張到人的意識領域,要使這種擴張成為可能恰恰需要一種心理決定論。
當然,也許有人反駁說,如果僅僅采取一種外部觀察的視角,僅考慮其外部行為,暫時不顧及其內心活動,在這種情況下,似乎物理決定論是可以成立的。在這種情況下,人的行動很難說是自由的,并且人的行動也必須遵循物質世界的規律,例如能量守恒定律等。柏格森指出,即使能量守恒定律,也只是物理學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形成的假設,將其設定為一切科學研究都必不可少的設定,這是缺乏依據的。能量守恒定律,表達的也只是一條重要的思維規律:“給出的就是給出的,沒給出的就沒有被給出”,即有者恒有,無者恒無,無不能生有,有也不會憑空地消失為無。一切科學都服從這條規律,然究其實質只是矛盾律而已。這條規律告訴我們,“無不能生有”,因此,每次經驗和觀察讓我們發現某種新出現的質或者量,我們都必須設定這個新出現的質或者量,一定來自某處,而不是憑空產生的。然而,哪些量被我們注意到,哪些量被我們忽視,其實取決于我們的觀察、興趣,以及我們開展認識和實踐活動所依賴的工具。柏格森寫道:“只有經驗才能告訴我們:從實證科學的角度看,在實有界的各方面和各作用中,哪些必得算作有,哪些必得算作無。”〔3〕對象的哪些方面可以算作實有,實有如何被測量和計算,也取決于經驗。因此,盡管在科學研究中,人們習慣性地設定能量守恒定律作為前提,但這個假設并非必然。而且,在笛卡爾和萊布尼茲之前,科學家并不知道能量守恒定律,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在科學上探索出一些新的發現。
柏格森進一步指出,能量守恒定律還在于以下信條,即每一個物質的點,在經歷了一定位移之后,仍然能夠返回其初始位置。在此假設中,時間其實不起作用。只要某物經歷了從A點到B點的運動,此運動用一秒鐘完成或一小時完成,其實無關緊要。在純粹物質的領域,是沒有綿延的。然而,在生命的領域,情況卻有所不同,因為生命活動有其固定節奏,無法加速,無法逆轉。有人反駁說,由于生命體內部的分子太多,因此,讓所有的分子都返回原初位置,雖無實際上的可能,但有理論上的可能。柏格森指出,至少在意識的領域,這種返回原處的假設是無法成立的。一種感覺,只要時間上略加延長,就變異為另一種感覺。例如,用1分鐘聽莫扎特,與連續5分鐘聽莫扎特,所獲得的感受必然是不一樣的。因此,對于生命體、對于意識,過去就應當被視作某種現實。“機械學所謂的物質點永遠處于現在這一剎那;那就一般生物而論,過去也許是真實的,就有意識的人類而論,則過去確定是真實的。……如果有人提出一種假設,認為意識力或自由意志是存在的,認為這種力或意志受著影響,并把綿延儲藏起來,從而也許不必遵守能量守恒定律,那么這種假設難道不是有許多可取的地方嗎?”〔3〕也就是說,和康德類似,柏格森可以承認,在物質領域,機械規律仍然有效;但是在生命的領域,特別是意識的領域,則有著自由意志。如果僅限于此,則柏格森的觀點仍然只是一種防御性的觀點。然而,柏格森并未停留于此,而是進一步指出,能量守恒定律僅僅適用于物質領域,若將其用于心理領域則是一種錯誤:“因為我們不慣于直接觀察自己,而通過我們從外界借來的形式以觀察自己。”〔3〕由于這個原因,人們就習慣于用物理的方式來看待和研究心理的東西,并且將心理序列的東西和物理序列的東西看成一樣的,想象人的意識其實是由無數個基本的意識狀態(基本粒子)通過某種特定的方式組合而成,因而這些意識狀態可以返回原處,接受意識或者理性的考察或者整理,而這正是19世紀的心理主義、聯想主義的錯誤,因此,柏格森要進一步對心理決定論進行批判性考察。
三、對心理決定論的批判
在柏格森所生活的19世紀末,心理決定論在心理學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其代表性的流派就是聯想主義心理學,即在哲學上以休謨、密爾等人為代表的英國聯想主義。這一派的觀點,可以歸結為將心靈視為無數個原子般的心理狀態的集合,每一個當下的心理狀態,都被之前的一系列狀態所決定,但每個心理狀態彼此之間,卻有著質的區別。當我作出一個行動,這個行動作出之前,其實在我心中有若干種處于競爭的心理狀態,但其中某一狀態以其強度占了上風,取得支配地位,凌駕于其他狀態之上,并且領導著其他狀態,從而引導我作出了該行動。對于人的心靈以及人的意識狀態的這樣一種看法,不僅是聯想主義的共識,也是許多反對聯想主義的哲學家所接受的。而之所以會出現這些錯誤,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咎于語言:“雙方都陷入了一種來自語言的混亂,這混亂的本源在于這個事實:語言本來不是為了表達內心狀態的一切微細分別的。”〔3〕
柏格森舉了幾個例子來反駁聯想主義:(1)交談的雙方。比如說,有兩個朋友一起談論一些話題,如天氣、氣候、時事、財經、家庭等。盡管外在地看,兩人共同談到一些話題,并且這些話題前后相續,形成前后銜接的因果系列。按聯想主義的邏輯,我們之所以談到氣候,是因為之前談到了天氣,而之所以現在談到了家庭,是因為之前談到了財經的走勢,而財經的走勢又受到時事的影響,如此可以將原因追溯到第一個話題:天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兩個人談到家庭時,兩人可能都將當下的話題與之前的某個話題聯系起來,然而兩個人腦海里想到的卻是不同的事情。(2)一個人站起來去打開窗戶,然而在站起來之后,他忘記了他行動的目的,于是呆立在那里。原本有兩個觀念,一個是想要去實現的目標,一個是實現這個目標所需要的與之對應的動作。由于前一個觀念消失了,現在只剩下后一個觀念。當前一個觀念消失,我們行為就由去開窗的行為轉變為起身站立的行為。從行為的性質來說,其實完全是兩種不同的運動。但是,從聯想主義的觀點看,這個起身站立的行為,可以隨時續以不同的目標行為,從而就成為開窗戶的行為、從書架上取書的行為、在柜子里取酒瓶的行為等等。聯想主義把行為轉化為時間上的點和空間中的軌跡,從而隨時可以接續上新的目標、新的后續行為。然而,聯想主義的錯誤正在于“它首先把這動作的性質因素去掉,而只保留了幾何學式的和不屬于任何私人的因素”。〔3〕(3)嗅玫瑰。每一個人在嗅玫瑰時,都可能引起不同的回憶,這些回憶或多或少,或清晰或模糊。而日常語言,只能表達玫瑰香味的客觀的方面、空間的方面。
柏格森指出,聯想主義之所以會出現這些錯誤,首先是因為他們混淆了兩種眾多性的區分,即并排列置的眾多性和互相滲透的眾多性。這種混淆有著極深的根源,甚至就代表著人們日常思維的方向,因為設想一個均勻、單質的場域(比如空間)的能力與用普遍概念進行思考的能力是緊密相關聯的。當人們試圖去分析、描述一個意識狀態時,其實已經是將這個狀態從某個總體中抽出加以考察,而沒有注意到這個狀態本來是和其他狀態一起,以互相交織、互相滲透、彼此交融的方式處于這個總體之內。因此,“聯想主義的錯誤在于把哲學家所提出的人為復制物代替心靈中所發生的具體現象,在于把關于事實的解釋跟事實自身混淆在一起”。〔3〕柏格森強調,聯想主義心理學帶給我們的是關于現象的一種描述,而并非現象本身;是一種通過象征、符號、語詞等進行的外在描述,而不是對于現象本身的直接把握或者整體把握。要更清楚地說明這一點,需要引入關于更深層的意識現象的考察。
四、自我與自由
柏格森接下來引入自我的概念。自我與世界發生接觸,外物通過感官給自我留下各種印象,這些印象并排列置,構成自我的表層。僅僅觀察這樣一些狀態,聯想主義學說大體上還是適用的。但是,如果從自我的表面往下沉,下沉到意識的深處,下沉到深層自我,就會發現這些意識狀態是彼此交融、互相滲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一個狀態同時渲染著別的狀態。例如,每一個人在愛、恨等情感中,各自有其獨特的去愛、去恨的方式、姿態、風格,然而人們卻只能用同樣的語詞,來描述和稱謂所有人的愛和恨,而忽略了每個個別的人獨特的樣式。因為“愛”“恨”“喜歡”“怨”等一些語詞,描述的是所有人共有的一些行為、心理的特征,只能描述一些非人格的、抽象的、普遍的東西。我們可以用無數多的語詞來描述一個人、一個心理狀態、一種心情,但所有這些描述都無法將其獨特性完整地再現。這就如同在兩點之間有一條線段,人們可以用無數個點來代替這個線段,但所有這些點都無法最終代替這個線段,而只能做到大概的近似。因為在點與點之間,總是存在空隙,從而可以增加無數個新的點。通過聯想主義的方式來考察所獲得的自我,其實只是自我在空間中的投影,只是自我的一個影像,只是“一個幽靈自我(Un MoiFant?me)”。如果能夠持續不斷地深入真正的自我之中,進入那深層的自我,那個基本自我(Moi Fondamental),將會發現所有的意識狀態都只是這個唯一的自我的某種表現、某種狀態、某種呈現,這個基本自我將這些狀態都包含在自身之中,并且在自身之中使得這些狀態互相滲透、彼此交融,從而形成一個整體。“這個內在狀態的外部表現恰恰是所謂的自由動作,因為只有自我是這動作的創作者,又因為這動作把整個自我表示出來。照這樣解釋,自由并不總是呈現為絕對的,像精神論者(Spiritualistes)所認為的那樣;自由可以有程度上的差異。”〔3〕也就是說,依據自我被呈現為表層的自我或基本自我,就關于自由的兩層不同理解。當自我感知一個同質化的空間,自我就上浮到其表面,這時自我就呈現一個又一個的狀態或者情緒,如同水面上漂蕩著一些浮萍。這樣一些浮萍,就如同在基本自我之上,添加了一個寄生的自我(Moi Parasite)。對于凡俗眾生而言,都受制于這種寄生的自我,從而不曾真正地領會到自由。“這樣,在基本自我之內有了一個寄生的自我,而寄生的自我不斷地侵犯基本自我。許多人過著這種生活,到死也不曾有過真正的自由。”〔3〕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那就是從表層自我深入下去,下潛到人的心靈深處的基本自我,從而讓人們的決定和行動體現人的整個人格、自我、靈魂。“事實上,引起人們作出自由決定的正是整個的靈魂。有一個動力式的系列跟動作聯系在一起,這系列越能代表基本自我,則動作越是自由的。”〔3〕在行動發自人的基本自我的情況下,行動就成為其人格、個性的表達:“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所做的動作并不表示一個膚淺的、幾乎處于我們的、清楚而易于說明的觀念;所做的動作符合我們全部最親切的情感、思想、期望,符合那能代表我們整個過去生活的人生觀,簡言之,符合我們個人關于幸福與榮譽的看法。”〔3〕與之相反,決定論者之所以未能認識到這種自由,是因為決定論者對于人的靈魂有一種機械論的看法,停留在表層自我,停留在意識的表面,并且把意識表象為多種狀態、多種觀念并排列置、互相競爭、彼此沖突的一個舞臺、一個場域。因此,柏格森總結道:“總之,當我們的動作出自我們的整個人格時,當動作把人格表現出來時,當動作與人格之間有著那種不可言狀的相像,如同藝術家與其作品之間有時所有的那樣時,我們就是自由的。”〔3〕
在柏格森看來,在西方哲學史的傳統中,無論是反對自由意志的決定論者,還是支持自由意志的哲學家,都分享著共同的錯誤,即在空間中來把握綿延和自我,從而或者將心靈看作完全服從外部物質世界的機械規律,或者將自由意志視作一種能夠在多種可能性之中進行選擇的能力。用密爾的話來說:“覺得意志是自由的一定就是這個意思:覺得我在作出決定之前先能夠選擇兩種可能之中的任何一種。”〔3〕在決定論者看來,在一系列的前件之后,接下來會出現唯一可能的后續行為;而在自由論者看來,在同一系列的前件發生之后,接下來可能會出現多種可能的后續行為。也就是說,在前者看來,前件一旦給出,后件將是唯一的。而在后者看來,前件被給出之后,后件并非唯一,而是有著多種可能的。
柏格森指出,人們通常所理解的自由表現為:“在兩種可能的行動X和Y之間,我游移不決,一會兒選擇X,一會兒又選擇Y。這就是說,我經過一系列心理狀態,而這些狀態可分為兩組,看它們是我傾向X時或傾向Y時的狀態而定。”〔3〕柏格森指出,這里的X或者Y只是一種象征的說法,應當理解為自我的兩種趨勢或傾向,而并非果真有兩個確定的X或者Y擺在我的面前。對于常識而言,往往認為在自己面前擺放著兩種或者多種平行的可能性。在柏格森看來,這樣一個想法,其實是在想象中設想到最后的動作,并且將過去、現在、未來放在一起,并且使之在空間之中展開。然而,對于一個已經完成的動作,是不可能在同一時間里同時完成兩件事情的,因為現實中,自我接下來要么走到X點,要么抵達Y點,而不可能同時完成兩個方向。因此,以下情形才接近真實:自我先走了O點,接下來又走到了X點,然后又走到了Y點。〔3〕
在柏格森看來,以往的心理學和形而上學,往往未能擺脫三種錯覺:(1)把強度當作心理狀態的數學特征,而忽視其性質。(2)拋棄意識所覺察到的具體實有或動力式進展,而把這進展在它已到達終點時的物質性象征當作代替品。(3)混淆時間和空間,總是把時間中的東西在空間中的投影當作時間中的東西本身。正因為這樣一些混淆,處在常識中的人們,其實并沒有真正地觸及自由問題。然而,科學作為常識的延伸,強化和固化了常識的思維方式,使得人們在空間化思維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種常識最終訴諸一種對因果關系和同一原理的信任。柏格森寫道:
因果關系是一種必然關系;……這關系會無窮地接近于同一關系,如一條曲線幾近于它的漸近線一樣。同一原理是我們意識的絕對規律,這原理肯定:被思考的東西,在人們思考它之際就是被思考的;這原理所有具有絕對必然性乃是由于它沒有把未來跟現在聯在一起,而只把現在跟現在聯在一起;這一原理表達的只是意識對其自身的信心……但是,因果原理,就其把未來與現在聯接在一起而言,從來都不具備某種必然原理的形式;因為實在時間的先后瞬間并不是彼此聯在一起的,而任何邏輯上的努力都無法證明,同樣的前件永遠可以引起完全相同的后果。〔3〕
也就是說,只能保證現在與現在的同一性,而且這種同一性本身實質上也并不具有絕對的必然性,其實只是意識對意識自身的一種信心和確信。而過去到現在、現在到未來的聯接的必然性,則完全不具備必然性,實際上在哲學史上,休謨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柏格森特別指出,笛卡爾實際上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難題,因此,笛卡爾認為物理現象的恒常性是由于上帝的持續不斷地賦予世界恩典來保證這種恒常性。
五、心理學因果性與意志理論
在批評了傳統的因果性觀念之后,唯一的理論出路就在于,是否存在一種不同于物理因果性的心理學因果性。柏格森指出,存在一種內在因果性,“內在的因果性是完全動力式的”,即通過綿延等概念來描述或者暗示的通過意識活動本身所呈現的因果性。柏格森在1903年2月26日寫給布朗什維格(Léon Brunschvicg)的信中指出,“或者自由是一個空洞的語詞,或者自由就是心理學因果性(Causalité Psychologique)”。〔5〕心理學因果性不同于物理因果性(Causalité Physique)。物理因果性意味著,一切服從數學化的決定論,一切皆不過是既有物質的重新組織,一切皆服從物理學法則。而心理學因果性,則意味著有某種新的東西的出現和創造。
關于心理學因果性,柏格森在1906—1907年的法蘭西學院課程“意志理論”中作了更為充分的解釋。他首先區分了兩種因果性,機械因果性(Causalité Mécanique)或動力因,理智因果性(Causalité Intelligente)或目的因。在此之外的第三種,則稱之為心理學因果性或者心理因果性(Causalité Psychique)。〔5〕柏格森將三種因果性歸結為三種不同的努力(Effort)。〔5〕機械因果性對應肌肉的努力;理智因果性對應某種注意的努力;而心理因果性則關涉一種意愿決策的努力。因此,需要聯系柏格森的“意志理論”來理解這種努力。
在這篇課程之中,柏格森首先指出,關于意志這一復雜問題,有兩個極端的立場:一是叔本華的立場,將一切意識視作意志的表現;二是決定論特別是機械論的立場,明確地排斥意志自由。要真正地面對意志問題,首先要解決的其實是這樣的問題:在機械論之中,是否有斷裂?是否有某種“自行生成的”東西偶然地出現在世界之中?這才是整個心理學背后的東西。然而,這是一個極大的難題,因為在心理學中,我們并不知道我們的心理學分析是否完備,即我們對于人的心理活動并沒有完備的知識。柏格森則主張世界本身就存在某種自行生成,使得機械論成為可能。也就是說,實際上是心理因果性使機械因果性和理智因果性成為可能。而要理解這種心理因果性,就要聯系柏格森所說的綿延、時間、生命、創造等概念。
六、小結
總體說來,柏格森認為如果綿延、運動、變化是一種真實的、無法否認的存在,那么自由也是這樣一種存在。他寫道:“自由乃是具體自我對于它所做動作的一種關聯。這種關系是不可被界說的,恰恰因為我們乃是自由的。”〔3〕因此,自由是一個事實。在《論意識的直接材料》一書的結論部分,柏格森再次強調關于自由、綿延等之所以會形成這樣或那樣的理論難題,在于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方式,即常識的思考方式,而科學、康德哲學仍然未能完全擺脫常識。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都是用借自外部世界的方式來考察人的內心世界,當然也就無法真正地,如其所是地把握內心世界。但是,一旦人們能夠通過直觀把握到內心的綿延,從綿延來把握自我,就能夠把握到自由是一種可以體驗到的事實。關鍵不在于從基于決定論的科學與物理世界出發,來說明自由如何可能,而是反過來,應當從意識、綿延、自由出發,來重新觀看和考察世界,并進一步說明決定論如何可能。柏格森哲學及其綿延觀和自由觀,對于20世紀法國哲學產生了巨大影響,薩特、梅洛-龐蒂、德勒茲等人都深受柏格森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