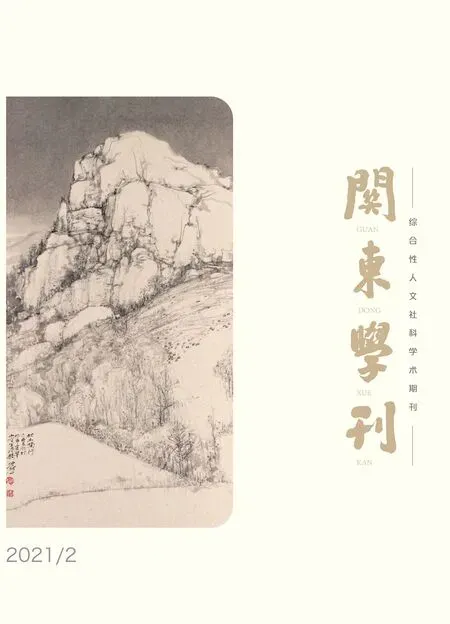賞鑒與著錄:中國古典書論在明代的完善
朱天曙
中國古典書論在明代的發展是和明代書法藝術的發展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明代初期,宮廷臺閣體書風盛行,宋克一脈文人書風延續著元代后期的風氣,并在章草、小楷書風上有新的開拓。尤其是宋克在章草上的復興,開啟了明人探索草書的新風氣。明代中期起,蘇州地區又形成了以文徵明、祝枝山、陳淳、王寵等為代表的“吳門書派”,在書法創作上突破元人趙孟頫的籠罩,取法晉宋書風而有了新的發展。同時,江南一帶鑒賞書畫和清玩的風氣盛行,他們在書畫活動中,形成了一套鑒賞、玩閱、收藏、著錄、研究的傳統,大大豐富了書法創作之外的內容。在書法理論上,明代除了魏晉以來傳統的筆法理論外,又在這種大的文化環境中興起了一種文人雅玩和賞鑒的新理論,這種理論是在北宋文人書法風氣以來的又一次新的開拓,構成了明代書論的重要特色。
一、從技法理論到學書的“體系化”
元代出現的以陳繹曾《翰林要訣》、溥光《雪庵字樣》等傳授書寫技法為代表的理論書影響到明代初期。這種從書法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實用的學習方法,在宮廷臺閣中得到流行,形成了以中書舍人為代表的“臺閣體”,適應宮廷詔敕和謄寫文件之需,書寫工雅的楷書。這一時期,姜立綱《中書楷訣》一書影響很大,他用圖例指示人們學習以“永字八法”為基礎的“間架結構八十四法”,是明代宮廷較為實用的技法理論書。明代初期的許多臺閣體書家,就是在這一類楷訣書影響下書寫的,多數刻板平正,缺少文人趣味。此外,李淳《大字結構八十四法》,專論題署,擘窠大書之法,每法取四字為例,加以說明。這種通俗的技法書,從元代開始流行,一直延續整個明代。
《書訣》一書是明中期豐坊論學書之法的一部書,具體是解說筆法傳授中的“雙鉤懸腕”法。他認為:“雙鉤懸腕者,食指中指圓曲如鉤,與拇指相齊而撮管于指尖,則執筆挺直,大字運上腕,小字運下腕,不使肉襯于紙,則運筆如飛。”(1)韋坊:《書訣》,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第505頁。“讓左側右者,左肘讓而居外,右手側而過中,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側行間直下而無敧曲之患。”(2)韋坊:《書訣》,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第505頁。“虛掌實指者,指不實則顫掣而無力,虛則窒礙而無勢,妙在無名指得力,三指齊撮于上,而第四指抵管于下。”(3)韋坊:《書訣》,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第505頁。“意前筆后者,熟玩古帖,于字形大小、偃仰、平直、疏密、纖秾、蘊藉于心,臨紙瞑墨,豫思其法,隨物賦形,各得其理。”(4)韋坊:《書訣》,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第505頁。這類討論集中在書寫技法中的執筆、運筆、字形、筆意等內容,是唐代以來關于技法理論的延續。
和豐坊《書訣》重技法討論不同,明代還有以《書法雅言》《書法約言》《寒山帚談》等為代表的一批重要書論,注重從書法學習的整體觀照,從技法臨習到古帖品鑒,再到精神體驗,是“體系化”的書論,獨立成篇,體系完整,在明代書論中有鮮明的特點。
《書法雅言》是明代嘉興著名書畫收藏家項元汴之子項穆所撰的一部書。此書包括“書統”“古今”“辨體”“形質”“品格”“資學”“規矩”“常變”“正奇”“中和”“老少”“神化”“心相”“取舍”“功序”“器用”等內容。項穆對書法進行了全面考察,不是單純講解技法和品第,而是深入地觸及了書法的本質問題。全書受唐代孫過庭《書譜》的影響,貫穿著“中和”的思想,主張雅正,以王羲之為正宗,主張“古今論書,獨推兩晉,然晉人風氣,疏宗不羈。右軍多優,題材獨妙。書不入晉,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詎稱逸品。”(5)項穆:《書法雅言》,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第521頁。對宋人以后的蘇軾、米芾進行批評,以為“蘇、米之跡,世爭臨摹,予獨哂為效顰者,豈妄言無謂哉!”(6)項穆:《書法雅言》,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第532頁。這有針砭時風的意義。明初繼承元人書風,中期學宋人,缺少平和中正的審美,這正是項穆提出“中和”的原因所在。
項穆還突破前人的品評方式,把書法分為正宗、大家、名家、正源、旁流五個等級,突出師法正宗在學書中的意義。他還把書法作品分成六個等級,即老少中和、少兒老成、老少兼有、有老無少、有少無老、不知老少,主張“玄鑒之士,求老于典則之間,探少于神情之內”,認為沒有規矩的絢爛,不如有規矩的平實。還主張“規矩入巧,乃名神化”,主張要達到“神化”之境,首先應做到“精熟”,然后是“定志”“養氣”,還主張“正書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閑圣道也”(7)項穆:《書法雅言》,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第513頁。。項穆的書論受理學思想的影響很深,強調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中和之美,提出了書法人文和哲學品格中的諸多共性問題,雖顯得有些守舊,但是其終生研究書道的經驗之論,核心思想仍有很多積極意義。
明末鹽城人宋曹所著《書法約言》是一部從創作角度討論書法的重要書論,內容分“總論”“答客問書法”“論作字之始”“論楷書”“論行書”“論草書”,涵蓋各種書體的技法、臨摹、創作、審美、流變等內容。宋曹論書從他的創作實踐中來,切實精到,主張“學書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轉腕,手能轉筆。大要執筆欲緊,運筆欲活。手不主運而以腕運:腕雖主運而以心運。”(8)宋曹:《書法約言》,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第563-564頁。他詳細解釋了由心悟而學書之法,主張“作楷者須令字內間架明稱,得其字形,再會其法,自然合度”(9)宋曹:《書法約言》,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第569頁。,“凡作書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運心,神采生于運筆”(10)宋曹:《書法約言》,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第570頁。,他認為“古人之神”是一種古法,取“古人之神”不能一味的模仿古法,要自出機軸,使古法優游筆端才能“傳神”,“形與心手相湊而忘神之所托”。他對具體書體也提出了個人經驗,如“作行草書須以勁力取勢,以靈轉取致”(11)宋曹:《書法約言》,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第572頁。,“勢”和“致”是書法中的兩個方面,不能偏廢,這些看法對書法創作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明末太倉的趙宧光《寒山帚談》是他討論書法的名篇,多有精義。此書內容分為上、下兩卷,上卷“權輿”論十五種字體,“格調”論筆法結構,“學力”論字之功夫,“臨仿”論臨摹法書;下卷包括“用材”論筆墨紙硯,“評鑒”論辨識淺深,“法書”論古帖,“了義”論書家秘訣。趙宧光精通文字學,曾有《說文長箋》問世。因而他討論書法,主張以篆書作為書法的根本。他在《權輿》篇中稱:“大篆敦而圓,骨而逸;小篆柔而方,剛而和,筋骨而藏端楷,籀則簡縮,斯乃舒盈,書法至此無以加矣。”在他看來,篆書無論大篆還是小篆,都是書法的極則,學習書法必須尊古,了解的篆書,才能把其他書體弄明白,篆書“上以溯古,下以通時”,學習書法要取法乎上,求得本源。“求帖先尋古文篆隸,始可窺張、鐘秘奧。得張、鐘而后可以別二王優劣,優劣渾渾,勿與說書。”(12)趙宦光:《寒山帚談》,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第324頁在他看來,要理解二王,也要從篆書入手。
趙宧光在《寒山帚談》中還專門設有《格調》篇,吸收了明代前后七子在文學上的格調理論,提出書法上也有“格調說”。他認為,“格”指能得古人氣格法度,“調”指能得運筆、結體、布局之方,“格”要尚古,“調”要尚逸。他在《格調》篇中說:“取法乎上,不蹈時俗,謂之格;情游物外,不囿于法,謂之調。”他認為,鐘王并稱,鐘有古法,富有古意,因而鐘以格勝,王有新法,富于個性創造,因而王以調勝。趙宧光還從用筆和結構兩個方面對書法的“格調”加以討論。他主張用筆為體,結構為用;用筆為情,結構為性。用筆要圓,有韻度,由識取實;結構要方,有骨力,由學取虛。在“結構”上,又分“結”和“構”,主張學書從用筆來,先得結法;從措意來,先得構法。“構”為筋骨,“結”為節奏,“有結無構,字則不立”,“有構無結,字則不圓”,只有“結”和“構”結合,才能得古人的精神。
在《寒山帚談》的《法書》篇中,趙宧光認為“晉人以無意得之,唐人以有意得之,宋、元諸人有意不能得。今之書家無意求,亦不知其所得者何物?”(13)趙宦光:《寒山帚談》,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第325頁。又說:“不學唐字無法,不學晉字無韻。不惟無韻,且斷古人血脈;不惟無法,且昧宗支家數。謂晉無法唐無韻,不可也;晉法藏于韻,唐韻拘于法。能具只眼,直學晉可也;不具只眼而薄唐趨晉,十九謬妄。”(14)趙宦光:《寒山帚談》,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第325頁。這些見解把晉唐和宋元書家之別作了明確的區分,很有見地。
二、明代名家的書法品評
明代書論,多重魏晉書風,而趙孟頫為取法晉人之代表,因而受到重視。明人力求書風遒媚與骨力,既有強調在規矩中求古人精神的內容,又有主張擺脫傳統束縛,標舉天趣,表現自我的理論。其中較有影響的是解縉、文徵明、祝允明、何良俊、王世貞、李日華、徐渭等人。
元末明初解縉《春雨雜述》中,論書法的有“學書法”“草書體”“評書”“學書詳說”“書學傳授”等。他認為書法有“用大”和“小用”之分,“小用”是個人的藝術,“用大”則是為國家、為宮廷服務。學習書法的方法如果不靠口傳心授,就不能得其精妙之處。必須依靠書法傳授的傳統才能學習好。像古人那樣努力下大工夫,才能達到精熟的程度。如孔子的弟子學習孔子那樣,“愈近而愈未近,愈至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治之已精,益求其精。一旦豁然貫通焉,忘情筆墨之間,和調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間,體合造物而生成之也,而后為能書之至耳。”“不可強為,亦不可強學,惟日日臨名書,無吝紙筆,工夫精熟,久乃自然。”(15)解縉:《春雨雜述》,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第499頁。這種重視學習書法傳授的傾向,形成了元代以來學習書法的風氣。從明初至弘治、正德年間的臺閣體書風正是在這種理論中產生的。
“吳門書派”最有代表性的書家文徵明論書以純正、典雅為書法的最高境界,這是繼承了元代趙孟頫的復古思想。文徵明對宋人書法尤其是蘇東坡、黃庭堅、米芾三家的書法是很推重的,認為蘇字“健勁渾融”,黃字“雄偉絕倫,真得折釵、屋漏之妙”,但總體上是以“典雅有法”為準則。他十分重視法度的精到,又在法度與個人面貌之間求得平衡。文徵明之子文嘉評其“為文醇雅典則,其謹嚴處一絲不茍”,其論書也是如此。他十分推重趙孟頫,稱其“結字用筆,無不精到”,“詞既雅麗,字復圓勁”。文徵明一生以趙孟頫為榜樣,書風中庸平和,端莊精嚴。但是,文徵明書風沒有像明初臺閣體書家書風單一,少文人趣味,而是在強調典雅的同時,注重文人寫意書風的藝術特征。他論懷素《自敘帖》,強調懷素“萬變二舉止自若”,論顏真卿《祭侄稿》稱“蕭然于繩墨之外”,這些看法,和宋人有很多相近之處。可以說文徵明論書融合了唐人重法和宋人重意兩個方面的特點。他的論書思想和審美觀念對“吳門書派”的書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祝允明也是明代中期“吳門書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書述》一文,收錄在文徵明所刻《停云館法帖》中。此文論述關于書法創作的根本原則,認為張芝、鐘繇、索靖、王羲之的書法達到中國書法的極致。后人遵循和學習,但基本上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發展到唐代,還是恪守傳統家法。進入宋代中葉以后,風貌為之一變,在“神”“骨”方面雖有晉代的風度,但很多人在書法中表現出自己的個性,不同于傳統的筆法。到南宋之后,學書者“謬誤百出”,“怪形盈世”,因而元代出現趙孟頫復興晉人的傳統。但他又認為趙孟頫的書法有“奴書”之氣,給予批評。祝允明還又《奴書訂》一文,對元明時期書家進行了品評,對宋克、張弼等同時代書家的書法作了肯定。他主張先古而后今,先“隨人腳踵”,而后能“不隨人后”,認為功力要和神韻相輔相成,統一“師古”和“師心”兩個方面,才能卓然成家,這個思想是十分有價值的。
祝允明之后的松江何良俊論書中認為,在唐代以前,集書法之大成者是王羲之,唐代以后則是趙孟頫。趙孟頫之后,集書法之大成者是文徵明。又推重顏真卿,以為“大令以下,趙集賢以上,八百年間唯可容蕭子云、顏魯公二人。”(16)何良俊:《四友齋書論》,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第142頁。
北宋時期,文人進行書法鑒識和品評時多為題跋,蘇、黃、米流傳下來的書論很多是如此,這種風氣到了南宋時有所變化。姜夔《續書譜》論書,將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建立了個人的品評體系,包括“真書”“用筆”“草書”“用筆”“用墨”“行書”“臨摹”“方圓”“向背”“位置”“疏密”“風神”“遲速”“筆勢”“情性”“血脈”“書丹”等內容,對書法藝術作了全面的討論,歷來為書家所重。到了明代王世貞,更加有全面整理古人書論的雄心。他在論述書法上建立了龐大的文獻體系,他輯錄古今書論,編成《古今法書苑》七十六卷,收錄了歷代有代表性的書法理論論著,加以分類和匯錄。在他的《藝苑卮言》一書中,其內容廣泛涉及到帖學的許多問題,書中論述到書法的特質和流變,對古今書家進行了較公允的品評。如他討論王羲之之后的唐人書法,認為:“右軍之書,后世摹仿者僅能得其圜密,已為至矣。其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緊勢游力、淳質古意不可到。故智永、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顏不得不變其真;旭、素不得不變其草。”又指出:“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遒、筋骨盡露。旭、素之后,不得不生辨光、高閑。”(17)王世貞:《藝苑卮言》,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第155—156頁。這些說法是很有見地的。王世貞論書,把“古雅”作為品評的基本標準,突出古代法帖“古雅遒美”“圓勁古雅”等特征。在他眼中,古法是一種自然天成的創作,質樸無華而又典雅平正。他推重晉人,以“古雅”作為審美取向,反對媚俗輕浮之風。更加可貴的是,《藝苑卮言》中論述了他同時期書家的作品風格、審美取向、書家題跋,對于了解明代初中期的書風發展有重要意義。王世貞之后的蘇州同鄉孫礦,在王世貞《書畫跋》的基礎上又寫成《書畫跋跋》,繼承了王世貞重“古雅”的審美觀,進一步強調天趣在書法上的作用,重性情而輕法度,提倡“無意”的創作,與古人要若即若離,反對狂邪和媚俗,這些觀念在當時都是十分可貴的。
明代中期以“吳門書派”書家為代表,多崇尚魏晉以來的傳統,形成了雅正遒媚為藝術特色的書風。從這一時期開始,也出現了一批新書風的探索者,如張弼提出了“天真爛漫是吾師”,力倡狂逸的草書,探求新的道路。陳獻章致力于心學,自創“茅龍筆”,開創了新的書風。沈周獨愛黃山谷的書法,吳寬推重蘇東坡,從魏晉傳統中脫離了出來,取法宋人,注重個性,在認識上也比元末明初有了新的變化。
明末江南地區文化發達,對書法的認識比較深入,但多在推重晉人的思想里加以發揮。松江的莫是龍論書主張“今人之不及唐人,唐人之不及魏晉,要自時代所限,風氣之沿,賢哲莫能自奮,但師匠不古,終乏梯航。”(18)莫云卿:《論書》,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第210頁。他認為,書法如不學習晉人,終將流為下品,力主以“晉人”為楷模:“鐘(繇)書點畫各異,右軍萬字不同。物情難齊,變化無方,此自神理所存,豈但盤旋筆札間區區求象貌之合者。右軍父子各臻其極,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駿,皆古今之卓絕矣。”(19)莫云卿:《評書》,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第211頁。明末嘉興的李日華以著述豐富而聞名,其《六硯齋筆記》《紫桃軒雜綴》《竹懶畫媵》《味水軒日記》等筆記中論書尤多。他也立足崇尚魏晉的傳統,記錄了明末很多文人的藝術鑒藏活動,表明這一時期在書畫鑒賞方面的內容豐富和研究不斷深入。他在論述鐘、王的同時,也對宋代蘇東坡、黃山谷、米芾以及元代趙孟頫多有肯定,論其所長,體現明人博雅賞玩的特點。
晚明時期,紹興徐渭的“古媚論”在這一時期較有代表性。徐渭詩文、書畫、戲曲無不精通。其書奔放奇崛中有妍媚,不拘固常,野趣天成。他在《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中說:“非特字也,世間諸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舍,豈真我面目哉?”他主張臨摹貴在表現個性,得古人精神。在題《趙文敏墨跡洛神賦》中重視趙孟頫的“媚趣”:“趙文敏師李北海,凈均也。媚則趙勝李,動則李勝趙。”這種重“媚”的觀念在他評倪瓚書法中也進一步強化:“倪瓚書從隸入,輒在鐘元常《薦季直表》中奪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20)徐渭:《評字》,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第128頁。在徐渭看來,“媚”和“古”是書法審美相對的范疇,“古”和“媚”的結合,是質和妍的統一。
除上述名家外,楊慎、“前后七子”、吳寬、沈周等明代各家也都有和書法相關的品評和題跋等。他們的書法品評,各有特色,各有側重,總體來看,初期重技法筆法,中期重晉唐和宋人書風,晚期則對鑒藏活動的記錄更多。總體來說,仍是以追蹤晉人書風為旨歸的。晚明時期,書論的集大成者當數董其昌了。
三、董其昌:晚明書論的集大成者
董其昌是晚明最有影響的書家,其書論集中反映在《容臺別集》的《書品》中。
董其昌的書論,也是強調“師法”和“師心”的統一,既主張臨古,又主張發揮個人性情。既主張“學書不從臨古入,必墮惡道”,又強調“離合之間,守法不變,即為書家奴耳”。他把“古”和“我”之間理解為“妙在能合,神在能離”,能將復古與創造、守法與變法辨證地統一起來。董其昌一生大量臨習古人法帖,包括二王、顏真卿、米芾、蘇東坡等,進而在臨中帶創,以古人之跡發個人之意,創造了自己的藝術面貌。
董其昌書論,還繼承宋人“以禪喻詩”的特點,在《容臺別集》卷一中,專列《禪悅》篇,又將其齋名取為“畫禪室”,體現他對禪宗的推崇。他以禪理論書,強調“頓悟”“熟后求生”和“平淡”。
在書論中,董其昌多次闡述“頓悟”在學書過程中的意義。他曾在《官奴帖》的臨本上稱“茲對真跡,豁然有會,蓋漸修頓證,非一朝夕。假令當時能致之,不經苦心懸念,未必契真。懷素有言‘豁焉心胸,頓釋凝滯’,今日之謂也。”董其昌所說的“漸修”與“頓證”,正是中國書法學習的兩種基本方法——長期的歷代法帖技法的訓練和創作中的自然創造相結合。
董其昌還強調書法中的“熟后求生”。他認為“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熟,字須熟后生,畫須熟外熟”,指出字與畫的區別,強調書法中“生”是“熟”后更高的境界。他曾自負地把自己和趙孟頫相比,認為“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熟后求生”是超越技法的精神表現和升華,也是從臨古到出新的必然。
“平淡”也是董其昌書學觀的重要內容,和“熟后求生”是一致的。“淡”的核心是平淡天真。“平淡天真”是宋人米芾的審美理想,董其昌傳承了米芾這一思想,強調“淡之玄味,必由天骨,非鉆仰之力、澄練之功所可強入”,他推重王羲之《黃庭經》“以蕭散古淡為貴”;他推重顏真卿楷書和行書,終生學習,并認為“平淡天真,顏行第一”;他臨懷素《自敘》,指出“皆以平淡天真為旨,人目之為狂乃不狂也”。可見他的審美標準中,“平淡”是一個極高的境界,“大抵傳與不傳,在淡與不淡耳”。他以晉唐法書為終生學習的目標,以為晉唐人得到這種真諦。他說:“禪家亦云,須參活句,不參死句,書家有筆法,有墨法,惟晉唐人真跡具是三昧”。董其昌一生的書法創作,正是在學習晉唐人的筆墨后形成個人靈動淡雅的書風的。
董其昌書論的形成,還與其長期的書法鑒賞與實踐活動聯系在一起,他以書法史觀來觀照書風變遷,用詩文、畫和書法進行了類比,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見解。他還以“韻”“法”“意”來總結晉、唐、宋三個歷史時期審美書風的變遷,這是前人沒有專門總結過的。他說“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為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趙子昂則矯宋之弊,雖己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河,蓋為法所轉也”。(21)董其昌:《容臺別集》卷二《書品》,明刻本。他將晉之“韻”放在首位,這種“韻”中,“不為無法,而妙處不在法”,晉人的書有高韻,要學唐人才能入晉。宋人取“意”,有得有失,得在“己意”,而失在“古意”,趙孟頫力矯宋人之弊,以“法”來求晉人之“韻”。董其昌的這種見解,使人們對二王以來書風變遷的時代特征、發展規律和書史價值有了更為明晰和深刻的認識,在中國古典書論史上,是書法史觀指導下的一次全新的古典闡釋,有著極為重要的學術意義,也是明代書論對前人的一次“集大成”的總結。
四、明代的書畫著錄與鑒賞
中國書畫鑒藏早在唐代就有記載。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對書畫鑒藏專門記錄,他認為中國書畫藝術在傳授、品第之外,還包括鑒識、收藏、賞玩以及跋尾押署、印記、裝裱、紙絹等內容。宋代米芾繼承了《歷代名畫記》所論的鑒賞方法,寫成《書史》《寶章待訪錄》等書法著錄著作。此外,宋代學者還多用題跋的形式將其鑒賞的內容寫在書畫作品之上而流傳下來,如南宋周密《云煙過眼錄》記載其鑒賞過的書畫作品,是一部重要的著錄書。這個風氣,一直延續到元代。
明代是中國書畫鑒賞最發達的時期。文人除在書畫上題跋外,還把所見的書畫作品寫成書畫目錄。明代還興起把記錄下來的書畫鑒賞內容整理成完整的體系,作為一類著作集中起來,稱為“書畫錄”或“書畫著錄”。這種著錄有將書法和繪畫綜合在一起的,也有書畫分開討論或只收書法一種的。
明代關于書畫目錄方面的著作,有文徵明之子文嘉所著的《鈐山堂書畫記》、朱之赤所著的《朱臥庵藏書畫目》;題跋方面的著作有文徵明《文待詔題跋》、王世貞《弇州山人題跋》和孫礦補充王世貞題跋的《書畫跋跋》。
明代的書畫著錄著作,比一般的書畫目錄更為詳細。最早有朱存理所著的《珊瑚木難》,收錄了唐、宋、元、明歷代書法作品,記載了這些作品的原文、款識、題跋、詩詞等。其原原本本的記錄忠實于原作,對于研究作品的形式、內容都有重要意義。
明代書畫著錄完整體系的著作要數嘉興人郁逢慶《書畫題跋》十二卷和續十二卷,它們是郁氏所見古代法書和名畫的記錄。他在著錄原文之外,還記載了款識、題跋、印記、紙張內容。汪砢玉所著《珊瑚網》也是這一形式的代表作,書中有書錄、畫錄各二十四卷,其中的“書錄”部分卷一至卷十八為“法書真跡;”十九、二十“石刻墨跡”(碑和帖);二十一為“叢帖”(集帖);二十二為“書憑”(收藏家);二十三為“書旨”(古人的書法理論);二十四為“書品”。“法書真跡”部分所收入的作品,都是古代流傳下來的原作。在諸家題跋之外,也記錄了印記、裝裱、紙張材料等。清代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匯考》一書收錄了汪砢玉這本書的內容。
明代末年,昆山人張丑所著《清河書畫舫》也是明代書畫著錄的代表作。《清河書畫舫》以人物為綱,收錄書法原作之外,還輯入各家題跋、印記等有關文獻資料。書后所附《南陽法書表》和《南陽名畫表》是當時著名書畫收藏家韓世能的收藏品。又附有《清河書畫表》,是其高祖張元素以來家族收藏品。此外還附有《法書名畫見聞表》,仿照米芾《寶章待訪錄》寫法,將自己所見聞的書畫做成一表,大致上區分為目睹和傳聞兩類。此外,張丑還著有一部《真跡日錄》,用隨筆形式記下的所見書畫鑒賞。這些著作是我們了解明末江南地區在書畫收藏和鑒賞方面的重要文獻。
結語
明代書論是中國古典書論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在總體追蹤晉宋的同時,也呈現了明代自身的獨特內涵。這一時期的書論總體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明代前期的書家除宋克等少數文人書家外,多以元代趙孟頫書法為楷模,致力于書寫精巧的書風,臺閣體書風盛行。進入中期,吳門書派興起,逐漸以唐宋書風作為取法對象,追求晉人王羲之的書法傳統。明代書論從元代的技法討論漸而轉向概括式的“體系化”的論述。
第二,這一時期產生了很多文人書畫鑒賞家和收藏家,他們重雅玩清歡,這種文化不斷發展,產生了新的藝術觀念和研究方法。其中以晚明董其昌最有代表性,一直影響到清代。董其昌書法理論受宋代米芾影響,用禪宗的妙悟對傳統書論進行了新的闡釋,是晚明書論的集大成者。
第三,明代后期以創作為主體的書論特色鮮明。晚明書法自徐渭以來,董其昌、倪元璐、張瑞圖以及明清之際的王鐸、傅山、八大等人都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他們在書法創作上,兼學晉唐和宋元,注重篆隸之法,有了新的藝術創作上的貢獻。他們的書論深入探索古代書法名家的特點,進一步追問書法藝術的本質,并在個人的創作中得到表現。明代的書法理論突破了元人,是在宋代書學理論基礎上的發展,具有了文人雅玩的新內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后期的書家,開始注重關注東晉二王之前的篆隸碑刻,并在創作中身體力行。趙宧光、傅山、八大、王鐸等名家都在篆隸書法上有所涉足,為清代碑學的興起開啟了先聲。
第四,隨著鑒藏雅玩活動在文人中流行,產生了新的著錄和研究方法,成為明代以來書論新的內容,一直影響到清代。明代中期開始的書畫目錄記錄作品名稱,到后來記錄作品的內容、尺寸、材料、題跋、裝裱等內容,著錄越來越豐富。一方面把古代法書的原始形態作了文獻記載,同時把在觀賞中形成的藝術思想、鑒賞方法也記錄下來,成為后代了解這一時期書法活動的主要文獻。這種書畫著錄的內容和方法成為明代書論的顯著特色,也是中國古代書畫鑒藏史上的重要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