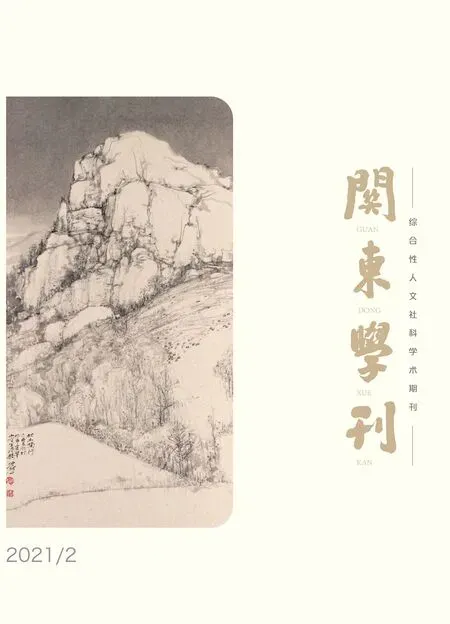從“圖像載體”到“影像見證”
——試析幻燈片作為媒介的功用沿革
原平方 梁欣彤
1922年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中說明了其棄醫從文的緣由。早年在日本學醫時,在微生物課上觀看老師播放的、用于消磨“多余光陰”的幻燈片。幻燈片呈現著關于日俄戰爭的景象,“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示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被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鑒賞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幻燈片中,國人“麻木的神情”直接而真實地展現在魯迅面前,從而對其產生刺激,激發其萌生放棄醫學轉而從文以治療國人“精神”的念頭。此后魯迅先生在另一篇文章《藤野先生》中也有對于此事的記述。“幻燈片事件”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事件,而觸發該事件的那張“幻燈片”實際上被影像與歷史賦予了“符號性”的意義。應該說,幻燈片作為一種傳播媒介,其價值與所載影像及呈現方式密切相關,同時其功能的變遷圍繞技術的發展和普及而進行,具有明顯的技術偏向性。
一、宣教:新技術初現階段的原始功能
在探討幻燈片的功用之前,我們需要對“幻燈片”進行一定的限定。狹義的“幻燈片”定義了幻燈片的物理性質,指的是一種“影片”,即正片、菲林,一般有135和120兩種規格,用來沖印或放大相片;而廣義的“幻燈片”代表了用于幻燈機放映的“照片”,也就是一種圖像媒介。本文所探討的“幻燈片”則主要基于后者的定義。
探討幻燈片的功用不得不提到放映幻燈片的裝置——幻燈機。幻燈機最初其實是傳教士的傳教工具。1654年,在德國的猶太籍人基夏爾的記錄中第一次提及了幻燈機的發明,幻燈機利用凸透鏡成像原理,將圖像放大投影于銀幕上。早期的幻燈片使用玻璃制成,依靠人工繪制。幻燈機作為傳教工具,主要的作用在于將幻燈片中所繪制的有關宗教內容的“畫”進行放大展示,便于配合傳教的宣講內容。恰如傳播學者麥克盧漢關于媒介的闡釋,“媒介即是信息”,什么樣的媒介傳遞什么樣的信息,因此幻燈片在傳教活動中承擔了“圖像”的功能。“幻燈片”即是“圖像”,“圖像”即是“宗教宣揚的信息”,這一階段的幻燈片主要發揮了宣教功能。
實際上,“幻燈片”的宣教功能也是伴隨著新的傳播技術誕生的。傳教士對于“宣教功能”的需求催生了幻燈機的發明,同時使幻燈片作為一種媒介開始出現。新傳播技術產生在早期的社會環境之下,而初現階段的新興技術也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正如“幻燈”技術因傳教需要而誕生,作為一種新傳播技術的“幻燈”技術早期亦被少數占據較高社會地位及技術能力的“傳教士”所掌握,其發揮的功能也因此主要以“傳教”為主。同理,隨著技術的誕生到普及,社會知識階層始終掌握接觸新興技術的“先機”,此后的幻燈片功能自然成為這一階層宣傳階層理念、傳揚知識內涵的“工具”。
雖然幻燈片隨傳播技術的發展幾經變遷,但是宣揚、教化功能作為“幻燈片”的初始功用仍然是幻燈片的主要功能之一,并延續至今。如在前文中援引的“幻燈片事件”中,幻燈片實際上是課堂上的教學工具,用于“顯示微生物的形狀”,使之更為清晰直接準確地傳授給學生。又如19世紀英國流行的一種演講形式,“每套幻燈片必須有附帶文字形式的講義,演講者不僅要放映幻燈片,還要朗讀并解說”(1)菅原慶乃:《聲音和文字:為“理解”電影的媒體史初探》,《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甚至在今天,傳統幻燈片作為一種圖像呈現形式,與計算機結合成為被廣泛使用的PowerPoint(PPT),在當今的教學活動中依舊發揮著重要作用。由此可見,宣教是幻燈片技術誕生的基本動力,也是幻燈片作為一種媒介最重要的職能。
二、娛樂:傳播技術普及下的衍生功能
美國傳播學者尼爾·波茲曼在關于“電視”作為媒介對于社會認知、文化結構等產生決定性作用的論述中認為,“文字信息”使人們保持思考的習慣,而“圖像”相較于“文字”更為直接,甚至“無需質疑”地向人們傳遞信息,使人們逐漸失去“思考”的過程,從而開始習慣于直接“理解”。也就是說,對“知識”的獲取需求,被“趣味的吸引”代替。“闡釋年代開始逐漸逝去,另一個時代出現的早期跡象已經顯現。這個新的時代就是娛樂業時代。”(2)[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章艷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同時,波茲曼還認為在電視媒介的影響之下,“教學已成為一種娛樂活動”,為教學所制作的“活動影像”,其教學目的已然不足以覆蓋其宣教功能。幻燈片作為影像媒介的作用雖不同于“電視媒介”,但兩者均攜帶著“圖像”的屬性功能——趣味性帶來的娛樂功用。
在魯迅先生的“幻燈片事件”中,對其產生精神刺激的幻燈片的播放緣由在于消耗“多余的光陰”,顯然該“幻燈片”所產生的效果遠遠不是“娛樂”,但出于“娛樂”的目的而呈現的事實則不可否認。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幻燈片的確具備一定的娛樂功能,“寓教于樂”即是早期幻燈片娛樂功用的集中體現。“1885年11月的上海,教育家顏永京舉辦了一場幻燈演講會。這場幻燈演講會的主題被定為:模擬環繞世界一周。該幻燈演講會中,放映了英國、德國、日本等國的風景名勝幻燈片。該演講會結束后大獲好評,后來還舉行了延長公演。”(3)菅原慶乃、鄭煬:《“理解”的娛樂——電影說明完成史考》,《當代電影》2018年第1期。這是在19世紀末上海舉辦的,與英國流行的演講形式基本類似的幻燈演講會。該幻燈演講會是一場以“理解”為初衷的娛樂盛會:各國風物近乎分毫畢現地以幻燈的形式一張張在觀眾面前展示,同時現場配以生動的解說。其從形式到內容所呈現的新穎特征足以吸引大部分受眾的注意力,同時其“聲”與“畫”的默契配合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觀眾獲取信息的趣味體驗感,從而發揮了巨大的娛樂功效。
精美的“畫片”展示佐以豐富有趣的內容演說,讓人聯想到一種曾經流行于我國的民間藝術——拉洋片。就幻燈片的此種呈現方式來看,二者異曲同工。而相較“拉洋片”這種藝術形式,幻燈片的娛樂功能更為顯著。“洋片又稱西洋景,是舊時跑江湖耍玩藝兒的一種。拉洋片需要有一個特質的木箱子,這個木箱子里裝著繪制好的圖片,人們要用凸透鏡來看。洋片的分類有很多,有自然風光,也有人物故事。過去在城市游樂場所、農村廟會,多有從事拉洋營生的人,伴隨著富有節奏的鑼鼓聲,畫上的人物景物與悠揚的唱詞相結合,別有一番滋味。”(4)李玉川:《拉洋片》,《光彩》1996年第12期。“拉洋片”的展示利用了與“幻燈片”相似的原理,雖然從物理屬性來看,“洋片”與“幻燈片”存在性質上的不同,但從呈現形式上看,“拉洋片”這種文藝形式,甚至可以擬稱為“透過木箱觀看的幻燈片”。從“圖像”媒介的角度出發,兩者本質上具有相同的功能。可“拉洋片”是一種純然出于娛樂目的的圖像呈現形式。在這種形式當中,“前所未見”的畫面是通過獵奇心理吸引受眾的手段;曲折離奇而充滿故事性的講演內容,既使受眾便于理解“畫片”,更增加了受眾觀看“洋片”的趣味性;富有節奏的“伴奏”、生動多樣的“唱腔”均是為了給受眾提供更好的觀看“洋片”的體驗感。“洋片”通過綜合性的呈現方式,調動“圖像”以引發受眾的情感反應。“從形式上看,畫片的人物、故事、環境、氣氛、色彩、動作,生動逼真。而且在音樂、演唱的配合下,觀眾的情緒始終被畫面所吸引。”(5)劉建勛:《陜甘寧邊區的藝術輕騎——新洋片》,《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1期。受眾通過觀看“洋片”在感性上獲得了巨大的愉悅,其作用更甚于理性的“信息”獲取,其娛樂功能格外顯現。
毋庸置疑,幻燈片所表現出的“娛樂”功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幻燈技術普及發展的一種典型表現。以此看來,作為一種傳播技術的“幻燈片”是從早期的被少數階層所掌握逐漸普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隨著幻燈技術的普遍傳播,其與“戲劇”“演說”及具有一定審美及趣味性的“圖像”藝術等結合使幻燈片自身也衍生出了與其承載內容相關的“娛樂”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幻燈片作為一種與“圖像”相關的媒介,其發展受到“圖像”傳播技術發展的影響,“圖像”傳播技術的升級也表現在幻燈片的功能轉變中。不難看出,“幻燈片”的功能與“拉洋片”所發生的功效有某種類似之處,而以此種形式呈現的“幻燈片”,或者說“幻燈片的播放”,已經初具早期“電影”的雛形。
三、紐帶:傳播技術升級過程中的過渡功能
關于“圖像”的媒介演變是由“靜態影像”到“活動影像”的傳播技術升級。在傳播技術的升級過程中,受眾對“圖像”的理解接受也相應發生了轉變,即從對畫報、照片此種“靜態影像”的理解到對電影這種“活動影像”的接受,“幻燈片”充當了兩者間的紐帶,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從19世紀末我國上海的“電影接受史”或可考證幻燈片發揮“過渡”作用的端倪。“在上海,電影接受不僅有游戲性的單線脈絡,游戲與文化交錯的理性空間也是電影的基盤,不過這樣交錯混雜的空間卻先于電影而出現,它在幻燈片的放映中已然誕生。在這樣兼具文化和娛樂的混雜空間里,上海電影‘重視理解’的美學方向也悄然扎根。”在同治皇帝的國喪期間,任何娛樂形式均被禁止,戲劇舞臺無戲可“演”便引進了幻燈,從此開啟了上海的幻燈放映時代。
如前文所述,上海所舉辦的幻燈演講會也佐證了初期的幻燈放映雖是以“知識獲取”為主要目的,但卻發揮了一部分早期電影的娛樂功能。“1895年,上海格致書院開始舉辦幻燈講座,第二年講座擬定六個主題,內容包括‘芝加哥世博會’‘動物學’等方面。每個演講兼有娛樂性質的幻燈片作為助興。”(6)菅原慶乃、鄭煬:《“理解”的娛樂——電影說明完成史考》,《當代電影》2018年第1期。在這些講座的“閑暇”時間里,娛樂性的幻燈片再一次成為“主角”,這說明以教育為目的的幻燈放映,與十年前同在上海、由顏永京舉辦的幻燈演講會有著相似的功用。這無疑在很大程度上為文化與娛樂融合奠定了基礎。
同一時間,用于演講會的幻燈機開始在上海各大劇院普及開來。在科學雜志《格致匯編》上出現了向劇場、大講堂出售幻燈機的商業廣告。“這些‘戲迷’群體與科學雜志的讀者多多少少會有重疊。科學雜志的讀者,也就成為了后來電影的潛在觀眾。幻燈作為‘理解’娛樂的科學展出為受眾所接受,也恰是以‘理解’為內核,其成為孕育上海電影觀賞美學的搖籃。”(7)菅原慶乃、鄭煬:《“理解”的娛樂——電影說明完成史考》,《當代電影》2018年第1期。也就是說,不同于單純的“靜態圖像”,“幻燈片”成組連續的出現,讓靜態的圖像出現了活動的趨勢,加之現場解說的配合,幻燈片所呈現的圖像雖未“活動”起來,但其連續的動態“信息”已經產生。受眾接受并開始理解這種圖像呈現方式所釋出的信息,從而開始習慣于此種狀態的圖像闡釋方式,因此,當真正的“動態影像”——電影出現后,受眾對電影的“接受”與“理解”近乎無礙。可以說,幻燈片在受眾接受由“靜態圖像”向“動態影像”發展的過程中充當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紐帶。而幻燈片的這種“紐帶”功能,也在“影像”媒介技術升級的過程中發揮了較強的過渡作用。
四、史料與藝術品:傳播技術升級后的剩余功能
隨著傳播技術的升級,比幻燈技術更為先進的“圖像”技術不斷出現,同時,幻燈技術也有一定程度的升級,幻燈片所具有的更為本質的功能作用也更為突出。幻燈片其本質為一種影像,而影像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與對事實的真實記錄。因此,傳播技術的革新在信息生產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在19世紀中葉,伴隨著賽璐璐膠卷的出現,幻燈片迎來了新的生產方式——照相移片法。用這種方法生產幻燈片,意味著幻燈片不再是單純的圖像描繪,因為人工繪制的圖像即使再精準也終究不能稱之為“真實”,但照相移片法使幻燈片開始具有真實記錄與反映客觀現實的功能,甚至可以作為一種歷史的“證明”。
關于傳統幻燈片發展最終形態的記述有這樣一段文字:“邊框由硬紙板制成,起固定作用,表面多以白色出現,一方面統一美觀,一方面便于將注釋、名稱等文字符號落于其上,更加明顯。幻燈片的主要部分以透明塑料膠片為材質,將繪畫、文字等印刷其上,更有高級品類,把照片等影像如相機膠片一般印制其上,讓觀者身臨其境。”(8)福雨:《收藏光影之色》,《北京紀事》2020年第12期。從我國幻燈片的發展軌跡來看,“其道路跨越了我國比較重要的幾個階段,全民衛生運動、學習英雄事跡、中國動畫片典型風格發展、城市標志性建筑崛起……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幻燈片成為一種大眾所接受的載體,記錄、見證、傳播著光陰的記憶。例如一部名為《看中國》的系列幻燈片,在這部系列幻燈片中,不僅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壯麗山河與風俗人情,還展現了當時的民生狀態,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國經濟民生的發展軌跡。再如一部北京幻燈片廠出品、主題為《吳作仁畫選》的系列幻燈片,文字介紹獨立成冊,與幻燈片的作品展示相輔相成,觀者既可領略畫家風采,又可詳細了解作品背后豐富的信息。幾十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再次走進幻燈片的世界,也如參閱歷史,或如曾經的青蔥歲月重新來過”。(9)福雨:《收藏光影之色》,《北京紀事》2020年第12期。照片是客觀世界的真實影像,其被印制在幻燈片上并經由幻燈機投影播放,便完成了對所記錄的“歷史真實”的客觀再現。
不可忽略的是,當幻燈片開始與“照片”產生連接,幻燈片與攝影藝術之間也就存在了必然的聯系。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影像藝術家們嘗試使用幻燈片來進行藝術創作,攝影藝術家用幻燈片的標準來審視攝影藝術與他們自身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之間的關系。在不同光影條件之下,幻燈片所呈現的“照片”與被拍攝物體本身產生了微妙差別,這激發著攝影藝術家利用幻燈片與攝影技術不斷進行試驗與嘗試,發掘幻燈片在視覺藝術領域的可能性。“我想要呈現的東西介于靜止與移動的影像之間,我想將這兩者之間的空間呈現出來,我實驗性的運用移動的影像和運動中拍攝到的影像,并探索通過全景影像(幻燈片)、語言和聲音呈現非線性的敘述結構。幻燈片是可以做到在空間中延伸的,方法是讓照相機和膠卷做同步運動。影像雖然是靜止不動的,但是卻包含了照相機、膠卷、拍攝對象隨時間先后運動的蹤跡。”(10)西格納·哈曼、周嵐:《在靜止與移動的影像之間:攝影幻燈片》,《裝飾》2007年第12期。攝影師西格納·哈曼即利用幻燈片進行了這樣的藝術嘗試。所以,當幻燈片與攝影技術發生關聯,其所承擔的功能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而這種變化本質上由傳播技術的變遷所引發。幻燈片成為“真實再現”的載體,承擔了“記憶”的作用,其作為一種“史料”的功用凸顯;同時,藝術創造對幻燈片的運用也激發出幻燈片的“圖像藝術”價值,這實際上是傳播技術升級后幻燈技術所提供的主要功用。幻燈片被升級后的“圖像”傳播技術所“取代”,其所承擔的主要功能變為傳播技術升級后的“圖像”媒介的“剩余價值”。
五、幻燈片作為傳播技術融合的當代功能
計算機的誕生讓電子科技充斥整個現代社會。20世紀80年代,企業家羅伯特·加斯金斯意識到了幻燈片商業化的價值。傳統幻燈片與現代計算機技術相結合,誕生了如今廣為人知的PowerPoint(PPT),即電子幻燈片,也稱演示文稿。電子幻燈片通過與幻燈機類似的投影儀進行投影展示,與傳統幻燈片的呈現方式幾乎無異,但其放映裝置的運轉動力全然不同,所展示的幻燈片內容也較傳統幻燈片更為豐富多元。在融媒體時代,各種媒介均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特征,電子幻燈片發展到今天也具有了一定的融合媒介特征。如今的電子幻燈片所呈現的內容除了傳統的文字、圖像以外,還包括視頻、音頻等多種媒介內容。唯一不變的是,電子幻燈片的放映過程仍然離不開解說者的演說。在大部分場景下,電子幻燈片仍呈現出一種“展示”與“解說”的功能。其實,這恰恰也是在融媒體背景下電子幻燈片體現出的最為主要也最重要的功用。
總之,幻燈片在傳播技術發展的進程中,以“圖像”作為媒介發揮了宣教、娛樂、記錄等功能。同時,在與不同技術相融合的過程中,幻燈片也保持并完善和健全了原有的功用,并且發展出諸如藝術創作等新興功能。由此可見,幻燈片的功能沿革具有典型的技術偏向性。換言之,傳播技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并決定著幻燈片功能的變遷,也使得幻燈片成為媒介發展史中一個不可忽略的有機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