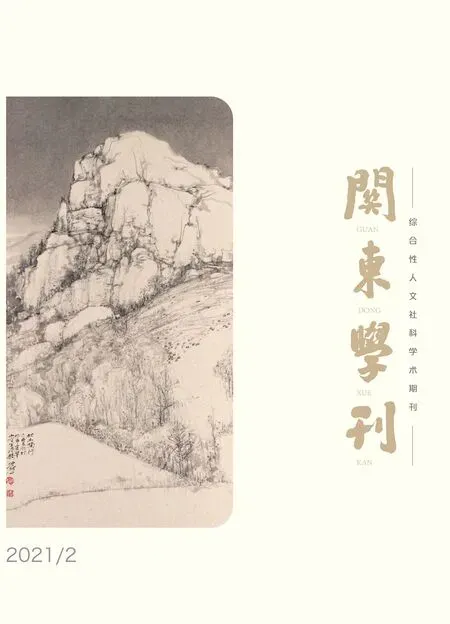簡論“新安畫派”藝術風格生成與構建
李度一
一、“新安畫派”的生成背景及影響
17世紀下半葉,正當明清易代之際,新安畫派的出現,是一種繪畫史現象、文化現象,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相關。因此我們應該在厘清新安畫派諸家技法、圖式、審美特征之前,更需進一步考證出新安畫派眾多畫家的身份、際遇、師承。如何選擇徽州新安山水中的黃山形象;如何在實際社會生活以及精神文化層面具有共性形象,這些都必須要置于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去加以考察。
唐代中國徽州著名畫家以張志和薛稷為代表,其后亦不乏畫人。在明清時期也出現了規模相當龐大的畫家群體,而這個畫家群則是以“新安畫派”為標志。
新安畫派早期畫家以程嘉燧、李永昌為代表;孫逸、汪之潤、查士標、弘仁為四大家;中堅人物以程邃、戴本孝等為代表;主要繼承者則有江注、姚宋、鄭旼、祝昌則等人,梅清、梅庚、石濤、汪采白為殿軍。石濤早年隨梅清學畫十年,常往來于揚州、南京、徽州之間,他是揚州畫派的先驅,也可以劃入新安畫派;至雪莊等變派而式微。
徽州文化是徽州本土的山越文化與歷史中原移民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一種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它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要意識形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耕文化。而這種傳統農耕文化一向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以退隱耕讀為其主要的生活方式,以“天人合一”傳統人本思想為核心意識形態造就了人們喜安靜、愛穩定、重山林野趣,同時也能在某個特定領域銳意進取的開拓精神。若從宏觀的徽州文化組成部分來看,新安畫派及徽州繪畫無疑是極其重要的一支。“新安畫派”的形成是經過長期積淀和不斷融合,首先是具有鮮明徽州特色山水的熏染;其次是諸多學說流派的不斷融合,從而形成了一種既有大的中華文化精神又富有地域特征的徽州文化;最后通過唐以降繪畫藝術的深厚積淀,直致形成繁榮的徽州畫壇與杰出的“新安畫派”。
徽州畫壇的繁榮與新安畫派的出現是多種因素相互影響促成的:1.徽州商業的繁榮、徽商的“賈而好儒”為畫家創造了有利的經濟條件;2.徽州經濟的富裕促使文化事業的繁榮,文化發達產生文人畫家;(1)黃劍:《中國山水畫通鑒·貌寫家山》,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年。3.版畫大興,為畫家提供了更多的創作機會;4.黃山、白岳等徽州本土山水對畫家的吸引與熏陶。
中國歷史上趨于成熟的山水畫創作始于唐代。明代董其昌曾借用禪宗“南北宗”的概念加以區分,并認為“南宗”高于“北宗”。在我們看來,南宗、北宗皆是文化性情及地域因素所致,南橘北枳,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應該不是簡單的高、下能夠概括的。
歷代山水畫家根據社會身份大致可劃分為士大夫畫家、畫院職業畫家、民間畫家;根據其政治態度來分為宮廷畫家與隱逸畫家;根據其創作路數分為明志抒情與追求筆墨技巧;根據其對傳統的態度分為模仿古人和勇于創新。師法自然又可分為重形式和重傳神,師古人可分為宗法一家和轉益多師等。
綜上所述,加以研究新安畫派的特點,我們認為新安畫派總體具有以下特點:以其社會身份看是隱逸的士人畫派;以其政治態度看是遺民畫派;從其創作方式看是師法自然而抒發性情;從繼承傳統看是“南宗”脈系;就藝術技巧與審美追求來說,既追求整體的形神兼備,又注重表達主觀情緒,從而形成主客觀統一的藝術追求。
新安畫派在明清之際的崛起有其鮮明的時代因素和積極的現實意義,它以隱逸的主觀情思、冷寂的創作風格顯示了天地之間、民族之中一種剛貞清峭的人間正氣;它以師法自然反撥因循守舊之風;其將自然與人品的結合彰顯出新時代畫品的“正大氣象”。因而,新安畫派審美追求的思想層面所起的歷史作用是積極而深遠的。
即便在當代,新安畫派及其作品審美精神,在今天的社會仍然有其十分積極的意義;可以提供積極的藝術文化的精神力量,對于社會的精神追求與建設有著不凡的價值。(2)郭因、林存安編:《經典回顧與現代思考·新安畫派》,《我看新安畫派》,安徽:安徽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8頁。
二、當代藝術現狀對于傳統的傳承需求與召喚
人類社會的藝術不斷推陳出新,人類的審美理想也會不斷演化。隨著經濟的繁榮,當代文化藝術也呈現流派紛呈的繁榮狀態。現當代藝術審美是在社會化、大眾化為主要表現追求的維度上體現的。藝術不同以往的社會化是由于某種需要與信息傳播方式的現代化;大眾化也是由高雅藝術到世俗生活的演變,如今的藝術職業不再局限于“小傳統”的精英階層。這種世俗化的態勢,在元代以后從文學、戲曲等藝術開始逐漸形成、發展。
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社會、文化風尚的環境變遷,中國藝術審美取向與價值論辯沿著時代脈搏發展,(3)于洋:《新世紀以來水墨藝術的都市情境與時代走向》,《藝術評論》2019年第1期。不斷趨于深入、細化和多元,特別是中國畫的內涵、價值與發展的討論一直是核心問題;這個問題表現了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呈現了藝術在新的時代中不斷開拓與多元發展。就歷史的實際看,幾乎每一個時代的斷面都是復雜而多元的,我們視野中的歷史其實是經過歷史文化的動態汰選,故而脈絡所呈現的比較簡潔清楚。
現當代藝術中有追求形式感至上的傾向,有的作品畫面模糊變形、荒誕離奇,令人難以用正常的思維面對甚至感到不可思議,似乎表現了某種特殊藝術風格的心理探索部分但又未落到追求的實處。有的當代藝術家過分強調自我價值,單純追求形式感、視覺上的純粹性,在創作中只考慮形式要素,忽略了內容在審美中的精神追求,往往有一些作品的創作形式感很強,但是整體的審美功能卻減弱,雖然形式看起來獨立,但失卻了內容的核心價值和功能,同時也造成了作品的核心概念、整體表達模糊,造成了傳達上的障礙,讓觀者受眾不知所云,從而減弱甚至失去藝術的社會功能。
提倡原創、強調個性都是藝術原則的積極部分,但是過分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創作與審美追求使現當代的有些藝術家閉門造車、夸張自我,不考慮藝術審美的社會功能與價值,經常通過怪異行為而顯示與眾不同,因此,作品個性張揚,不容易被理解,具有多變性和隨意性。這樣就會缺乏受眾,失去藝術的社會功能。我們注意到,現代派藝術與后現代藝術,有著特殊的文化背景。這就如同中國藝術也有著特殊的文化背景,其中的藝術文化傳承、延續是其審美追求與存在的基礎。與中國書法繪畫等藝術的規律一樣,每一個區域文化的藝術都有自己的傳承與延續性;從藝術發展的規律看,創新與傳承共同處于這條藝術文化延續的河流之中。
互聯網時代信息高速發展,認識多元化和審美多元化凸顯。藝術代表的是至高無上的一種精神追求,是一種靈魂上和心靈上的亨受。藝術之所以能夠成為藝術,就是因為其所處的、所引導的境界,能夠讓真正懂得欣賞的人理解其中精髓,從而進入某種精神境界。當代社會的藝術審美發生新變化,崇尚流行性、標新立異、形式化、表面化的傾向,這反映出當代社會一代人內心的浮躁和不確定性。當代藝術創作偏向于“消費型藝術”,“消費型藝術”單純為了消費而生。例如藝術作品的價值、評價與金錢價格的直接、過分聯系現象,就是消費型藝術的明確表現。消費型藝術具有的特點就是去迎合某些大眾口味,這些口味往往不能代表文化藝術的先進性與真實價值,這就使得消費型藝術在“藝術的真實功能與價值”追求方面失去方向,失去藝術的社會功用與責任承擔,在低層次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越陷越深。另外,當代藝術審美的另一個特征就是藝術走向流行性趨勢嚴重,流行性藝術就是“快餐文化”的表現,而中華文明的根基從來都不是帶有“流量性質”的快餐文化。中華文明是帶有延續性、繼承性、揚棄性,其哲學、美學、社會學的設定,有著長遠意向,與“快餐文化”有著本質的不同。
仔細分析造成當代藝術審美現狀及趨向的社會原因,大略有以下幾個方面:
1.思想普遍浮躁。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科技不斷發展和變遷,人們的思想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們從當初物質貧瘠年代的樸實到現代追求物質生活,忽略了精神追求。很多人的思想變得越來越浮躁,致使某些畫家追名逐利觀念嚴重,不重視文化、技能、精神審美的藝術性,致使“消費型藝術”普遍。“如某些畫家經常舉辦畫展,其目的就是銷售作品,使藝術作品直接產生經濟價值,致使消費型藝術遍地開花,讓藝術作品淪為大眾消費品。”改革開放使當代人被“物質主義”主導,導致藝術單純地嘩眾取寵、追求新奇。“消費型藝術”與“物質主義”的關系這里就不加論述了,至于其在社會上的種種負面現象比如“浮躁”,肯定是值得關注的。
2.受西方文化藝術影響過重,西方文化優勢被過度放大。在文化藝術領域中國藝術和西方藝術有著文化、政治、宗教、精神等方面的不同。有些人崇洋媚外思想嚴重。中國傳統文化藝術被遺忘,甚至被認為不先進不科學。誠然,當代中國藝術反傳統成為現代藝術主流,它用新奇、怪誕甚至丑陋等形式特寫不正常的社會現象,用常人不注意的角度和深度顯現社會問題,用常理不能體察的方式來展示社會和人文的內含。其消極現象與積極意義有時候是并存的。有些“實驗水墨”脫離了美與哲學的核心,剩下的只是形式的怪異甚至丑陋,這與中國歷史上藝術家的“尚怪”風格不可同日而語。中國人在文化的十字路口的思考已經很久,當代對文化藝術的思考,當代文化藝術家面對的問題,也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畫藝術現代轉型的重要課題。現當代都市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同時共存共融,信息時代對視覺文化的創新提供了時代的機緣,也為文化藝術的當代表達提供了多元路徑和選擇。開放接受文化的影響已經很久,是否一個揚棄的時代正在出現?當代的藝術家任重道遠。
3.近現代對中國畫藝術的態度。回顧百年以來中國畫發展歷程,只有民國初期的文人畫還有堅持中國文化精英性和經典性價值;其后的中國畫論壇是在一片危言聳聽的“滅絕論”中發展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有中國畫藝術窮途末路論,融合中西、改良中國畫論;然也有陳師曾、黃賓虹、傅抱石、潘天壽、陸儼少、張大千、齊白石、吳昌碩等堅定傳統的守護者。當代中國畫壇,各種藝術思潮激烈交鋒,各派藝術風格爭奇斗艷、繁雜紛復、五光十色,中國畫家們仍然在為中國畫藝術的發展進行著種種苦心孤詣的探索。
當代在全球化文化開放的環境下,在民族文化藝術全面復興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實現傳統筆墨的現代轉型,如何在保留中國畫本質性的基礎上展現新的面貌,如何認識中國畫“傳統”的內涵與外延,已然成為了諸多藝術家與理論家難以回避的課題。也可以說,時代在召喚著那些真正具有革新精神與革新實力的藝術家、理論家,對于藝術實踐、藝術理論等的揚棄仍然是當今中國畫最重要的課題。問題不在于繼承與創新,而是如何繼承、如何創新。
三、新安畫派的傳承發展與構建
當代中國畫藝術講究傳承已成定論,但如何傳承中國畫藝術卻是眾說紛紜。不過,在當下全球化發展,全面復興傳統文化的環境下,在中外文化交流比較中,對中國畫的民族性特征發展方向已有了一個清晰認識,那就是既要確立中國畫獨特的審美精神特征、充分體現中華文明精粹,又要開拓視野、兼容并蓄;無論古今中外,無論南北都可以包容借鑒,從而從中華文化振興的戰略高度審視中國畫的發展趨勢。
中國畫之所以能夠歷經千年而不衰,傳承有序的發展在其中起到關鍵性作用,正因如此才使得中國畫發展歷久而彌新。那么,如何正確認知中國畫的有序傳承呢?萬舒在《新安畫派的傳承與拓新》一文中稱:“從畫派形成發展的角度,大致可以從下面幾點著眼。一是看筆墨技藝傳承,有哪些共同特征;二是看藝術品格傳承,有哪些相通之處;三是看學養積淀傳承,有哪些相同之處;四是看如何師古人,在處理‘師古人之心’與‘師古人之跡’關系上有哪些相似之處;五是看在如何師‘造化’方面有哪些相通之處;六是看地域文化影響,一種地域文化因子是如何成為‘遺傳基因’,造成了一個地域畫派的眾多畫家的共同藝術風貌。”
綜上所述,新安畫派在對前人傳承有序和自我守正創新上無疑是成功的,而這種傳承與創新在后世的新安畫派畫家群中依然延續著,這對當下畫壇無疑有著積極的啟示意義。
(一)弘仁“獨宗倪黃”及對元四家的傳承
弘仁的繪畫風格傳承有序且脈絡清晰:他由元人上溯北宋,由倪黃而上溯董巨,弘仁的傳承是“取法乎上,借古開今”的自覺選擇,是“學人”的自律與“畫癡”“墨癡”的情懷,也是眼界開闊、洞見深邃的吸收、綜合和創新。弘仁的傳承在本質上是守正出新,他同樣由元人上溯北宋,從倪贊、黃公望直追董源、巨然,其并不拘泥于某家某派,這使得弘仁在筆墨形制上能夠突破元人,從而超出元代文人畫程式的窠臼,獨辟蹊徑,以董巨筆墨、倪黃精神、北宋格物及元人氣韻來“真寫新安山水,寫真新安山水”,這是他繪畫風格不同流俗的關鍵所在。弘仁的這種有序傳承和內部突破對后人黃賓虹、賴少其產生了深遠影響。雖然古人精神、技法、路徑多為后代師法——幾乎所有后代名家都是經過師法宋元、傳承精神而得以成功,但是就其具體的取舍看,每個人又是不一樣的。弘仁的取法,顯然目的比較清楚,所取、所得也比較清晰,其形成的風格也是獨樹一幟的,這是取法以后的感悟與實踐不同造成的。
(二)黃賓虹的“匡正時弊,借古開今”
黃賓虹繪畫的有序傳承同樣更加自覺。相較于弘仁的“取法乎上,借古開今”,黃賓虹反對明清以來師古不化的繪畫取法,同時對民國以來受西方影響的虛無主義繪畫嗤之以鼻,故而黃賓虹藝術思想中還包含著“匡正時弊”的現實意義,這對當時畫壇可謂是一劑良藥,其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黃賓虹在繪畫上視野開闊且轉益多師,是一位難得的藝術大家,他在“白賓虹”中后期不僅傳習新安諸家,而且臨習元四家中重筆濃墨一路風格,旨在改變明清以來山水畫能淡不能濃墨的畫風和畫法。他在“白黑賓虹”過渡期,繼續探索新安畫派前輩畫風,但重點已轉向對“元四家”的學習,同時關注北宋諸家。他在“黑賓虹”時期,雖然繼續學習新安諸家、元代大家,但是重點在直追宋人,傳習南宋畫旁涉北宋畫。非常自覺地“擬宋人筆墨寫新安山水”,將“師古人”與“師造化”有機結合,由此完成了“陰面山之變”,以扭轉董其昌、四王流風余韻下畫壇眼界狹窄的弊端。正如其在自畫題跋中多次強調:“北宋人畫跡如人夜行山,昏暗中層層深厚。”又云“畫欲暗不欲明”,以為浮薄者誡。他在《畫學篇》中又針砭時弊地指出:“馬遠夏圭只邊角,吳偉技參野狐禪。婁東海虞入柔靡,揚州八怪多粗疏。邪甜俗賴昭炯戒,輕薄促弱宜芟除。”(4)葉子編:《黃賓虹山水畫論稿》,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第7頁。黃賓虹終身修養學問人格,筆墨精進,精研新法,終創“五筆七墨法”,成為后人難以企及的里程碑。
(三)賴少其的“入”于傳統,“以形媚道”
賴少其和新安畫派的淵源起始于解放初期他在上海籌建中國畫院的時候。傅抱石、吳湖帆、唐云等一批知名畫家向他推薦與展示了歷代繪畫名作,其中有弘仁、程邃等新安畫派筆下神奇壯美的黃山圖;而黃賓虹筆下深厚的黃山更是震撼了賴少其。從此“安徽黃山”就像磁鐵一樣深深吸引住了來自廣東的賴少其。
自20世紀50年代始,賴少其開始在黃賓虹的指導下研習新安畫派。對弘仁、程邃、戴本孝等名家進行系統性的研究臨摹,尤對程邃更為青睞,對其“干筆渴墨”的用筆技巧尤為傾服,其所謂“恨晚生三百年,不能拜其為師”。他在安徽省文化宣傳部門任職期間,借調出各文博館的古典精品進行臨摹、學習、研究,幾乎臨遍了博物館內所有的程邃作品,由此逐步建立了他以程邃、戴本孝、黃賓虹三家為傳承有序的新安畫派體系。
賴少其的“新黃山新安畫派”體系得益于他對新安畫派的“入”與“出”。“入”是入于傳統,以“古人為師”。他說:“學習傳統不能停留在一般理解上,也不能口頭上說,而是下苦功夫臨摹”,因為“兵無武器難稱雄,不學傳統空唐突”;又說“古人之法多失傳,安可不吃乳汁不認娘。”所以他把入于傳統視為“固有的基礎”和“根本的方法”。把師古人視為一種豢養之功,一種內修,目的是建立自我的新安畫派體系。(5)羅一平主編:《大道之道·賴少其作品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5年,第7頁。
賴少其研究新安畫派傳統非常講求策略,他研究明清著眼于明清藝術家是如何“游心于意趣性情,筆墨的情趣和意趣密切相關,故而他的中國畫作品在用筆技巧上自然靈動,墨色變化上干、焦、濃、淡并用,意境上深含厚拙與沉雄并存的審美精神。
他學習宋畫,主要研究宋人是如何“以形媚道”,即宋人在繪畫中是如何做到超越自然物象的約束,做到“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劉勰《文心雕龍》),以及“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毫端”(陸機《文賦》),他在《點滴體會》手稿中寫道:“在布局方面我學習黃賓虹,遠學荊、關、董、巨,因此,在取景時常常是尋找上述畫師所經常采取的一山一水。”賴少其師古而不泥古,他采取弘仁及宋人之法畫黃山之骨和黃山之勢。所以,賴少其畫黃山多畫大幅,重在造磅礴、拙厚、蒼茫之氣,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繪畫風格,故被稱之為“賴氏黃山”。
賴少其給當代中國山水畫發展的另一個啟示是對“入”和“出”的精準把握:把“入”于新安傳統視為創作手段,把“出”于傳統視為最終目的,既要“入”的深厚,又能“出”的智慧。賴少其“出”于傳統是確立“以天地為師,以黃山為師,以黃山為友”的創作路徑,探索與實踐的目的是“傳統我用”。其若不入傳統則無法掌握諸多筆法技巧,若不出于傳統則又囿于古人枷鎖,也更無“賴氏黃山”一說了。
賴少其是中國畫壇20世紀具有全面修養的藝術家。他在詩文、版畫、書法、山水畫、篆刻等方面均有涉獵且成就非凡。他更以其錚錚鐵骨的精神品格,以“入”與“出”的傳統的文化探索,以“丙寅變法”,“師我心,寫我法”的藝術探索和生命“虛與氣合”超然于一切的生命境界,在20世紀中國美術史中書寫了自已濃墨重彩的華麗篇章。賴少其的藝術精神也在21世紀中國畫壇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四、結語
繼黃賓虹、賴少其之后,當今中國山水畫壇一批又一批山水畫家有意或無意的、有形或無形的都在與新安畫派產生聯系。在筆墨、圖式、思想內涵上產生了很多畫家、研究者、共鳴者。但是,也應該看到,在傳承新安畫派時,僅從技法和形式表現岀來的變化是遠遠不足以發展新安畫派。重要的是應該在思想感情和文化內涵上加以充實。更確切地說,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詩詞歌賦,中國文化的儒釋道融合構成了中國畫的高超藝術表現形式和審美精神。這里我們注意到,傳統精神與時代精神之間的演化與契合:中國傳統藝術精神本來在世界上就是獨樹一幟的;在歷史上的某些時代,中國藝術精神可以說是引領世界藝術潮流的。中國人的審美將人與自然的生命哲學轉化成山水畫的審美,這已經是很先進、很特別藝術思想與審美追求。如果我們在當代的民族文化復興的大背景下結合時代的精神、思想、科技與社會文化需求,必然有著更加開闊的藝術道路與境界。傳統技術、寫實寫生、大眾需求、文化高度、藝術高地、東西互動,所有這些歷史與時代的力量的集中展現,都在催生著新的復興時代的藝術風尚。在此背景下,新安畫派以其巨大的體量、醒目的高度、豐厚的積累、典型的傳承、積極的革新精神……對新時代的中國畫創作與審美追求等都有著特別積極的作用。
新安畫派的傳承和發展,以至于中國山水畫藝術的發展,乃是每一個文化人、每一個畫家的責任和擔當。作為當代山水畫家,一個當代文化藝術工作者,怎樣用手中的畫筆來表現民族文化復興背景下的壯麗山河;如何用手中畫筆來抒發時代和民族的情感和責任,毫無疑問,時代給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