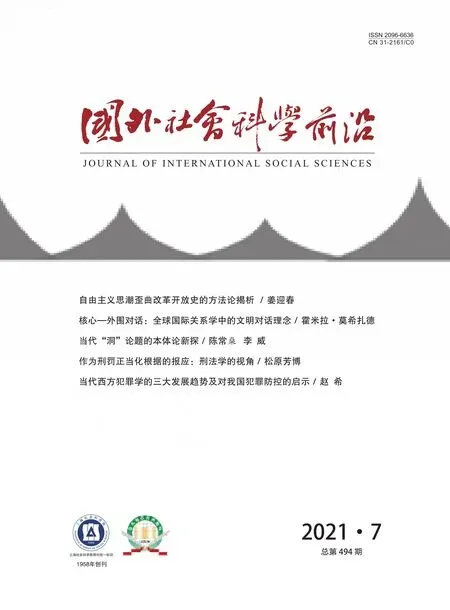自由主義思潮歪曲改革開放史的方法論揭析
姜迎春
4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不斷推進改革開放,著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著力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著力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成功開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發展取得了歷史性進步。對這樣的歷史性進步,有些人并不認同,時常拋出中國發展“糟得很”的驚人之語,其立論依據是自由主義理論,判斷中國發展好壞的唯一標準是“全盤西化”是否成為現實,即中國是否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這種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錯判歷史與現實,希冀改變我國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實際上是對改革開放歷史進程及其偉大成就的否定,其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影響大、危害深,嚴重破壞學科生態,嚴重污染育人環境。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對歷史與現實的錯誤認知源于其唯心主義方法論,即用主觀意志歪曲客觀實踐,具體表現為:歪曲歷史進程,否定改革開放的基本內涵;妄言“歷史倒退”,否定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盲目崇拜“西式民主”,否定改革開放的政治基礎。
一、歪曲歷史進程,否定改革開放的基本內涵
我國實行的改革開放,起始于1978年,至今已經40多年,其基本內涵是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對外實行開放政策以吸取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緊緊抓住“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這個改革開放的根本,極大煥發了社會主義的生機與活力,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日益彰顯。而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認為,改革開放就是推動中國加入西方主導的“現代世界體系”,放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放棄黨的領導。這就根本改變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基本內涵,這樣的“改革開放”無異于“顏色革命”。
為了否定我國改革開放的基本內涵,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的一大“創造”是通過扭曲歷史,將不同的歷史事件和歷史進程都說成是“改革開放”,并稱這個過程就是“加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過程。經過這樣的歷史改造,“改革開放”被完全抽象化,“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系就被割裂了。通過這樣的改造,“改革開放”成了加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歷史過程。有人提出:通常所謂“改革開放”,表征一種文明更張與政治轉型的歷史運動,構成了現代中國的主流政治意志與歷史意識,迎應的正是這一現代世界體系。中國之加入現代世界體系,起自“改革開放”,就發生在此現代世界展開之際,而成為現代秩序建構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這個尚未終結的歷史進程的重要環節。持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論者認為,晚近一個半世紀里,中國已然有過三波“改革開放”,它們延綿接續,回應這個現代世界與世界體系進程。第一波大約起自1860年,終于1895年,整整35年。其以洋務運動為旗幟,昭示著一個“古今中西”的時代降臨華夏,中國由此開始了自己的現代化歷程。第二波起自1902年清末變法,至1937年“抗戰”爆發止,又一個35年。在此時段,清末王朝、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制,三個階段,政體雖殊,理路則一,接續前行,而統貫為一大整體。舉凡民族國家建構、市場經濟、社會改良、立憲代議體制、現代程序主義法制,以及教育、新聞傳播和思想市場建設,均有所嘗試,均有所建樹。1978年底至今的40多年,主要截至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實為第三波“改革開放”,其進程是以向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流政治意志和世界普世文明的致意與皈依,匯入世界歷史潮流,重新開始中國文明的復興與中國制度主體的建構歷程。
上述這個“三波改革開放論”為“改革開放”鋪陳了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在這里,“改革開放”已有近160年的歷史。前兩波“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事件是洋務運動和戊戌維新運動,1978年以來的所謂“第三波改革開放”成了“向世界普世文明的致意與皈依”,并稱這種“致意與皈依”是“現代中國的主流政治意志與歷史意識”。“三波改革開放論”貌似具有歷史依據,然而,主觀主義化的“歷史碎片”不能成為任何理論的立論基礎。
第一,將不同性質的歷史事件和歷史進程同質化,其實質是用主觀意志扭曲客觀實踐。“三波改革開放論”只看到并不存在的“現代中國的主流政治意志與歷史意識”,并將這種虛構的“政治意志與歷史意識”夸大、冒充為永恒真理,以為只要不停晃動這面“永恒真理”大旗,就站到了評判歷史的制高點。這種唯心主義歷史目的論的方法就是用觀念史代替客觀的歷史進程,歷史成了觀念的工具和玩偶。馬克思對蒲魯東的一種“怪論”的批判完全適用于“三波改革開放論”:“蒲魯東先生無法探索出歷史的實在進程,他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套怪論,一套妄圖充當辯證怪論的怪論。他覺得沒有必要談到17、18和19世紀,因為他的歷史是在想象的云霧中發生并高高超越于時間和空間的。一句話,這是黑格爾式的廢物,這不是歷史,不是世俗的歷史——人類的歷史,而是神圣的歷史——觀念的歷史。在他看來,人不過是觀念或永恒理性為了自身的發展而使用的工具。”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3頁。
第二,“三波改革開放論”否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及其偉大成就,根本否定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三波改革開放論”將改革開放抽象為“向世界普世文明的致意與皈依”的歷史進程,通過“重寫”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人民性、實踐性和時代性,將改革開放界定為向資本主義文明的“復歸”。這樣,“改革開放”就成了一個資本主義化的歷史進程。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歷史實踐過程,“三波改革開放論”企圖用主觀意志否定這個過程及其必然性,說明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始終停留在純粹思維的范圍之中,而這種思維仿佛順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頑強的事實”。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7頁。看起來,唯心主義思維的消化能力似乎很強大,因為這種思維可以不顧事實,企圖用想象消化一切客觀歷史進程。
第三,雖然“三波改革開放論”主觀主義、唯心主義的方法論特征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它的目的并不局限和滿足于思維領域。“三波改革開放論”中的歷史唯心主義服務于其改變歷史的“善良意志”,但是這種“善良意志”在中國不可能結出善果,歷史和現實都不可能為這樣的“善良意志”提供實踐支撐。有人提出,“放眼百年中國轉型歷史,可以看出,相較于1911年和1949年的兩次易幟,它并非屬于‘另起爐灶重開張’的開天辟地的創舉,毋寧,如主事者所言,旨在‘撥亂反正’,通過告別革命的去政治化與奉行‘發展是硬道理’的世俗化努力,接續清末以還開啟、兩度中斷的與世界主流文明‘接軌’的進程,繼續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實現百年未竟的華夏復興夢想,徹底解決‘中國問題’。”從這里可以看出,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的“善良意志”就是中國必須與所謂“世界主流文明”即資本主義文明接軌,一切歷史進程都服務于這個“善良意志”。蘇共垮臺、蘇聯解體同自由主義“善良意志”的不斷發酵密切相關,這樣的歷史教訓太沉重、太深刻了。在自由主義政治視野中,蘇共垮臺、蘇聯解體“好得很”,是中國的“好榜樣”,中國應當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家”。這樣的“善良意志”當休矣,因為自掘墳墓式的改革只會使中國四分五裂,只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發展中斷,只會使中華民族喪失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機遇。
二、妄言“歷史倒退”,否定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基于偏執的主觀意志和主觀標準,即以是否與所謂“世界主流文明”即資本主義文明接軌作為判斷改革開放是前進還是倒退的唯一標準。有人根據這一標準得出了危言聳聽的結論:就當下而言,“改革永遠在路上”的官方宣諭與希望依循行動圖和時間表而“將改革進行到底”的大眾呼吁,兩套改革話語的出現及其對立,亦為其后果。在此,起源于地中海文明的現代世界的現代秩序浪打潮頭,逼迫出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任何拒絕這一世界體系的努力均為癡人說夢。可基于既得利益、固守基本盤的徒勞掙扎,亦且如影隨形。故而,時至今日,晚近這一波改革之道義動機不存,利益動機亦失,所以才裹足不前,甚至出現了為此不惜返身回頭之跡象,而形跡可疑。前述這個結論之所以錯誤,是因為它無視社會實踐本身,只憑主觀意志和主觀標準來評判歷史,它脫離社會實踐,也脫離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實際。
我國40多年改革開放是前進了還是倒退了,判斷的標準不是主觀意志和主觀標準,而是社會實踐本身。40多年改革開放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我國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社會主義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更加突出。這些歷史性成就是客觀的,也是我們評判改革開放的客觀標準。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罔顧這些客觀標準,用主觀意愿代替客觀實際,必然得出荒腔走板的結論。比如,有人用抽象人性論評判改革開放,用所謂“普遍人性”裁剪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就成了可以任意搓揉的面團:晚近所謂“改革開放”,順天應人,己立立人,就在于經由一個去政治化的進程,向普遍人性低頭致意,包括向追求自由這一人性讓步。同時,所謂普遍人性,不僅意味著“食色性也”,也在于,或者,更在于抉發與涵養理性,以人類理性打理公共生活,將安寧和平生計的希望寄托于理性的良知良能。畢竟,溫飽有余,乃求斯文,而斯文在茲,端賴于茲。凡此歸總,意在造就一種秉賦理性的自由個體,恰與中國歷史政治的現代進程及其內在理路,若合符契。在這里,脫離了具體社會實踐的“理性”“人性”“自由”被打造成了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萬金油”,作者想怎么抹就怎么抹。在這樣的胡亂涂抹之下,我國40多年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和歷史進步性被徹底歪曲和置換了。將自由主義理論中的“理性”“人性”“自由”胡亂運用于歷史評價,恰恰是非理性的典型表現。當然,自由主義論者從來都不承認自己有非理性的表現,他們總是自認為是“人類理性”的代言人。因為有了這樣的自我認知,非理性的自我評價就自然流露出來了:一個受過學術訓練的法學家階層出現于學術共同體和社會生活共同體,發揮著意想不到的啟蒙作用,其于養育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同時,成為法律理性的堅定守護者;實際上,法學家階層的出現,在印證了刻下漢語文明人文知識分子的整體性衰朽的同時,表明隨同移植型法制而來的法意熏陶下的法學家集團的自由主義價值立場,早已成為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
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極力美化所謂“世界主流文明”即資本主義文明,其方法論錯誤是明顯的。第一,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不能指出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性,特別是不能指出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趨勢和歷史局限性,而是將資本主義文明永恒化、終極化。第二,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不能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病癥與資本主義文明內在地聯系起來,將資本主義文明抽象化、神圣化。第三,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把資本主義經濟、政治、道德等“因素”“詩意般地混雜”在一起,對經濟、政治、道德等“因素”相互關系的理解必然陷入混亂,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認知就必然陷入碎片化、表面化。所以說,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對資本主義文明的理解是錯誤的,將其美化為“當代世界主流文明”顯然是荒謬的。我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實踐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表現出優越于資本主義文明的制度優勢和巨大的發展潛力。妄言我們“必須與資本主義文明接軌”,這有悖于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
鄧小平曾經指出,對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和文化不能盲目地無計劃無選擇地引進,更不能不對資本主義的腐蝕性影響進行堅決的抵制和斗爭,“現在有些同志對于西方各種哲學的、經濟學的、社會政治的和文學藝術的思潮,不分析、不鑒別、不批判,而是一窩蜂地盲目推崇。”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頁。鄧小平指出的這一現象一直存在,錯誤社會思潮的產生、發展和泛濫與此直接相關。比如有人提出:發展經濟必須對外開放,重獲世界主流的接納,亦即獲得占統治地位的西方發達國家的認可,因而,向洋人昭示法制,回應制度挑戰,實在是做生意的基礎,也是由經濟而政制,由法制而政治的連環套路。現在,所謂“世界主流”即西方發達國家并不認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它們將中國的發展視為對自己的威脅。對這一現象的理解,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的解釋是,我們沒有向所謂“世界主流”主動示好,沒有將自己主動轉化為“世界主流”的文明樣式。這就是自由主義者的天真幻想,似乎世界歷史發展都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都在他們的掌控之中。但是,幻想終究是幻想,它不可能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精神向導,改革開放依靠的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和人民群眾的歷史創造偉力。
三、盲目崇拜“西式民主”,否定改革開放的政治基礎
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提出,改革開放就是“向英美所主導的大西洋文明時代的世界體系低頭致意”,也就是向“世界普世文明的致意與皈依”。那么,完成這種“致意”和“皈依”的標志是什么呢?就是中國放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實行“西式民主”,即所謂“憲政民主”。這是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的核心理念和最終目標,目的是否定和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的政治基礎,藉此在中國完成“顏色革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的人把改革開放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體制的方向改,否則就不叫改革開放。這是曲解我們的改革開放。不能籠統地說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后。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我們不能邯鄲學步。世界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1《習近平關于總體國家安全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9頁。
在自由主義理論中,民主只有一種,只有資本主義民主才是民主,社會主義民主不叫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根本沒有民主。有人根據這一民主理論提出,當代中國“現在所缺的,是民主和法治”;“當下中國,轉型歷史正在爬坡,需要的是助力‘推一把’;民主政治正在敲門,缺的是‘臨門一腳’。對于富于理想并且深諳政治本質的政治家來說,可謂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時代呼喚著自己的政治與政治家,要求他們經由政治決斷,將中國從訓政引領向憲政,最終完成中國文明的政治秩序的現代性轉型,徹底走出歷史三峽,實現中華民族的政治成熟。”在這里,自由主義民主論者,完全無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中國的成功實踐,完全無視資本主義民主的根本缺陷,完全無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當代世界的先進性。
自由主義民主論者只相信一點,就是中國必須移植“西式民主”即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因為這樣的民主制度是萬能的,是最先進的,是人類終極民主制度,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必將在中國“落地”:自從晚近中西交通以來,東西沖突頻密,自由主義及其所表征的政體展現出無與倫比的正當性,因而,如何讓它在中國生根,遂成一個躲不掉的大問題。換言之,自由主義及其一套政制設置對于中國文明來說是不是可欲的?如果是可欲的話,那么,如何落地生根成長,漸成中國文明中的有機組織部分?特別是其政治制度如何逐漸于中華大地肉身化,并且融會為中國人日常生活實踐中之灑掃應對、言談舉止?凡此種種,早已構成一個百年問題,大家一直在追問,也一直尚未能夠獲得圓滿解決。這里有兩大誤判,一是所謂“自由主義及其所表征的政體展現出無與倫比的正當性”。同封建主義相比,自由主義確有它的正當性,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它的正當性逐步被它的矛盾性、欺騙性、腐朽性所窒息。自由主義如果永遠都有“無與倫比的正當性”,就不會有社會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盡管社會主義在實踐進程中出現過種種曲折,但是,它的先進性和優越性是自由主義所沒有的。二是所謂自由主義“在中國生根”是“躲不掉的”。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成功實踐已經證明,“自由主義及其所表征的政體”在中國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只會越走越寬廣。中國人民沒有任何理由要走回頭路,沒有任何理由要選擇已經被實踐證明是落后的“自由主義及其所表征的政體”。
四、結 語
要科學評價40多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首先,必須緊扣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不能從主觀愿望出發,更不能從脫離中國實際的錯誤的愿望出發,不能用頭腦中固有的形形色色的虛假理念衡量客觀的歷史進程。其次,要科學認識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這個進程是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奮斗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實踐史,而不是西方“憲政民主”理念的實現史。唯此,才能正確把握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內在聯系。有的人根本無視歷史進程本身,將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概括成為西方“憲政民主”理念的實現史。因為這個理念還沒有變成現實,所以“改革開放”就沒有實質性進步,“立憲與建國,是清末以還幾代中國人的中心議題。包括適之先生在內,幾代先賢積勞積慧,須臾不離乎此,而顛沛流離在此。若說百年之內頭等大事,唯此為大。迄而至今,情形大變,而基本格局尤在,‘中國問題’尚未根本解決,轉型進程猶在途中。”所以,“今天再論適之先生,需要重溫適之先生,他對于‘中國問題’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建國’的思索,作為一百多年來中國思想文化中一筆重要的精神遺產,需要我們于重溫中汲取力量,為當下的努力注入思想的活水源頭。”在這里,自由主義論者深陷虛假理念的泥潭無法自拔,我們只看到“自夸的論調,集市般的喧嚷,大吹大擂的口氣”1[德]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75頁。,而中國人民的光輝奮斗史、改革開放的生動實踐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巨大進步史都在他們的視野之外。
總體來看,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是一個用學術話語包裝起來的空話體系,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論者就是列寧曾經批判過的“主觀哲學家”,制造理論上的污泥濁水是他們的“天職”,“我們的主觀哲學家——試圖由空話轉到具體事實,就立刻滾到泥坑里去了。他在這個不很干凈的地方,大概感到很舒服:安然坐著,收拾打扮,弄得污泥濁水四濺。”2《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5頁。為防止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的“空話”泛濫成災,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和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滌蕩“主觀哲學家”們制造的污泥濁水完全是必要的。否則,我們的理論生態就會惡化。縱觀人類歷史,在特定社會條件下,謬誤的迷霧也會遮蔽真理的光輝,捍衛真理從來都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旗幟鮮明堅持真理、立場堅定批駁謬誤”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