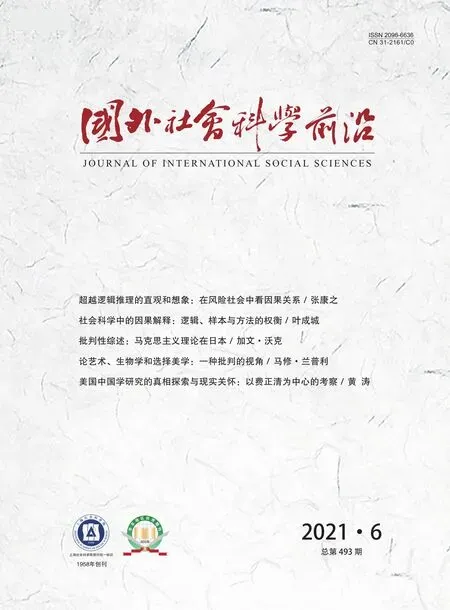自然審美的想象力問題辨析
孫 偉 李慶偉
羅納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的形而上學想象力是一種重要的自然審美模式,艾倫·卡爾松(Allen Carlson)認為該模式是一種仍然有待于進一步發展的具有潛力的自然審美模式。卡爾松將赫伯恩的想象力模式作為一種對于認知模式的擴展:“對于環境欣賞而言,我們可能列舉出一種多元的或更為相對的詮釋。然而,更為主觀化的詮釋的希望可能來源于我們文化傳承的另一層面,它與科學知識相同,似乎更有普遍性。在赫伯恩所謂的‘形而上學想象’的審美關聯性進行辯護之中,他暗示出這種可能性。”1[加]艾倫·卡爾松:《自然景觀》,陳李波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第11頁。在赫伯恩之后,艾米麗·布拉迪(Emily Brady)和瑪莎·伊頓(Marcia Muelder Eaton)等人對于想象力模式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布拉迪對于赫伯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進行了進一步的發展,在其基礎上總結出自然審美之中想象力發揮作用的四種形式。2Emily Brady, Imagination and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56, no 2, 1998, pp.139-147.伊頓提出了對于想象力模式的重要批評,她認為想象力總是難以和虛構分開,在一種虛構的想象力之中,感性會淹沒理性,并且會忽略自然審美的一種整體性的要求。伊頓認為,如果要讓想象力在自然審美之中發揮自身的作用,它就必須建立在自然環境科學知識的基礎之上。3Marcia Muelder Eaton, Fact and Fiction in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s Criticism, 56:2, 1998.國內學者聶春華指出了赫伯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試圖在嚴肅的審美和瑣碎的審美之間取得平衡,并認為赫伯恩的美學思想具有一種融合當代環境美學不同立場的特質,并為未來的環境美學提供了指引。4聶春華:《羅納德·赫伯恩與環境美學的興起和發展》,《哲學動態》2015年第2期。陳國雄認為赫伯恩提出了環境審美模式研究中的主要問題——主觀的審美對象和客觀的科學知識如何結合,并且通過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思路。5陳國雄、杭林:《羅納德·赫伯恩環境美學思想研究》,《鄭州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這些國內外學者對于赫伯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的研究都強調了該模式對于環境美學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但較少涉及對于該模式內在矛盾的分析。鑒于想象力模式仍然是一種有待進一步推進的環境審美模式,在前人基礎之上進一步推進對于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的研究是有必要的。由于環境美學交叉學科的特性,在當代現象學對于想象力的最新研究基礎之上,審視赫伯恩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的內在矛盾并提出解決方案將會是有意義的嘗試。美國現象學家約翰·薩利斯(John Sallis)對于想象力現象學進入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建立了一種以想象力和自然為主題的現象學理論。在薩利斯的現象學研究基礎上,討論形而上學想象力和現象學想象力的區分,以及兩種想象力理論對于自然的不同理解將有助于一種更為完善的審美想象力模式的出現。
一、形而上學想象力
羅納德·赫伯恩是當代自然美學的開創者,他的著名論文《被忽略的自然美》是當代自然美學的奠基性文獻。同時,他也是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的提出者,他這樣定義形而上學想象力:“我認為它是一種解釋性的要素,可以幫助我們去闡釋自身關于自然情境的整體經驗。它是一種與經驗整體相關,而不是僅僅與當下經驗相關的帶有形而上學特征的看作……或解釋為……”1Ronald W. Hepburn, Landscape and the Metaphysical Imagination, Environmental Values, vol.5, no 3, 1996, pp. 191-206.赫伯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不是某種當下的直接感知,而是對于直接感知經驗的二次加工,帶有某種反思的特性。赫伯恩的想象力現象學模式建立在知覺和想象的二元對立的哲學基礎上,在強調知覺和想象的區分的同時,認為想象力作為對于知覺經驗的加工有助于提升我們的自然審美經驗,而且這種加工同時帶有著某種形而上學的特征。赫伯恩強調想象力的形而上學特征并非是要返回形而上學傳統,他的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服務于其對抗科學主義的審美模式的目的。赫伯恩指出科學主義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對世界的豐富性的簡化,而在這種簡化的過程之中,很多對于人類來說值得保留的東西都不復存在了,他強調:“最為關鍵的是,關于自然的審美經驗,是增強我們去辨別出那個相比于科學的客觀世界更為重要的生命世界的方法。”2Ronald W. Hepburn, Landscape and the Metaphysical Imagination, Environmental Values, vol.5, no 3, 1996, pp. 191-206.需要注意的是,赫伯恩強調審美世界和科學實在世界的區分并非是沿襲了形而上學傳統之中的兩個世界的劃分,他僅僅是想要強調某些形而上學的特質在發揮想象力之時的作用。對于赫伯恩來說,想象力無法對于本體論問題給出回答,審美經驗也并不需要對于世界終究是什么這一問題給出回答。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在對于風景的審美鑒賞之中存在著兩個極端。其中一個極端是主體傾向于將當前的審美感知理解為是一瞬間的,另外一個極端是審美主體將預設的形而上學的想象力范疇應用到審美活動之中,以一個更為宏大的時空整體的標準來理解當前的審美世界。”3Ronald W. Hepburn, Landscape and the Metaphysical Imagination, Environmental Values, vol. 5, no 3,1996, pp. 191-206.在兩種極端之中,赫伯恩認為一種合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介于這兩個極端之間,也就是說欣賞者既不能僅僅滿足于當下的自然審美經驗,也不能對于當下的自然審美經驗做出過分的形而上學的理解。赫伯恩認為當下的知覺經驗由于并不包含著一種反思性的思想成分,因而并不能夠引領我們通向自然本身的真理。另外,赫伯恩認為對于知覺經驗所作出的解釋和反思也會存在不合適的狀況,這主要體現在基督教傳統之中。由于基督教對于兩個世界的劃分,自然作為此岸世界相對于精神性的彼岸世界來說是不完滿的,是不能夠為自身提供意義的。
赫伯恩認為一種合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必須擺脫以上兩種極端的影響,他強調合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必須是非宗教的,同時又不能是完全以自然科學的模式為導向。因此,赫伯恩將目光投向了藝術,他認為在一些杰出的藝術作品之中,形而上學想象力得到了最為完美的實現。“夜空,盡管我們可能知道它是無垠的、黑暗的,就像一個鑲嵌了無數寶石的穹頂把我們安放于其庇護之下;但是,那閃耀的距離是無限的,我們感受到它的無限,在其純潔之光中欣喜。”4John Roskin,1843-60 Modern Painters, Library Edition, 轉引自Ronald W. Hepburn, Landscape and the Metaphysical Imagination, Environmental Values, vol.5, no 3, 1996, pp. 191-206.赫伯恩認為約翰·羅斯金(John Roskin)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合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的典范,在羅斯金的描述之中,無限作為一個形而上學的概念對于我們的自然審美經驗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赫伯恩十分重視羅斯金關于感受的論述,他認為我們在夜空的審美經驗中“并不是去認識無限而是去感受無限”。1Ronald W. Hepburn, Landscape and the Metaphysical Imagination, Environmental Values, vol.5, no 3, 1996, pp.191-206.然而,由于赫伯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是一種對于知覺經驗進行解釋的想象力,根據這種模式的想象力我們并無法真正做到“感受無限”,我們關于無限的夜空的審美經驗僅僅是我們根據“無限”這一形而上學的概念對我們關于夜空的知覺經驗所作出的解釋,其中不可避免地已經包含了認知的成分,這在很大程度上違反了他自己提出的去“去感受而不是去認識”要求。2Ronald W. Hepburn, Landscape and the Metaphysical Imagination, Environmental Values, vol.5, no 3, 1996, pp.191-206.
二、形而上學想象力的矛盾
赫伯恩提出了自然審美之中包含著瑣碎和嚴肅兩個極端,其中瑣碎的自然審美是一種對真正的自然的歪曲,沉迷于私人的趣味使得我們背離了自然審美的對象。“一種膚淺的自然美學是就其混淆、忽視或者是壓抑了關于對象的真理而言的,它在關于什么是自然的錯誤理解的道路上去感受和思考自然。”3Ronald W. Hepburn, Trivial and Serious i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 in Salim Kemal and Ivan Gaskell (eds.),Landscape, Natural Beauty, and the Art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5.在赫伯恩看來,嚴肅的自然審美是一種直接通達對象之真理的模式,而瑣碎的自然審美則背離了這一目標。一種合適的自然審美模式需要建立在對于自然的本體論探究的基礎之上,我們要欣賞自然之美,首先要保證我們所欣賞的是自然而不是別的什么東西。因為,我們可以推斷出赫伯恩的這種“如自然般的”原則和他所要求的整體化(oneness)的立場是一致的。“一種最為突出的審美典型就是我們自身的生命和我們面前的景色的知覺相似性,植物的枝葉伸展就好像我們的血脈伸展那樣,平靜的海浪沖刷岸邊的節奏就好像我們自己的平靜的呼吸的節奏。在這里,與自然的一體就是對于這種人和自然和諧與共鳴進行審美的享受,而不是對它們進行理論的認知。”4Ronald W. Hepburn, Landscape and the Metaphysical Imagination, Environmental Values, vol.5, no 3, 1996, pp.191-206.赫伯恩認為人與自然的一體不能夠通過科學的認知而實現,而需要通過一種審美的欣賞活動來實現。但是,問題在于赫伯恩所論述的人與自然的一體很難分清到底是一種類比上的一體還是一種事實上的一體。
人與自然的一體建立在一種人和自然的連續性的形而上學基礎之上。連續性的形而上學反對西方傳統的分離性形而上學,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并非是一種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對象關系,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的連續,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個連續的部分。阿諾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認為:“連續性觀點的出現為環境是什么和意味著什么做出了最好的解釋。然而連續性并不是只為環境所限制,它是實現更一般的形而上學理解的關鍵。”1[美]阿諾德·柏林特:《生活在景觀中》,陳盼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第5頁。柏林特的介入美學就是以連續性的形而上學作為自身的基礎,赫伯恩的整體性立場顯然也建立在這種連續性形而上學的基礎之上。赫伯恩的矛盾之處在于,在提出了“如自然般的”自然鑒賞原則和人與自然作為一個整體的立場的同時,他又認為形而上學的想象力想要提升自然審美的嚴肅性的話,就必須包含一定程度的反思,這種反思破壞了他自己所提出的原則和立場。赫伯恩關于想象力之中的兩種成分的劃分體現了這種矛盾。思想成分(thought component)和感知成分(sensuous component)是赫伯恩對于形而上學想象力之中的兩種要素的區分。2Ronald W. Hepburn, Trivial and Serious i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 in Salim Kemal and Ivan Gaskell (eds.),Landscape, Natural Beauty, and the Art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赫伯恩認為自然審美存在二元結構,感知成分是一種感知的直接性,思想成分代表了一種對于感知直接性的反思。
我們可以通過這個例子來理解赫伯恩對想象力之中兩種成分的劃分:“我面對著一處初夏的風景。我看見到處都是新生的樹葉的嫩綠,白色和粉色的野花,那里有鳥叫有蟲鳴,有溫暖的太陽和潔白的云。我唯一的思想成分就是:享受這些,此時此刻!一個朋友站在我的旁邊,沉思于同樣的一片風景,對于他的知覺經驗用不同的思想成分進行了修正:多么美麗!但是這些僅僅是死寂的冬天與蕭瑟的秋天之間的插曲。”3Ronald W. Hepburn, Landscape and the Metaphysical Imagination, Environmental Values, vol.5, no 3, 1996, pp.191-206.在這里,感知成分也就是當前之所見,而思想成分則是對于當前之所見的一種反思。赫伯恩舉這個例子想說明兩種不同的思想成分的區分,以區別出一種合適的思想成分和不合適的思想成分。合適的思想成分與審美經驗具有內在的聯系,而不合適的思想成分與審美經驗之間的聯系是外在的。我們需要注意的不是赫伯恩對思想成分合適與否的區分,而是他所論述的自然審美之中的思想成分是否是必要的。思想成分意味著對于直接的感性經驗的反思,這代表人暫時從所欣賞的風景之中抽離。也就是說,赫伯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要求一種審美者和審美對象的分離、審美知覺和現審美想象力之間的分離。這種分離的傾向造成了赫伯恩的美學思想內部蘊含著一種內在的矛盾,這表現為他既要求審美者融入當前的自然環境之中,從而獲得一種和自然一體的審美經驗;又要求審美者暫時從審美情境中抽離出來,對于自己的審美經驗進行反思。
傳統美學用藝術美的標準來衡量自然美,這延續了美學再現論的傳統,這種傳統強調藝術是對于真實事物的再現。赫伯恩對于形而上學想象力中兩種成分的劃分帶有一種對自然進行再現的特征。這是由于他把自然當做可以被人的意識加以圖像化把握的對象。這主要是因為他對于想象力的理解沒有脫離意識哲學的范疇,因為在意識哲學那里,想象力是一種局限于圖像性的意識活動。赫伯恩把自然經驗理解為一種圖像性的意識活動,而他所論述的思想成分只是對我們圖像化的自然經驗進行的反思性再加工。當赫伯恩堅持“如自然般”自然審美原則之時,他遵循的就是一種美學的再現論傳統,他把自然審美經驗理解為一種對于自然的模仿論式的再現。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建立在傳統想象力理論關于知覺和想象力對立的基礎上,這種想象力哲學把想象力理解為作為主體的人的意識活動,是對于某種知覺內容的二次加工。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像一臺精密的電腦那樣存儲下我們審美經驗之中的感知要素,并且依據某種形而上學的算法來對這種被存儲的感知要素進行加工和處理。
在這種知覺和想象力對立的哲學基礎之上,自然已經不是作為一種原初呈現的自然,而是一種經過人的意識活動加工的自然經驗。赫伯恩試圖建立一種合適的、和自然審美經驗有著內在聯系的想象力模式,但是,這種追求注定是無法實現的,因為在他的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之中已經內在包含著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也就是說初始性的對于自然的知覺經驗和我們第二次的對于這種初始性知覺經驗的加工的對立,是無法真正實現一種人和自然統一的自然審美經驗的。在這種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之中,人和世界的對立無法消除,也就是總是人和自己打招呼,而不是世界和人打招呼。
當赫伯恩試圖依靠形而上學想象力來提升自然審美的嚴肅性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他所遵循的是一種表現主義的傳統。表現主義傳統重視人的內在情感,把自然現象理解為人的內在情感的外部象征。赫伯恩的表現主義美學特征和美國哲學家喬治·桑塔耶納(George Santayana)的美學思想具有一種內在的聯系,桑塔耶納這樣論述表現的特質:“在一切表現中,我們可以區別出兩項:第一項是實際呈現出的事物,一個字,一個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現力的東西;第二項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遠的思想、感情,或被喚起的形象、被表現的東西。這兩項一起存在于心靈中,它們的結合構成了表現。”1[美]桑塔耶納:《美感》,楊向榮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71頁。我們可以看出,赫伯恩認為的想象力的感知成分基本上對應于桑塔耶納的實際呈現出的事物;而想象力的思想成分則對應于桑塔耶納所說的暗示的事物。這種表現主義的美學傳統雖然盡力地彌補審美中主觀和客觀之間的分裂,但是它們無法最終實現統一,按照曾樊仁的說法,這種傳統美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實體論的美學,而現象學則顛覆了這種實體論美學。2曾樊仁:《生態美學基本問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
陳國雄指出赫伯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與浪漫主義傳統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系:“浪漫主義者對自然的欣賞很少單獨關注自然的感性形式,經由豐富的想象,這種對感性形式的關注更多地與主體的情感及對世界的冥思密切地聯系在一起,這就必然會造成自然成為人類情感與理念的象征。”3陳國雄:《環境美學的理論建構與實踐價值研究》,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66頁。浪漫主義自然觀念有助于擺脫科學主義立場對于自然的簡化,但是帶來的問題就是將人的情感和價值強加到自然之上,自然以人類的文化形式和情感形式來展現自身,這違背了如自然本身來欣賞的要求。赫伯恩意識到了這種問題,因此,他強調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需要在直接性感性經驗和過度的形而上學解讀兩個極端之間做出謹慎的選擇。在上述關于自然審美的例子之中,顯然,第一種思想成分被赫伯恩認為是合適的形而上學想象,而第二種思想成分則被認為是一種過度的形而上學想象。赫伯恩謹慎地選擇一種合適思想成分,以避免形而上學想象力陷入一種浪漫主義式的過度情感。
赫伯恩和浪漫主義者眼中的自然都仍然是一種物質的惰性的自然,而不是一種可以表達自身意義的自然。無論是再現論的傳統還是表現論的傳統都忽視了自然本身的真理,因此,雖然赫伯恩的美學提出了“如自然般的”審美標準,但是他建立于再現論和表現論基礎上的美學思想并沒有辦法完成這一任務。最終,赫伯恩面對的困難就在于他必須回答自然審美之中的情感性因素是否是一種審美主體將自身的情感朝向自然的投射。
赫伯恩的美學思想本身的矛盾和張力是由于其思考的復雜性和涉及的問題的艱難所導致的,這種矛盾和張力也是赫伯恩美學思想的迷人之處。赫伯恩既想避免自然審美被納入自然科學的軌道,又想避免人文主義視閾之中的自然的人化。赫伯恩調和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立場必然帶來一種多元模式的自然審美,這也為未來的環境美學指明了方向。但是,他所建立的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并不足以完成建立一種新的美學的任務,因為,這一模式缺乏對于自然的本體論的探究,并且建立在一種陳舊的知覺和想象力的二元對立基礎之上。赫伯恩形而上學想象力的矛盾就在于其“如自然般”的標準和與自然一體的標準要求一種一元化的審美模式,而他的形而上學想象力卻是一種二元化審美模式。二元化的審美模式并沒有擺脫西方形而上學之中的主體與客體的對立,雖然它要求人與自然的一體,但是這種人與自然的一體僅僅是一種外在的類比,并不是一種具有內在聯系的一體。
三、現象學想象力
赫伯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是一種具有潛力的自然審美模式,但是需要對于它的內在的矛盾進行克服。其內在矛盾的根源在于他并沒有超出傳統美學的范疇,因此,在傳統美學之中所包含的主客觀分裂是他無法克服的。雖然赫伯恩意識到了主客觀分裂在美學中造成的問題,也試圖通過形而上學想象力來調和這種矛盾,但是這種調和是無法成功的。因為,赫伯恩在主客觀分裂的前提下進行的調和無論怎樣努力都是一種外部的結合,而不是真正的內部的統一。實現主觀與客觀的真正統一需要對于主客觀分裂之前的原初狀態進行追問,約翰·薩利斯的想象力現象學契合了這種對于原初狀態進行追問的要求。
(一)去主體化的想象力
赫伯恩的想象力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當代的意識哲學或者心靈哲學對于想象力進行的簡約是貧乏化的代表。從薩利斯現象學的角度來看,赫伯恩對于形而上學想象力進行嚴格概念界定的做法具有一定風險,那就是有可能通過這種定義而扼殺了想象力自身的神秘性,從而使想象力失去讓人感到驚奇的力量。“人們不能冒險對想象力進行簡單的理解,因為這種沒有任何風險的、不受任何質疑的關于想象力的概念很可能會讓想象力僅僅屈從于人們對它的理解,而不是從想象力自身出發的顯現。”1John Sallis, Force of Imagination: The Sense of Elemental,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p.13.薩利斯認為對于想象力進行概念化是一種缺乏想象力的表現,因為任何的概念都來自于想象力自身的運作,沒有哪一種概念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關于想象力的問題。
薩利斯的想象力現象學試圖擺脫那種傳統哲學把想象力視為主體的某種能力的模式,他眼中的想象力不是一種建立在知覺基礎之上的意識活動,這種現象學想象力包含了欣賞者和欣賞對象之間某種處于共振狀態的融合模式。“一種解構性的運動需要我們去懸置那種占有關系中主體和想象力的關系。作為一種能力,想象力總是被認為是從屬于作為主體的人,或者在前現代的哲學之中的靈魂。”2John Sallis, Force of Imagination: The Sense of the Elemental,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p.146.現象學想象力具有一種解構性的力量,想象力的運動瓦解了一切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結構,比如主體和客體、心靈和物質。這種解構性的想象力也就不再是作為主體的人的某種能力,并不是被人所擁有的作為意識活動的能力。
赫伯恩的想象力起到的是一種關聯的作用:“將我們所知覺到的自然對象的形式和自然的本質形式聯系起來,把我們知覺到的自然和我們自身的立場和設定聯系起來,最終使我們感覺到自己通過沉思活動和自然處于和諧一體之狀態中。”3Ronald W. Hepbur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 3, issue 3, 1963, pp.195-209.這種想象力的關聯作用在赫伯恩看來是一種人和自然之間的內在性的聯系,但是,這種內在性的聯系是建立在主客體分裂的基礎之上的外在結合,而薩利斯通過現象學想象力試圖揭示的是一種主客體尚未分化的原初狀態。薩利斯的現象學想象力改變了傳統想象力哲學之中的知覺和想象力之間的對立狀態,這種包含了知覺經驗的想象力提供了一種直接通向自然的途徑,在現象學想象力之中所呈現的自然是一種在主客二分之前的原初的自然經驗。這種原初的自然經驗隱含在人類文化的層層包裹下面,雖然它經常以文化或藝術的形式出現,但是并不等同于文化或藝術本身。葉秀山這樣描述這個主客體不分的世界:“基本的經驗世界本就是一個充滿了詩意的世界,一個活的世界,但這個世界卻總是被‘掩蓋’著的,而且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它的覆蓋層也就越來越厚,人們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把這個基本的、生活的世界體會并揭示出來。”4葉秀山:《美的哲學》,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頁,轉引自彭鋒:《完美的自然》,北京大學出版社,第51頁。對于薩利斯而言,藝術天才最為重要的作用就是為我們通向這種原初的自然經驗提供了渠道。根據傳統的想象力理論,藝術天才的最為重要的特征就是他們具有異于常人的豐富想象力,這種豐富的想象力表現為他們天才的藝術創造活動。但是,對于薩利斯來說,藝術天才與其說是具有著豐富的創造力,倒不如說他們是擁有敏銳的發現和觀察的能力,也就是說,藝術天才的作品是自然言說自身的通道。
(二)元素的自然
薩利斯的想象力現象學要求我們首先要去懸置關于自然的兩種理解方式。第一種是科學主義的立場,在這種立場之上我們把自然看做是物的集合。第二種是人文主義的立場,在這種立場之上,我們認為自然離不開人類文化和情感的建構,其代表就是浪漫主義傳統。經過懸置之后,我們只剩下關于自然的基本感知,這種關于自然的基本感知被薩利斯稱為元素(elemental)。因此,對于薩利斯而言,自然也就是作為元素的自然,它在想象力之中呈現自身。在薩利斯的想象力現象學那里,我們不是通過類比的方式和自然融為一體而是本身就和自然一體,這種一體不能作一種單純的在自然之中的理解;而是說經過懸置的自然,本身就是一種原初性的關系。
元素的自然代表了一種在主客體分化之前的原初關系。“在元素的自然領域之中,既沒有物也沒有屬性,因此與物的屬性相關的邏輯在這里統統不起作用。”1John Sallis, Logic of Imagination: The Expanse of Elemental,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2, p.159.元素不是這個物質世界的組成部分,在薩利斯那里,自然以元素的方式向我們顯現,我們不能把這種自然的顯現理解為自然是由元素組成的,而是說,自然以諸多不同元素的共存方式顯現于想象力之中。想象力最為重要的作用就是通過自身的神秘力量,將各種不同的元素聚集在一起,從而打開一個自然得以向我們顯現的空間。這個空間不是一種我們日常理解的物理性的空間,而是一種由想象力的力量所創造出來的場域。在這個場域之中,事物自身的顯現得以可能,這個空間也就是一種呈現性的空間。“只有通過想象力的盤旋,空間才能出現在那里。”2John Sallis, Logic of Imagination: The Expanse of Elemental,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2, p.162.想象力所敞開的空間是一種讓各個不同的元素在保持互相之間的矛盾狀態的同時聚集在一起。“在想象力的邏輯之中,矛盾是可以被維持的,因此,想象力的邏輯是一種超限的(exorbitant)邏輯。”3John Sallis, Logic of Imagination: The Expanse of Elemental,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2, p.161.一般的邏輯以避免或者消除矛盾作為任務,但是想象力的邏輯卻可以使矛盾雙方保持在自己的限度之中,那是因為傳統的邏輯是一種抽象的邏輯,而想象力的邏輯是一種具象化的邏輯。正是想象力的作用使得我們可以將天空和大地這一對矛盾保持在自身的限度之中,又以一種整體性的方式顯現。在薩利斯那里,天空和大地作為兩個重要的元素,它們所敞開的空間正是由于想象力的作用。“天似穹廬, 籠蓋四野”,在詩歌之中,正是想象力的作用釋放了那元素的自然力量,想象力的力量本身就是元素的自然的力量,因此,好的藝術并不是人的創造物,而是元素的自然自身的表達。
想象力的力量起到一種召喚和聚集的作用,它把不同的元素聚集到一處向感知開放,真正能夠感受這種想象力力量的人是天才的藝術家。在天才的藝術家的作品之中,想象力的力量得到了最大的釋放,而這也是元素的自然(elemental nature)自身的顯現。想象力之中所呈現的自然是元素的自然,想象力現象學所追求的自然經驗是一種主體和客體尚未分化之時的渾然一體的經驗,這完全不同于赫伯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所追求的統一的、具有內在聯系自然經驗。赫伯恩的主客體統一的自然審美經驗是一種主客體分化之后的重新統一,也就是說,這種統一是建立在分化基礎上的統一,是一種外在性的統一。真正天人合一的主客不分的自然審美經驗只能是一種現象學式的想象力,只有在現象學的想象力之中,自然或者環境才能夠被經驗為一個非對象化的與欣賞者完全統一的整體。
對于薩利斯而言,想象力現象學所致力于實現的是一種人和自然的原初關系,在這種原初關系之中,人和自然的二元對立是不存在的。元素的自然代表了這種原初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在薩利斯那里,自然的本體也就是一種關系。這種關系并不是一種外在性的一個物體和另外一個物體的關系,而是一種現象性的關系。這種現象性的關系隱藏在我們的日常經驗下面,只有在特定的時候它才能顯現出來。想象力開始盤旋之時,也就是這種現象性的關系顯示自身的時候。薩利斯這樣描述想象力的盤旋:“那么,這里只有盤旋自身而沒有盤旋者,沒有任何事物隱藏在之下。它不像是我們所說的閃光(flashing lighting),盡管我們的語法要求我們去說是光在閃,但是事實上,那里并沒有光隱藏在閃的后面,閃沒有任何的作用者(agent);光就是閃自身。因此,這種情況也對于想象力的盤旋(hovering)也是一樣的。在事物自身顯露的意義上那里只有盤旋能夠向人類顯現。”1John Sallis, The Return of Nature: On the Beyond of Sens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6, p.101.現象學想象力的盤旋不僅僅是在我們欣賞自然之時才能夠被激發,在我們欣賞天才的藝術作品的時候,想象力的盤旋也同樣的可以被激發,因為,天才的藝術品本身就具有璞和真的特色。要激發現象學的想象力,我們必須擺脫赫伯恩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之中的思想成分,我們不能對我們的審美經驗加以反思性的審視,這種反思性的審視會破壞我們的作為一個整體的審美經驗。想象力的盤旋需要我們拋卻自身的反思性注意力,需要實現一種忘我的狀態。“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南北朝吳均的著名詩句道出自然本身所具有的讓人忘我的狀態,因此,真正的投入自然的懷抱,實現赫伯恩所要求的人與自然的整體性, 需要的不是一種反思性的思想成分,而是一種非反思的,直接性的投入。
四、結 語
赫伯恩形而上學想象力的內在矛盾表現在他想要堅持一種人和自然作為一個整體的立場,但是又想避免這種整體立場所帶來的一些負面因素。人與自然的整體立場容易導致的負面因素是它容易導致一種“什么都行”的審美模式,這種任意性抹殺了自然和環境美學作為某種理論的嚴肅性。赫伯恩認為提升自然審美的嚴肅性并不只能依靠科學認知的方法來實現,他試圖用形而上學想象力來提升自然審美的嚴肅性。然而,形而上學想象力之中感知成分和思想成分的二元對立又違背了整體性的要求。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的內在矛盾同時表現在它的哲學基礎是二元對立的形而上學,在其中,知覺和想象力處于對立的二元狀態,但是赫伯恩的整體性美學立場又要強求一種一元的審美知覺。在傳統形而上學的基礎上,赫伯恩對于一種理想的自然審美理論的追求是難以實現的,因為,在傳統想象力哲學之中所隱含的人與世界的對立,意識和世界的對立是無法克服的。赫伯恩的形而上學想象力模式需要一種新的哲學基礎,而薩利斯的想象力現象學完美地契合了這種需求,在這種被重新理解的想象力基礎上,人和世界的對立得以克服,想象力不再是一種主體的意識活動,而是一種真正的人與自然的融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