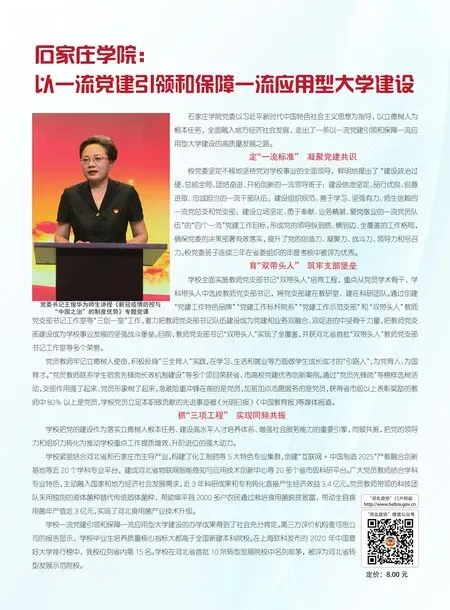文史集粹
【 勤儉節約是黨的優良傳統 】
不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建設時期,毛澤東都是勤儉節約的典范。毛澤東始終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員,從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終身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習慣。他的飲食可謂簡單隨意,一日兩餐或三餐,粗茶淡飯,不吃山珍海味。吃飯時不小心掉到桌面上的飯粒,他都一粒粒夾起,送到口中,從不浪費。他常說:“我們國家還不富裕,人民群眾生活還有一些困難,我吃那么好,心里不安呀。我吃的飯菜很好了,什么時候中國的老百姓都能吃上四菜一湯,那該多好。”他的衣服鞋帽,許多都是補了又補,一件睡衣打了73 個補丁,一條毛巾被也打了54 個補丁。
厲行勤儉節約,周恩來總理也是榜樣。他的飲食同樣清淡,從不浪費一粒米、一片菜葉。每次吃完飯,總會夾起一片菜葉把碗底一抹,把飯湯吃干凈,最后把菜葉吃掉。吃飯時,偶爾掉在桌上一顆飯粒,也要馬上撿起來吃掉。有人對他如此節儉感到不解,總理說:“這比人民群眾吃得好多了!”
(摘自《浙江老年報》)
【 蘇章斷案 】
漢順帝某年,蘇章被任命為冀州刺史。他在審理積案的時候,發現大貪污犯清河太守,正是他以前最要好的朋友。
一天晚上,蘇章備下酒菜,請來那位老朋友。二人一邊喝酒,一邊暢敘舊情,十分快樂。這位清河太守的心里,原來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摸不透蘇章對自己的罪行采取什么態度,這下好像石頭落了地。他長吁一口氣,得意地說:“人家頭上只有一頂青天,唯獨我頭上有兩頂青天啊!”蘇章正色道:“今晚我請你喝酒是聊盡私人舊誼;明天冀州刺史開堂審案,卻是執行公理王法。”
第二天,蘇章正式開堂,對這個清河太守判刑定罪。此之謂:“先盡私情,再了公事。”
(摘自《燕趙老年報》李宏/文)
【 曹植說疫 】
217 年冬,一場嚴峻的疫情在東漢的疆域里大肆蔓延開來。到底有多嚴峻?曹植在《說疫氣》一文中這樣記載:“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正好印證了《說文解字》的定義:“疫,民皆疾也。”
著名的文學團體“建安七子”,竟有五人死于這場大疫。當時,謠言四起,有人就說,這是鬼神所為。于是,民眾信以為真,在門上懸掛符箓,以期鎮宅抗疫。曹植覺得這種行為非常“可笑”,并指出:“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此說雖然不盡“科學”,但樸素唯物的傾向已夠難能可貴了。
(摘自《今晚報》趙趕秋/文)
【 誰創造完善了評劇花臉老生唱腔 】
1953 年,以賀龍為總團長的中國人民慰問團赴朝鮮慰問志愿軍,當時中國評劇院小白玉霜、魏榮元在朝慰問演出《秦香蓮》,魏榮元飾演的包拯(花臉行)的唱腔,基本上套用京劇。賀龍看戲后對魏榮元說:為何不像評劇唱腔?遂給他個任務:創造完善評劇花腔唱腔。
魏榮元(1923-1976),唐山市豐潤區紫草塢村人,評劇凈行名家。從1953 年從朝鮮回國后,他借鑒京劇花臉唱腔特點,結合評劇音樂旋律和音色特點,創造完善了評劇花臉聲腔藝術,并在調式上進行了大的調動,創造了〔新流水板〕。1954 年他與小白玉霜再合演《秦香蓮》時,唱到“與駙馬打坐開封堂上,聽我把從前事細說端詳”這段花臉唱腔時,巧妙創新于評劇,〔二六〕板又吸收了京劇和河北梆子的音律,從而發展了評劇〔二六〕板式,且充分保持了評劇〔二六〕板式穩健大方的特長。“開封堂上”一句加強鼻音和腦后音,強調亮音,行腔剛毅,突出包拯正義嚴明、剛直不阿的性格。“細說端詳”一句,是從京列〔西皮原板〕和河北梆子旋律演化而來,“端詳”二字顯示出氣勢磅礴,莊重威嚴。同時,魏榮元對評劇老生唱腔也多有創新,如他在現代戲中飾演老生行當創造的〔新流水板〕,即是吸收京劇〔流水板〕并揉進其他劇種旋律的獨創之作。
(摘自王德彰著《談戲說史》)
【 [啄木鳥]“柴火”不寫“柴禾” 】
讀報刊,常見將“柴火”寫為“柴禾”的情況。如說“以前農村家家燒柴禾做飯”“小時候我常去地里拾柴禾”。“柴禾”是錯用,應是“柴火”。
“柴火”是名詞,指的是做燃料用的樹枝、秫秸、稻稈、雜草等。“柴火”中的“火”字不讀第三聲,而讀輕聲。而“禾”指莊稼的幼苗,如“鋤禾日當午”。禾苗不宜當柴燒,“柴禾”不組詞。一些作者之所以寫作“柴禾”而不寫“柴火”,可能是對“火”字的含義了解不全。“火”字有多個義項,除常用的指物體燃燒的光焰以及槍炮彈藥、發怒、緊急、興旺等外,還當“焚燒”講,《禮記·王制》有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從這個含義來講,寫為“柴火”才合詞意。
(史 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