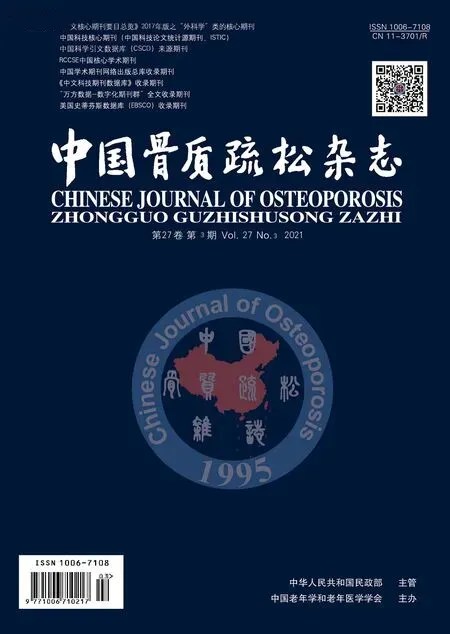血清胃饑餓素水平與絕經后骨質疏松癥合并代謝綜合征患者骨密度相關性研究
鄭坤杰 劉晴晴 耿建林 張雪坤
衡水市人民醫院內分泌科,河北 衡水 053000
代謝綜合征是一種高胰島素血癥,脂質異常,高血壓和腹部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風險增加的疾病[1]。近年來代謝綜合征患病率持續上升,尤其是中年女性,其患病率高達27.8 %[2]。骨質疏松癥由于骨量減少和微觀結構改變而導致骨強度降低,這增加了骨折的風險并增加死亡的風險,對老年人群健康有著重大的影響[3]。代謝綜合征和骨質疏松癥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具有相似性,隨著年齡的增加,疾病惡化,心血管疾病和骨折等疾病的后果嚴重,而且骨細胞和脂肪細胞均為間充質干細胞分化而來[4]。骨密度(BMD)受基因和環境因素的影響,50 %~80 %來源于遺傳因素,30 %~50 %來源于環境因素,同時肥胖和代謝綜合征也是遺傳和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復雜疾病[5]。胃饑餓素(ghrelin)雖然不屬于脂肪因子,但由于它是內源性瘦素拮抗劑,具有促食欲的特性,因此引起了學者的極大興趣。有證據表明它具有多效性,包括食欲增加、胃腸動力增強、葡萄糖代謝調節和抗炎作用[6-7]。除了它在肥胖和胰島素抵抗中的作用,胃饑餓素在骨代謝中的作用也被提出。盡管已經廣泛探索了BMD和體重及脂肪因子的相關性,但是胃饑餓素和絕經后代謝綜合征患者BMD的研究有限。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血清胃饑餓素與絕經后骨質疏松癥合并代謝綜合征患者骨密度相關性。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設計和一般臨床資料
納入我院初診未經治療的絕經后骨質疏松癥患者(T評分<-2.5,按照2017年中華醫學會骨質疏松癥診斷標準)參加研究。排除標準:服用抗骨質疏松的藥物、出現心血管并發癥、慢性腎病和視網膜疾病、中風、心肌梗死等疾病的患者。所有參與者在隔夜禁食后采集血液樣本,隨后進行離心獲得血清樣本,并在-20 ℃下儲存備用。血清胃饑餓素通過RIA(Ghrelin Human RIA Kit RK-031-30,Phoenix PharmPharmticals Inc.,Belmont CA)進行評估,最低檢出限為0.1~0.6 ng/mL,批內變異系數為5 %。檢測受試者的體重和身高,計算BMI。同時檢測腰圍(在直立狀態下,肋骨的下端和骨盆的髂嵴之間保持水平區域的周長),血液樣本放入檸檬酸鈉抗凝管中。通過自動生化分析儀(Olympus,Tokyo Japan)測量所有患者空腹血漿葡萄糖、總膽固醇和三酰甘油的水平。使用羅氏商業試劑盒通過電化學發光免疫法(Cobas e601自動免疫分析儀,羅氏,德國)檢測骨轉換標志物Ⅰ型膠原氨基端延長肽(Procollagen type Ⅰ aminoterminal propeptide,P1NP)和β-I型膠原羧基端肽(cross-linked C-terminal telopeptide of type Ⅰ collagen,β-CTX)。使用QDR 4500型號的Hologic DXA雙能X線檢測儀測量腰椎(1-4)和左股骨頸骨密度。
代謝綜合征診斷標準:①超重和(或)肥胖BMI≥25 kg/m2;②空腹血糖FPG ≥6.1 mmol/L(110 mg/dL)和(或)2 h PG≥7.8 mmol/L(140 mg/dL),和(或)已確診糖尿病并治療者;③收縮壓/舒張壓≥140/90 mmHg,和(或)已確診高血壓并治療者;④空腹血三酰甘油≥1.7 mmol/L(150 mg/dL),和(或)空腹血HDL-C<1.0 mmol/L(39 mg/dL)。具備以上4項組成成分中的3項或全部者可確診為代謝綜合征。
1.2 統計學處理
數據統計分析采用SPSS 21.0軟件。連續變量表示為均數±標準差,定性變量結果使用百分比表示。采用單樣本Kolmogorov-Smirnov檢驗確定連續變量的分布。采用t檢驗比較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對兩組以上連續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比較;使用卡方檢驗對分類變量進行檢驗。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分析胃饑餓素水平與骨密度之間的相關性。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本研究共納入320位絕經后骨質疏松癥女性受試者,其中絕經后骨質疏松癥合并代謝綜合征78位,絕經后骨質疏松癥女性不合并代謝綜合征242位;如表1所示,絕經后骨質疏松癥組(OP)和絕經后骨質疏松癥合并代謝綜合征組(OPMS)的身高、體重、BMI、血糖、腰椎(L1-L4)和股骨頸骨密度、Ⅰ型膠原氨基端延長肽和β-I型膠原羧基端肽和胃饑餓素水平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均<0.05)。骨代謝指標P1NP (骨形成指標)和β-CTX (骨吸收指標)水平顯示,OPMS組骨轉換較OP組顯著增加(P<0.05);OP明顯大于OPMS組患者年齡(P<0.05);在兩組受試者中,OPMS組胃饑餓素水平明顯低于OP組 (P<0.05)。此外,OPMS受試者體重和身高均高于OP受試者。在不同的亞組中,OP組女性中其血糖水平更低(P<0.05)。然而,OPMS組和OP組之間觀察到總膽固醇和三酰甘油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 (P<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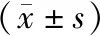
表1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進一步探索胃饑餓素與絕經后骨質疏松癥患者代謝參數的相關性,在矯正年齡和BMI后,使用Spearman相關分析后發現血清胃饑餓素水平與骨密度呈負相關;和骨形成指標P1NP和骨吸收指標β-CTX水平呈正相關,但與三酰甘油、血糖和總膽固醇未發現相關性(見表2)。

表2 絕經后骨質疏松癥合并代謝綜合征患者胃饑餓素與代謝參數的相關性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ghrelin and metabolic parameters in patients with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complicated with metabolic syndrome
3 討論
肥胖和骨質疏松癥是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在發達國家發病率不斷上升。肥胖最初被認為對骨骼有保護作用,因為許多研究證實了體重和所有部位骨骼的骨密度(BMD)之間呈正相關[8]。然而,體重與骨折風險之間的關聯更為復雜[9]。為了解釋體重與BMD的相關性,已經提出了幾種理論,肥胖者骨骼的機械負荷增加,胰島素抵抗導致的胰島素水平增加,脂肪組織中雌激素芳構化程度增加,性激素結合球蛋白(SHBG)水平降低[8]。由于脂肪因子的發現,脂肪組織不再被認為只是一個脂肪庫,而是一個復雜的內分泌器官,參與調節許多代謝過程。胃饑餓素是一種類脂肪因子,具有增加食欲、增強胃腸動力、調節葡萄糖代謝和抗炎作用[6-7]。關于胃饑餓素在骨代謝中的作用,大多數實驗數據支持對成骨細胞增殖和分化的刺激作用[10],但尚不清楚胃饑餓素對絕經后婦女代謝綜合征患者骨密度的影響。本研究發現骨質疏松癥患者胃饑餓素更高,進一步研究表明胃饑餓素和絕經后婦女代謝綜合征患者骨密度呈現負相關性。
身體脂肪和BMD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并且已經報道了研究表明涉及體脂肪與BMD增加或減少的矛盾結果。絕經后婦女代謝綜合征出現BMD減少的原因被認為是由體重增加介導的。這伴隨著絕經后婦女由于雌激素缺乏導致的腹部肥胖和體重增加,并且隨著施加于骨骼的物理負荷上升,骨形成的速度緩慢增加,抵消了由代謝綜合征引起的BMD的減少[11]。在本研究中,獲得了類似的結果,在絕經后代謝綜合征患者不同骨密度組的體重有明顯不同。然而,前瞻性研究[12]表明骨量隨著體脂肪量的增加而減少。在國內的一項大型研究[13]中,體脂肪量與骨量呈負相關。在絕經后婦女中,BMD與瘦體重和脂肪量之間的關系與BMD呈正相關,脂肪量影響更為顯著[14]。
在本研究中,血清胃饑餓素水平和骨形成指標P1NP及骨吸收指標β-CTX水平呈正相關。在其他研究[15-16]中,已經報道了代謝綜合征,腹部肥胖,胰島素抵抗,炎癥反應和BMD之間呈負相關。炎癥反應介導的代謝綜合征和BMD之間密切相關,促進細胞因子產生的脂肪細胞和骨重塑的細胞共同起源于骨髓間充質干細胞的分化,并且在脂肪細胞的方向上繼續進行,破骨細胞激活骨轉換并且導致BMD降低[15],而代謝綜合征導致的輕度炎癥會增加骨吸收并導致骨質流失的進展。有研究表明代謝綜合征患者血清高靈敏度C-反應蛋白的水平上升和BMD下降之間的顯著相關性[17]。在BMD和慢性炎性疾病(2型糖尿病)的關系的研究中發現高血糖會降低骨形成和抑制成骨細胞;同時通過刺激破骨細胞活性來增強骨吸收,導致BMD降低,骨折風險增加[18]。
當然本研究有其局限性,第一,橫斷面研究,僅限于胃饑餓素和絕經后代謝綜合征出現骨質疏松癥之間的研究;第二是不能確定之間的因果關系,絕經后女性患者難以代表整個點;第三,由于骨質疏松癥影響因素較多,如女性激素的分泌、鈣和甲狀旁腺素,維生素D等指標對BMD的直接影響,最終影響研究結果。
總的來說,本研究表明胃饑餓素水平升高是絕經后婦女合并代謝綜合征出現骨質疏松癥的獨立危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