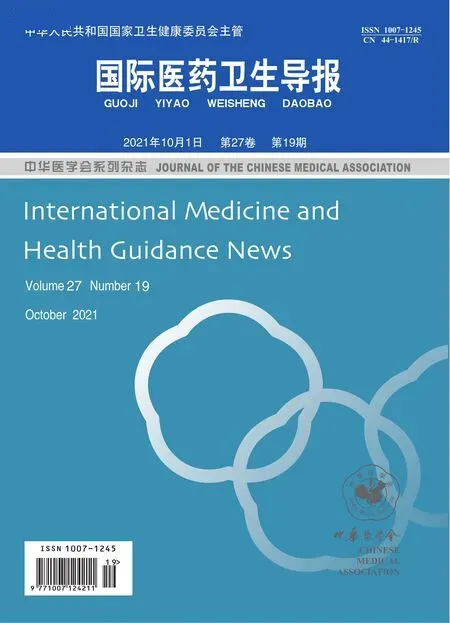γδT細胞與自身免疫性疾病關系的研究進展
武文燕 宋守君 薛海波
1濱州醫學院附屬醫院內分泌科,山東 256603;2濱州醫學院煙臺附屬醫院全科醫學科,山東 264010
γδT 淋巴細胞是通過無限制性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直接識別入侵生物表面的抗原發揮其毒性T 細胞功能的一類T 細胞亞群[1]。γδT 細胞分布于機體的黏膜、淋巴組織、上皮接觸組織(皮膚和胃腸道)以及脾臟的紅髓中,約占整個T 細胞的30%,γδT細胞只占人類循環T細胞池的小部分。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機體對自身抗原產生免疫反應,進而導致體內多系統損害的疾病。其包括: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疾病(autoimmune thyroid disease,AITD)、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胰島素依賴性糖尿病、類風濕關節炎、系統性硬化病等。近年來隨著社會工業化發展,大量研究顯示全球自身免疫性疾病發病率逐年升高,且病情復雜,治愈率低,加重了患者和社會的經濟負擔。目前臨床治療方案較為單一且不良反應較大,嚴重影響患者預后及生活質量。闡釋γδT 細胞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不僅對疾病發病機制有更深理解,也為γδT 細胞靶向治療的發展提供理論支持。本文就γδT 細胞與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關系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γδT細胞的發現及研究進展
1.1 γδT 細胞的分類 γδT 細胞是不依賴于外周啟動和分化,在個體發育早期有明顯的成熟發育途徑,是第1 個顯示功能反應性的T 細胞群體[2]。γδT 細胞可以在胸腺中發育性編輯以產生獨特分子的離散效應子集[3]。γδT 細胞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是特定Vγ/Vδ 配對的結果,優先地,Vδ1 鏈與不同的Vγ1 家族(Vγ2/3/4/5/8)配對,分布于皮膚、脾臟、肝臟等;而Vδ2 通常與Vγ9 鏈配對,主要分布于外周血中;Vδ3 細胞常與Vγ2 或Vγ3 配對,可在外周血和肝臟中發現[4]。每個亞型的獨特特征決定了免疫調節在維持體內平衡和自我耐受方面的有效性以及導致自身免疫和慢性炎癥病理結果的上升[5]。
1.2 γδT 細胞的功能 γδT 細胞作為免疫系統的第3 個分支,被認為是第1 個能夠提供免疫效應T 細胞和免疫調節細胞因子的宿主防御機制的T 淋巴細胞[6]。γδT 細胞在正常組織和炎癥組織中的不均勻分布和解剖定位在自身免疫、同種免疫中起重要作用。由于γδT 細胞是先天性淋巴細胞,它能感覺到自身的局部環境,并通過T 細胞抗原受體(T cell receptor,TCR)、細胞因子受體、共刺激受體、抑制受體和自然殺傷受體的組合進行調節。這些受體識別各種環境配體或刺激物、誘導信號級聯,導致關鍵轉錄因子的表達,進而決定γδT細胞的身份和效應功能[7]。活化的γδT細胞具有多種效應功能,包括分泌促炎因子、抗原提呈能力、免疫調節功能、輔助B 細胞功能、誘導樹突狀細胞的分化和成熟等。
1.2.1 細胞因子的產生 γδT 細胞遵循獨特的胸腺內外功能成熟途徑,根據細胞因子譜,γδT 細胞可分為白細胞介素(IL)-17 產生的γδT 細胞、干擾素(IFN)-γ 產生的γδT細胞和抗原提呈的γδT 細胞[8]。γδT 細胞在免疫應答早期就動員,在胸腺成熟期間,γδT 細胞亞群的印記導致在沒有TCR 激活的情況下產生強效促炎性IL-17 的先天能力[9];在自身免疫模型中Vδ1γδT 細胞可活化產生大量IL-10,少量IL-2、IL-4、INF-γ,還可通過凋亡相關因子配體相互作用及穿孔素顆粒等途徑產生細胞毒作用;Vδ2γδT 細胞其亞群存在感染部位,產生大量的INF-γ;Vδ3γδT 可以釋放Th1、Th2、Th17 細胞因子,誘導樹突狀細胞成為抗原提呈細胞。它們通過γδT 細胞自身或其他免疫細胞直接或間接誘導自身免疫應答[10]。
1.2.2 識別抗原 γδT 細胞對宿主免疫能力的貢獻是獨特的,因為它們具有獨特的抗原識別特性[1]。表達的γδT抗原受體作為模式識別受體,具有識別病原體相關分子模式和應激誘導自身抗原的能力[3]。根據不同的亞型,γδT細胞可以識別不同類型的抗原。Vδ1T 細胞可以識別MHCⅠ類鏈相關抗原A 和B 以及上皮細胞上頻繁表達的應激誘導分子,并呈γδTCR 依賴性[11]。γδT 細胞對MHCⅠ類分子T22 的識別基本是由TCRδCDR3 區域的一個特定序列模體決定的[12]。Vδ2T 細胞和Vδ1T 細胞可反向激活Toll 樣受體的表達[13]。激活后,Vδ2T 細胞以下方式發揮其潛在的效應功能:產生細胞因子、趨化因子和裂解酶;進行細胞毒性和非細胞毒抗病毒活性;向CD4+和CD8+T 細胞呈遞抗原。Vδ3T 細胞可被CD1d 激活,CD1d 可與糖脂結合,殺死CD1d 靶細胞,釋放多種細胞因子(包括Th1、Th2 和Th17)[14]。
1.2.3 輔助B 細胞 γδT 細胞對體液免疫有很強的影響,具體來說,B 細胞從骨髓開始的一系列發育步驟分化為抗體產生的漿細胞過程都受到影響,表明γδT 細胞有能力調節B 細胞發育的精確階段[15]。活化的γδT 細胞能夠形成γδT-B 細胞協作,控制循環免疫球蛋白水平(所有亞類)并影響自身抗體的產生[12]。γδT 細胞對IL-4的產生有強烈影響,IL-4 是一種1 型細胞因子,在個體發育早期、終生和免疫反應中表達,是控制B 細胞發育和成熟的關鍵細胞因子[13]。在缺乏Vγ4T細胞的情況下,由于γδT細胞間隔的改變和不能產生IL-4,所有這些B 細胞亞群均減少[14]。Vδ1γδT 細胞對活化B 細胞的反應依賴于B 細胞表達B7 和CD39,在與多克隆B 細胞活化和增殖的疾病中,γδT 細胞的擴增一直被觀察到。B 細胞與T 細胞共同作用于適應性免疫反應,都具有抗原特異性的克隆表達受體,其中B 細胞最終產生特異性抗體,T細胞幫助他們達到分化最終水平[10]。
2 γδT細胞產生炎性細胞因子與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研究進展
γδT 細胞在正常組織和炎癥組織中的不均勻分布和解剖定位在同種免疫、自身免疫或免疫中起著重要作用[1]。在某些自身免疫疾病患者的病變中,γδT細胞在浸潤性T細胞中的比例異常增高,γδT 細胞是促炎細胞因子IL-17、IL-23、IFN-γ、TGF-β 的主要來源,這些炎性分子負責形成炎癥環境,通過不同的途徑來增強疾病進展[15]。不同的疾病表型和結果與γδT 細胞的存在或不存在之間的關系可以清楚地辨別出來。現就γδT 細胞分泌的炎性細胞因子與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關系進行闡述。
2.1 促炎細胞因子IL-17 γδT 細胞獲得了胚胎胸腺發育中產生IL-17 的能力。表達γδT 細胞受體的T 細胞是促炎細胞因子IL-17 的重要先天來源[16]。IL-17 的強大炎癥作用主要與招募免疫細胞的能力以及與其他促炎性細胞因子的協同作用有關[17]。
2.1.1 IL-17 參與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疾病的發病AITD 即橋本甲狀腺炎(hashimoto thyroiditis,HT)和Graves病(Graves disease,GD),是常見的器官特異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以淋巴細胞浸潤和甲狀腺纖維化為特征。HT 特征在于大量的γδT 細胞浸潤(其中以Vδ1亞型細胞占優勢)[18],γδT細胞促進HT 患者自身抗體的產生,通過1 個細胞表面FasL和Fas 的結合實現自身免疫性T 淋巴細胞凋亡。進一步研究發現,在HT 和GD 患兒中,血清sFasL 水平均與IL-17 水平呈正相關,提示sFasL 介導的細胞凋亡可能協同IL-17 介導的炎性反應共同參與AITD疾病發生[19]。
IL-17在HT發病機制中的重要性在不同臨床試驗中均得到證實,并得到疾病實驗模型的支持。實驗研究證實了甲狀腺纖維化與炎癥介質增強的關系,在初次診斷的HT患者局部甲狀腺組織中,血清IL-17 水平及IL-17 蛋白的表達明顯高于正常人[20]。甲狀腺纖維化與炎癥介質之間存在相關性,IL-17 及其誘導產生的炎癥因子形成炎癥環境,進一步證實,IL-17 可通過促進間質纖維化進一步加重HT 甲狀腺組織局部炎性反應,繼而導致甲狀腺組織局部纖維化[21]。
2.1.2 IL-17 參與SLE 的發病 SLE 是一種復雜的多系統自身免疫性疾病,影響皮膚、關節、腎臟和神經組織等多個器官的損傷[22]。盡管許多研究表明,由于γδT 細胞的過度活化、凋亡和自噬,SLE 患者外周血中γδT 細胞數量較低[23],但在人類SLE 和動物模型中的一些研究已經證明γδT細胞在發病中的作用[22]。
γδT 細胞可能通過產生各種炎性細胞因子IL-17、TGF-β、IL-4、IFN-γ 和IL-10 參與SLE 的發病[24],大量臨床試驗表明SLE 患者外周血中IL-17 水平顯著升高。SLE 患者的Vδ2γδT 細胞減少和Vδ3γδT 細胞增加,調節失衡的T細胞信號轉導以促進IL-17的產生[25],SLE合并狼瘡性腎炎患者IL-17 水平升高,且IL-17A 水平與疾病活動性評分呈正相關。然而活動期SLE 患者的外周血細胞表現出較高的凋亡速度,推測在活動期SLE 患者中γδT 細胞增殖受抑制與凋亡增加有關[26]。
2.1.3 IL-17 參與自身免疫性肝炎的發病 肝臟是機體進行全面免疫調節或防御的重要器官,肝臟中γδT 細胞是功能特異性亞群,具有調節肝臟疾病發展的功能[27]。γδT細胞在脂肪性肝炎中發揮中心性作用,γδT 細胞通過CCR2、CCR5 和NOD2 信號進入肝臟,并以ICOS-ICOSL 依賴的方式向IL-17A+表型傾斜[28]。An 等[29]報道,來自腸道微生物群的脂質抗原由肝細胞CD1d 提供,并激活常駐γδT細胞,維持IL-17 的產生,促進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發生。數據表明在正常小鼠肝臟中,γδT 細胞表達IFN-γ、IL-22、TNF-α和IL-17A。然而,在脂肪性肝炎期間,肝臟γδT細胞(特別是Vγ4γδT 細胞亞群),在ConA 激發的肝臟中產生IL-17,IL-17 介導的肝細胞、肝星狀細胞、Kuppfer 細胞和激活導致進一步促炎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產生、活性氧的產生和膠原沉積的增加,加重損傷,使肝細胞易于死亡和疾病進展[30]。說明γδT 細胞的活化及其IL-17 的產生是肝臟炎癥和纖維化發生發展的必要條件[31]。同樣,我們發現人類Vδ2γδT 細胞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的肝臟炎癥中起保護作用,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由免疫耐受激活發展,外周血Vδ2γδT 細胞數量減少,隨疾病的進展,Vδ2γδT 獲得CD45RA+CCR7終末分化的效應記憶表型。Vδ2γδT細胞通過產生IFN-γ抑制CD4T細胞分化IL-17[32]。
2.2 促炎細胞因子IL-23 IL-23 是一種主要的促炎細胞因子,負責啟動多種細胞因子如IL-1、IL-6,趨化因子如CXCL、CXCL-2和IL-8的分泌;并且能夠促進記憶性T細胞的增殖和誘導IL-17 的產生[16]。廣泛的病原體相關分子模式和細胞因子可以觸發IL-23 介導的炎性反應,并增加IL-23 的多種效應,使這種細胞因子成為炎癥中心[33]。IL-23介導的炎性反應失調可能導致慢性炎癥和組織損傷,這導致了IL-23與銀屑病等多種自身免疫疾病有關。
銀屑病是一種主要由T 淋巴細胞異常激活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征是角質形成細胞異常增殖和白細胞大量浸潤,有明顯界限的鱗狀紅斑斑塊。IL-23主要由真皮樹狀細胞和巨噬細胞產生,IL-23已明確與銀屑病的發病機制有關,銀屑病皮損中IL-23、IL-17 的基因和蛋白質表達增加[34]。研究表明,IL-17分泌型γδT 細胞在銀屑病皮損中表達頻率較高,即產生IL-23 刺激皮膚γδT 細胞擴張,真皮γδT細胞組成性表達IL-23受體,IL-23通過與IL-23受體相互作用和激活下游信號通路,IL-23 主要刺激Vγ4 和Vγ6T細胞亞群產生IL-17[35],從而加劇了局部炎癥的發生發展。局部皮膚炎癥通過皮膚γδT 細胞群的組成和性質的長期和全身變化,導致對相同刺激的更快和更強的二級反應[36]。后續研究表明,Vγ4γδT細胞主要誘發皮膚炎癥,是IL-17的主要產生者。具體來說,脂聯素是胰島素代謝的介質,通過結合脂聯素1 抑制小鼠真皮Vγ4γδT 細胞產生IL-17,脂聯素缺乏小鼠表皮Vγ4γδT細胞浸潤增加,出現嚴重的皮膚炎癥[37]。IL-23/IL-17 軸在銀屑病發病中的中心作用一直是研究重點,阻斷IL-17A、IL-17 受體單位或IL-23 P19 可以逆轉銀屑病的臨床、組織和分子特征[38];并且γδT 細胞或IL-17 受體缺乏可顯著降低IL-23 誘導的表皮厚度和中性粒細胞浸潤,而IL-23/IL-17抑制劑已顯示出治療作用[37]。
3 小結與展望
外周血γδT 細胞是先天性和適應性亞群的異質混合體,機體不同器官間的免疫細胞的適當分布是保證免疫系統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γδT 細胞產生過度的促炎因子、致病性自身抗體,最終導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反有研究表明,γδT 細胞在阻止自身免疫反應和減輕自身免疫反應中有調節作用。目前γδT 細胞在自身免疫反應中的作用證據尚且不足,限制了更為確切的發病機制。因此未來仍需繼續尋找γδT 細胞分泌促炎細胞因子的作用機制,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診斷、治療提供更為直接的證據和更為方便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