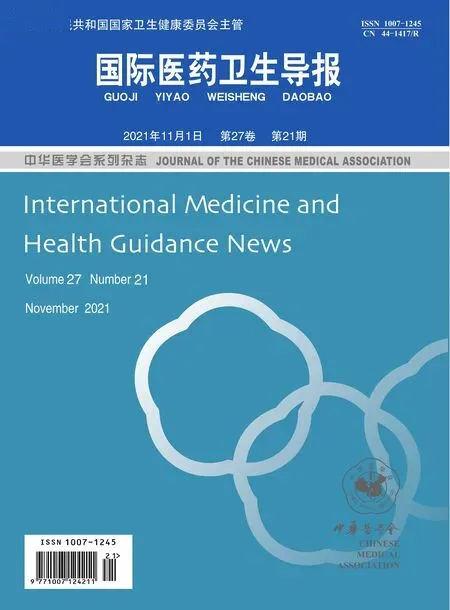潰瘍性結腸炎復發因素的研究現狀
李秀美 徐寧
濱州醫學院煙臺附屬醫院消化內科一病區,山東 264100
潰瘍性結腸炎的診斷缺乏“金標準”,需排除因感染或其他因素引起的結腸炎性病變,屬于排他性疾病[1]。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UC)在臨床上主要表現為反復發作的腹痛、黏液膿血便合并腹瀉、里急后重等,部分UC患者還并存不同程度的全身表現(腸道外表現)[1-2]。目前UC的臨床分型主要分為初發型及慢性復發型[3],其中慢性復發型更為常見,即達到臨床緩解期后再次出現癥狀。在Keshteli 等[4]的研究中,對已達到臨床緩解的 20 名 UC 患者隨訪,發現有7 名患者在研究期間復發,復發率達35%。我國有研究學者在對97 例患者隨訪2 年,期間有49 例(64%)復發[5]。由此可見,UC在臨床上復發率較高,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活質量,并且治療難度增加。引起UC復發的因素較多,但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較少。結合目前研究,就內鏡表現、感染、飲食等因素對UC復發的影響加以綜述,希望以后對此方面研究有積極作用。
1 內鏡下表現及病變范圍
1.1 內鏡下及組織病理學表現 根據2018 年炎癥性腸病共識意見對潰瘍性結腸炎的分析,內鏡檢查及腸道黏膜活檢是診斷UC的主要標準之一,通過鏡下表現將腸道炎癥的嚴重程度分為輕、中、重3 個級別[1]。同時共識還指出隱窩基底部漿細胞增多是UC最早的光學顯微鏡下表現,且預測價值較高。腸黏膜組織炎癥可增加疾病復發及結直腸腫瘤的風險[6]。國外有研究表明,UC 的組織學表現中基底漿細胞增多、隱窩結構改變會存在復發的重大風險,組織病理學在預測復發和充分評估炎癥水平方面的潛在價值對后續治療有積極意義[7]。2019 年美國胃腸病學會指南也提到了黏膜愈合,進一步說明組織學緩解的重要性及地位。由此可見,及早行結腸鏡檢查及病理活檢有助于發現早期病變,提高緩解率,降低復發率。
1.2 病變范圍 通過內鏡檢查將所見炎癥累及腸道的最大范圍做出說明(即蒙特利爾分型),E1(直腸):局限于直腸,未累計乙狀結腸;E2(左半結腸):累及左半結腸,即脾區以遠;E3(廣泛結腸):廣泛病變累及脾區以近乃至全結腸。華婷琰等[8]通過對71例UC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發現病變范圍越廣,各主要臨床表現的發生率、病情的嚴重程度都隨之增加,且病變范圍與內鏡下觀察到的病變嚴重程度呈正相關,同時腸外表現也更易發生于病變范圍廣泛者的結果。也有研究進一步證實了上述觀點,病變范圍與UC的整個病程中并發癥的發生率、病情嚴重程度及預后有很大關系[9]。通過內鏡檢查,明確炎癥病變程度、病變范圍,對制定治療方案及隨訪計劃均有重要意義。從以上層面來看,不僅內鏡下炎癥評分低、病變范圍狹窄的患者預后好,復發率低,且對UC患者完善內鏡檢查進而明確上述指標分級,可以選擇更有效的治療,從而提高臨床緩解率、減少重復住院率。
2 感 染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腸道感染不但能夠誘發UC,更與UC 的復發有關。腸道感染可以不同程度的引起菌群紊亂、異常的免疫反應,近些年幽門螺桿菌(Hp)感染、巨細胞病毒感染以及各種感染引起的腸道菌群失調一直是UC 復發的研究熱點。
2.1 感染致腸道菌群失調 腸道微生態與腸道免疫系統相輔相成,在UC 的發生、發展及復發中占據了重要角色[10]。正常的腸道菌落在機體中發揮眾多有益的生物學作用,并協助構建腸上皮保護屏障,促進腸黏膜免疫系統發育,從而保護腸壁,減少腸道炎癥的發生[11]。由此可見,菌群失調對UC復發有一定影響。同時腸道感染使UC患者腸道菌群多樣性減少,有益菌減少,而致病菌增多,從而導致復發。有大量報道表明UC 患者腸道內致病微生物檢出率高于正常人,較常見的有艱難梭菌、致病性大腸桿菌及巨細胞病毒[12]。且近些年通過糞菌移植改善微生物多樣性從而維持炎癥性腸病臨床緩解的研究越來越多,且取得了積極的結局[13-14],亦可證實這一觀點。
2.2 Hp 感染 Hp 感染被證實與多種消化道疾病的反復發生密切相關。李興豐和賴衛強[15]通過一組臨床對照實驗發現Hp 感染可能是UC 疾病發展過程中的保護因素,其機制可能為通過作用于促炎性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IL)-1、IL-6、腫瘤壞死因子(TNF)-α]使之下調,而對抗炎因子(IL-10)進行上調,且增加了益生菌濃度。同時國外學者研究發現Hp 感染后可刺激機體產生抗體,提供免疫保護,并可同時抑制腸道中大腸桿菌產生并釋放IL-1 和IL-12,從而下調腸道黏膜的炎性反應程度,減輕疾病嚴重程度并減少復發[16-17]。
2.3 巨細胞病毒感染 巨細胞病毒是一種機會致病性病毒,因UC 患者需長期應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劑治療,且因腸道病變導致營養吸收差、腸道保護屏障受損,均增加了病毒或細菌的易感性,而巨細胞病毒感染又可加重UC的病情。我國學者研究表明,與未合并巨細胞病毒感染患者比較,感染患者發熱、腹痛等炎性反應更重、病情更復雜,且存在激素抵抗現象,延長了治療時長[18]。有研究表明,予以UC患者抗病毒治療可降低腸道手術切除概率[19];但也有不少臨床試驗提示不論是否存在巨細胞病毒感染,對UC患者的臨床結局無明顯差異,易不會導致UC復發。因此,巨細胞病毒感染是否為UC的因素之一,還需更多的試驗加以證實。
3 生物指標
對于潰瘍性結腸炎預測復發方面暫無公認的金標準,臨床上多通過患者表現出的病史、查體及輔檢結果等來綜合評估。因內鏡檢查為有創操作,不易被更多患者接受,所以找到1 個理想的實驗室指標尤為重要,可以更加便捷的預測UC 復發,及早進行干預。已有研究證實,鈣衛蛋白(calprotectin,CP)水平可預測 UC 復發,國外學者 Tibble等[20]研究中,CP 的水平為 50 μg/g 或更高時,預測復發風險增加13倍。吳道刻等[21]通過一項前瞻性研究,對196例UC患者留取糞便標本檢測CP,發現糞便中CP 含量高的分組復發率顯著高于正常組,并將臨床數據繪制成ROC,表明CP 預測早期復發的最佳預測值為269.7 μg/g。由此可見,針對復發高危患者可常規檢測此指標,及早調整治療策略,從而降低復發率。
4 煙草攝入
UC 的發生、復發與環境因素密切相關,而吸煙是其中最主要的環境因素。已有科學研究表明吸煙是UC 的保護因素,戒煙者及不吸煙者UC發生率更高,甚至于UC患者在戒煙后更易復發,已戒煙的UC患者在停用激素等藥物后可以通過復吸小劑量的煙草維持臨床緩解。這一觀點由Harries 等(1982 年)以問卷的形式首次提出,隨后有更多研究證實了這一關系。其機制可能與煙草中的尼古丁影響了腸道的神經內分泌活動有關,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吸煙這一環境因素作用于UC患者可能的機制為:促進結腸黏液的生成、減少結腸血流量從而減少結腸黏膜表面炎癥介質、通過增加結腸上皮細胞纖維間的緊密性而加強腸道的屏障作用、調節腸道運動及CO 的抗炎能力[22]。由此可見,吸煙不是潰瘍性結腸炎的復發因素,還可維持臨床緩解狀態減少腸道炎癥的發作及復發。但吸煙對人體健康弊大于利,仍需勸導吸煙患者減少吸煙量。
5 飲 食
飲食是除吸煙外另一重要的環境因素,科學飲食不僅能起到減低腸道炎癥發作及復發,還有輔助治療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規范的飲食指導是控制炎癥性腸病的關節環節之一。綜合目前研究,引起UC患者重復住院的飲食因素主要有:辛辣生冷食物、飲酒及高脂、高蛋白飲食。其中硫化氫是蛋白質的代謝產物,會對結腸細胞產生毒性作用,導致結腸黏膜損傷;在Geerling等[23]的回顧性研究中則證明了若過多攝入脂肪酸,則會代謝生成促炎因子(如白三烯類物質),進而影響腸道對膽固醇類物質的吸收,吸收不良后在腸道聚集形成高凝狀態,引起腸道血管痙攣,血管緊張度增加,進而影響腸道血供,最終導致黏膜損傷;在2012 年周云仙和應立英[24]通過一項納入81 例炎癥性腸病患者的回顧性研究中發現,辛辣生冷食物、酒類和油膩食物均為潰瘍性結腸炎患者的不耐受食物,會影響疾病的轉歸,但存在個體差異,在后續的研究中應更加細化。綜上,對UC 患者進行科學的飲食管理,對其臨床結局有積極的影響,但應個體化分析,最終以減少藥物治療、提高生活質量及減少住院次數為目標。
6 維持治療
不限于UC 治療,現患者因對疾病認識不足、某些疾病治療時間過長、對藥物不良反應的抗拒等原因,不按醫囑用藥,甚至自行停藥,是疾病復發及控制率低的重要原因。針對此,應積極加強患者教育、增加隨訪次數,督導患者規范用藥,從而減少疾病的復發。
7 腸外表現(extraintestinal manifestations,EIM)
炎癥性腸病的EIM 多樣,且發病率較高,患1 種EIM 后又增加了其他類EIM 出現的風險,這一特點增加了UC 治療的難度。UC 常見的EIM 主要有關節損傷、皮膚黏膜受損表現、眼部病變、肝膽疾病等[1]。由此可見,潰瘍性結腸炎不僅是一種消化系統疾病,更是一種累及全身各系統的綜合性疾病,部分EIM 可先于UC 發病,掩蓋原發病病情,對UC的臨床經過、治療及預后有明顯的影響[25]。國內學者通過實驗表明UC 的EIM 可能與結腸炎的半年內及1 年內復發有關[26]。雷曉燕等[27]曾回顧性調查 115 例住院患者,經對數據進行logisitic 回歸分析顯示合并EIM 與UC 患者的重復住院率呈正相關性,其中以肝功能損害為主要變現。因此對于合并EIM 或以EIM 為首發癥狀的UC 患者,應完善相關炎癥免疫指標,防治EIM 的出現或加重。綜合目前已有研究,大多數EIM 與腸道炎癥相互促進,增加了治療及緩解難度,了解并掌握其發病機制,有助于UC的早期診斷和治療,從而盡早進入臨床緩解,減少重復住院率。
8 基因水平
UC 具有反復發作的特點,除與上述環境、腸道微生物等多種因素有關,在基因(遺傳)水平上也有一定關系。近年來研究較多的微小RNA(miRNA)在多種免疫性、腫瘤性及炎癥性疾病中存在表達異常,其主要通過影響下游基因轉錄后水平的表達來發揮生物學功能[28]。在UC患者體內,腸道黏膜內的miR-155 基因表達較正常人升高,并使下游靶基因轉錄異常,從而促進UC 的發生發展[29]。張鳳等[5]采用熒光定量PCR 檢測UC 患者及健康者體內miR-155 的相對表達量,發現血清高miR-155表達患者UC 復發風險高于低表達患者,其機制可能與腸道黏膜屏障功能障礙有關。其次,本研究也進一步證實了EIM、CRP、ESR 是UC 患者復發的危險因素。也有研究表明,信號素3E(SEMA3E)基因可調節腸道免疫功能,UC 的發生、發展及緩解后復發與腸道免疫失衡密切關聯,但有關SEMA3E miRNA與UC復發關系的研究還較少。我國學者通過對109 例UC 患者隨訪,其中48 例(44%)患者復發,且復發患者的SEMA3E miRNA 相對表達量為(0.62±0.15),低于未復發(1.09±0.24)患者[30]。由此可見,在UC 的疾病進展中,遺傳因素也有著重要的地位。
綜上所述,UC 的復發與多種因素相關。內鏡及病理檢查對疾病的診斷、隨訪極為重要;達到臨床緩解或在治療期間的患者,應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和健康良好的生活習慣;感染可在多層面上導致UC 的復發,應定期檢測炎癥指標、維持腸道菌群動態平衡,及時發現致病菌入侵或“異常”菌群增多現象。除上述外,患者的情緒、職業、年齡等均會對UC 的發病及復發產生影響。因此,臨床醫生治療時要根據患者的實際情況,制定治療方案,減少疾病復發。而對于今后的研究,個人認為,基因層面亦至關重要,雖然個人基因無法改變,但可通過基因檢測等技術,及早發現高危人群并給予干預措施。UC 復發率高的特點嚴重降低了患者的生命質量,甚至帶來癌變等更嚴重的后果,希望后續研究能發現更多的相關誘發因素,早期干預,給UC 患者帶來更多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