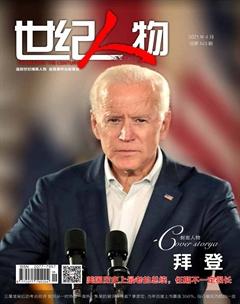東吳的毀滅該怪誰?

孫權為掌控權力,喪失了進取之心。曾經的江東猛虎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則是一個被權力欲沖昏頭腦,以致人心散盡的“孤家寡人”。當晉朝軍隊揮師南下時,長江天塹再也無法保衛江東了。隨著孫吳的滅亡,三國的時代畫上句號。
自秦漢以來,這段中華帝國第一次陷入分裂的歷史,見證了人心的向背離合,給了后人寶貴的經驗。但重塑帝國大一統的西晉王朝,并未像秦漢那樣給中國帶來一段長期的統一時期。
此后,中華帝國開始面對一個新的主題,這個主題一直伴隨帝國的歷史長達千年,直到清王朝方才塵埃落定。
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三國志》卷四十六《孫破虜討逆傳》
孫策的遺愿
建安五年(200 年),江東霸主孫策遭仇人暗算,匆匆撒手人寰,臨終之時,他將自己的基業,托付給了弟弟孫權,而以上這段話,既是小霸王臨終時的遺言,也多少預告了自孫堅創業以來的東吳政權,即將迎來一場政治發展的轉向。
東吳高層當家人的更替,到底預示著什么呢?要想理解東吳內部發生的變化,還得從孫權的父親說起。
自黃巾軍起義以來,東漢帝國四分五裂,軍閥混戰,其中,以江東人士孫堅為首的一支武裝力量,先依附于袁術,后向東南發展,渡過長江,占領了大片土地,后來參與三分天下的東吳政權雛形,即于此時期形成。
但是,由于輕敵,孫堅在進攻長江中游的江夏時被劉表手下黃祖(一說為呂公,見前文)所殺,而他的兒子孫策,則在經歷了短暫的喪親之痛后,迅速從痛苦中走出來,接過了父親手中未竟的霸業。
孫堅一家,原為江東的寒族,所以回歸家鄉的樸實情感,自然成為其政治事業的推動力。可是,此時孫策接手的政權當中,大多為跟隨父親南征北戰多年的江西舊人(淮泗集團),江東士族雖然控制鄉里的財富和人丁,但很少被其接納。
所以雙方的矛盾不小, 而更重要的是,孫策一家出身卑微,江東士族仍奉東漢王朝為正朔,這也在無形中不斷撕裂著新生的東吳政權。
此時,對于孫堅的兒子們來講,最為可取的辦法就是團結江東 士族,利用其錢糧和威望做支撐,鞏固來之不易的基業。
可是,孫策并沒有這么做,他崇尚武力征伐,不肯輕易向被壓制的江東士族 拋出合作的橄欖枝,所以對方看他缺乏合作誠意,也處處與其作對, 例如許貢門客刺殺孫策,即是孫策與江東士族關系惡化的后果。
不過,創業的坎坷和艱辛,畢竟在逐漸改變著孫策的政治理念,可命運之神并沒有留給他行動的余地。俗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當死亡向孫策襲來時,他最先想到的,也是最后想到的, 就是告誡自己的兄弟,一定要改變自己以往過于剛硬的政策,注重團結江西舊人和江東士族,尤其是后者。
團結新舊勢力
孫權何等聰明,他掌權后,十分重視兄長的經驗,克制傷悲,臥薪嘗膽,除了繼續重用來自江西的舊人,如彭城張昭、廬江周瑜、臨淮魯肅,以籠絡父兄留下的人才,還特意主動開放政權,積極聯合江東地方勢力。
所以在孫權當政以后,東吳迎來了發展的高峰,不但結束了孫策死后的短暫動蕩局面,還主動出擊,擊殺了與自己有殺父之仇的黃祖,引得荊州劉表叫苦不迭。
在取得一部分江東士族的支持后,孫權繼續對南用兵,進攻南方的少數民族山越。東吳大軍層層圍困,后逼迫其離開山林,遷到平原丘陵從事農業生產,成為東吳政權治下的編戶齊民,這又加強了孫權的實力。
日后,統一北方的曹操出動超過二十萬大軍南下赤壁,試圖進攻長江以南地區。江東士族為保全財富,主動與孫權親近,以抗拒曹操,維護一方安寧,免受戰亂波及。
因此,在孫策遺言的影響和現實政治的需要下,東吳內部凝聚力大大加強,此時是東吳國力的上升期,也是孫權與江東士族關系的蜜月期。
當然,政治講究剛柔相濟,孫權之所以能鞏固自己的政權,除了主動向地方勢力分享利益,允諾對方保留“復客制”與“世襲領兵制”等特權制度外,其長期依賴的江西舊人也起到了牽制、平衡江東本地勢力的作用。
不過,這種短暫的平衡很快遭遇挑戰,先是周瑜、魯肅等舊臣離世,江西勛貴凋零殆盡,繼之的則是來自江東的后起之秀,例如出自吳郡大族陸氏旁支的陸遜,因屢立戰功,坐到了丞相的高位。
收服山越、奇襲荊州襲殺關羽和夷陵之戰痛擊劉備,這些都是陸遜的政治資本,而這也暗示著江東士族在經歷了被壓制的低谷后,將迎來政治局面的柳暗花明。
東吳進入難得的安定期
面對江東士族的壯大,孫權也并非無動于衷。一方面,此時漢獻帝禪讓帝位予曹丕,割據益州的劉備也在諸葛亮等人的支持下即位稱帝。孫權得到這些消息后,也按捺不住效法對手稱帝的心情。
所以,為了服務于自己的這個最高目標,他還需要承認江東士族的既得利益,以換取地方勢力對他稱帝的認可。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本地的江東士族集團不受抑制地膨脹,這必將威脅皇權的穩定,所以在稱帝后不久,他又相繼設立校事、察戰等官職,負責監視群臣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