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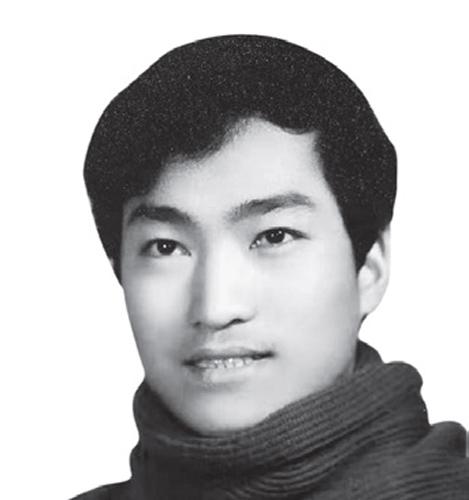
金弢
來德后一個問題始終讓我糾結:德國和日本兩國為何對歷史的反省會如此截然不同?
1985年我隨王蒙率隊的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西柏林,與德國諾獎得主、《鐵皮鼓》作者格拉斯二次相會。二十七年后,他發表了批評以色列及德國政府的詩作《非說不可的話》,這首詩在德國引發了全民范圍的大討論,批評之聲響徹云霄。格拉斯在給我的回信中表示:“對我的作品,多家刊物以惡劣的方式作出回應,他們對我詩作的內容置若罔聞,將我本身當作他們的攻擊目標。我雖事先有所心理準備,然他們的所作所為、對我的侮辱,其程度之強烈,完全出乎我的預料;他們蓄意損人的詆毀,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
有一種觀點:“歷史的責任不能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整個民族都有責任。”我贊同這種說法。加入名為 Unitas 的社團后,我向德國友人提問:“你們對那段歷史作何感想?是否感到自己也負有責任?”回答是:“我們從不認同納粹政權,它跟我們不能同日而語。”他們表示納粹迫害的不只是猶太人,還有持不同政見的德國人,只要不符合法西斯思想理念,就無一例外會遭到迫害。他們這個歷史傳統悠久的知識團體在30年代被嚴厲取締就是一例。
“我們雖是同一民族,但政見判若云泥。反法西斯組織白玫瑰紹爾兄妹和謀殺希特勒的德國軍官馮·施陶芬柏格只是成百上千人物事例中的一二,他們代表著日耳曼民族的正直與良知。”
一位年長會員說,1950年代初他去美國,總是被人問:“你也是納粹嗎?” 他說:“好像我們是個德國人就是納粹!” 我問他們如何作答,他們說:“我會盡力解釋,萬一解釋不通,這歷史的包袱只能承擔下來,誰讓我們是德國人!然而我們的民族共識是,對那場人類劫難承認得越徹底,我們的包袱就越輕。新納粹主義只會讓我們再次承擔起歷史的重負。”
德日兩個民族對自己那段不光彩的歷史截然不同的態度,或許源自國情不同。
“二戰”時的日本舉國上下萬眾一心,幾乎沒有出現過對本國公民的大規模迫害與屠殺,在日本民族的心目中,對外侵略是一場民族戰爭,贏則俱榮,敗則俱毀。一旦國家認罪,則意謂著每個人認罪。因此戰后幾十年來歷屆政府都死不道歉,甚至試圖歪曲歷史。
而德國是撕裂的。1980年代,分裂的東、西德國都不遺余力地標榜自己如何對納粹的清算,都把歷史的罪過推到柏林墻的另一邊。說來也巧,兩個集中營,一邊一個。
另外,地處歐洲中心的德國,戰后四周強國林立,若想擺脫歷史,脫穎而出,唯獨了結過去,從零開始。而在當年的亞洲,日本一家獨大,這種壓力對日本微乎其微。
日本現行的民粹主義思想在德國是行不通的,德國民族與納粹歷史的決裂已被寫進法律。任何一個德國政要想留守政壇,務必與歷史劃清界限,無條件地同情、支持、幫助猶太人,而這正是格拉斯被指責的焦點所在。
同時,歐洲敏感的地緣關系也迫使德國走這一步,英、法兩個戰勝國無時無刻不死死盯著,一再翻舊賬,容不得丁點的風吹草動。執政黨對歷史的態度,更是在野黨攻擊的法寶。這種精神壓力,日本人是感受不到的。
這兩個民族都身負歷史罪孽,但國情相悖,也導致了一國徹底反省,甚至唯恐不及; 另一國則麻木不仁,至今無動于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