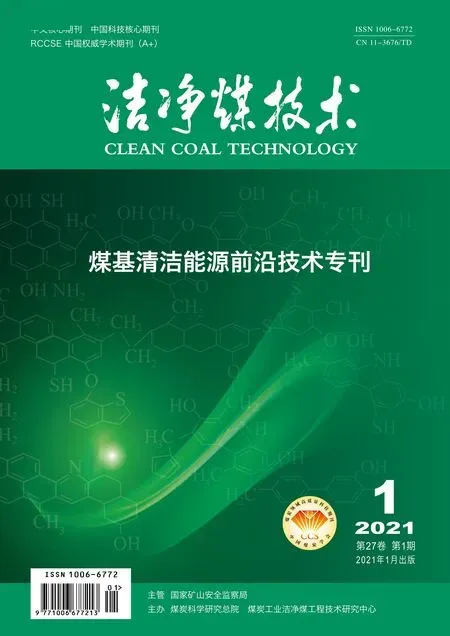不同揮發分含量煤種與熱解半焦混燃熱態試驗研究
陳登科,閆永宏,彭政康,王興益,孫劉濤,孫 銳
(哈爾濱工業大學 能源科學與工程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
0 引 言
我國當前正處于城市化、工業化階段,需要大量能源消耗作為支撐,“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使我國形成了以煤炭為主體的一次性能源消費結構[1],占我國已探明煤炭儲量55%以上的低階煤(褐煤/次煙煤)煤化程度低,蘊藏的揮發分相當于1 000 億t油氣資源[2]。但由于低階煤水分高,直接燃燒或氣化效率低,且現有技術無法充分利用其資源價值,導致煤炭資源的巨大浪費。熱解半焦是指泥煤、褐煤和高揮發分低變質煙煤等在隔絕空氣的條件下受熱,發生一系列物理化學變化析出大量輕質揮發分產物被利用后剩余的固體產物[3]。熱解半焦在電站鍋爐中的應用前景主要包括:作為可處理的大量工業廢物;可成為煤炭替代品,節省煤炭資源;若使用恰當,將有助于減少電廠的污染物排放、排渣和腐蝕。但由于其揮發分較低(Vdaf<10%),著火和實現穩定燃燒較原煤需更高著火溫度,為拓展其在電廠動力用煤等領域的應用,有必要引入一些易燃高揮發分煤種作為混燃燃料,以改善電站鍋爐中熱解半焦的燃燒特性。
目前混煤燃燒主要關注問題包括混煤著火性能和燃燒穩定性、碳燃盡率、污染物NOx排放等[4],試驗研究手段大多是在熱重分析或管式沉降爐上進行。邱建榮等[5]選取多種單一煤及其按不同比例組成的混煤在沉降爐上進行了一維燃燒試驗,認為摻混比和混燒煤質對混合燃料著火性能影響較大,混煤中高揮發分煤比例增加時,著火溫度降低,采用分級燃燒并摻燒高揮發分煙煤時,燃盡率明顯提高。陳鑫科等[6]采用數值模擬方法研究了混煤摻燒方式和優化配風對著火和燃盡特性的影響,結果表明:摻燒方式是影響混煤燃燒著火特性的重要因素;在爐外摻混方式下,摻入高揮發分煤能改善低揮發分煤的著火特性;爐內摻燒方式可抑制混煤燃燒過程中的氧競爭作用,提高低揮發分煤的燃盡率。
近年國內外部分學者主要關注煤與石油焦[7]或生物質焦[8-9]的混合燃燒,對煤與熱解半焦混合燃燒的研究不多。李慧等[10]在兩段式滴管爐上研究了熱解半焦空氣分級燃燒的NOx排放規律,結果表明:在空氣分級燃燒中,相同主燃區溫度條件下,二次風比例由高到低變化時,NOx排放先迅速下降再緩慢回升,燃盡率先快速升高而后趨于平緩。梁寧等[11]利用HCT-2型綜合熱分析儀,選取不同比例的熱解半焦與煙煤進行混合燃燒試驗,結果表明:隨著半焦比例的增加,混合燃料的燃點逐漸升高,最大燃燒速率和平均燃燒速率逐漸降低,燃燒區間逐漸向高溫區移動,燃燒逐漸困難。燃性指數Cb、穩燃性指數G、綜合燃燒特性指數SN都隨半焦份額的增加而降低。
由于不同揮發分煤種的反應性不同,其與半焦摻燒形成的混合燃料的燃燒特性(如著火距離、燃盡率、NOx排放等)受到混煤的交互作用影響而無法按單一煤質線性加權預測。本文在350 kW中試規模煤粉爐上進行濃、淡著火熱態試驗,選取典型褐煤(HM)、煙煤(YM)、次煙煤(LRA)分別與神木熱解半焦(SC)進行混合,熱解半焦摻混比例為50%,研究不同揮發分含量煤種與SC摻混的混合燃料的著火特性及NOx排放特性影響,并深入研究其燃燒過程,為大型電站鍋爐燃用混合燃料提供參考與指導依據。
1 試 驗
1.1 350 kW煤粉燃燒系統
試驗在350 kW煤粉燃燒系統(PCFS)上進行(圖1),該系統主要由爐膛、給粉系統、供氣系統、丙烷穩定燃燒系統、空氣預熱系統、測量和采樣系統組成,主要設計參數見表1。其中爐膛為管式結構,沿豎直方向布置,上部為主燃燒區,是試驗系統的關鍵組成部分,總高為1 280 mm。試驗裝置端部一次風/混合燃料噴口、二次風射流噴口及丙烷助燃燃氣噴口對稱布置,如圖2所示。正式投入混合燃料前,為創造燃料著火的高溫環境,需要對爐膛進行預加熱,預熱過程的高溫煙氣由丙烷氣體燃燒產生。混合燃料特性試驗中,保持總空氣流量及一、二次風比率不變,設定主燃燒區出口空氣過量系數為0.9,一次風速為19.7 m/s,一次風溫為210 ℃,混合燃料一次風粉煤濃度的濃淡比(濃淡比是混合燃料射流中濃側粉煤濃度與淡側粉煤濃度之比[12-13])為2。

圖1 350 kW PCFS熱態試驗系統

表1 PCFS主要設計參數

圖2 爐膛頂部一次風煤粉燃燒器和氣體助燃燃燒器裝置結構布置
PCFS系統的啟動過程為:首先啟動引風機將爐內降為負壓,然后啟動丙烷燃氣系統投入高溫煙氣,每側設定為50 kW熱功率運行(點火熱功率100 kW)。爐膛中部溫度達到400 ℃時,啟動鼓風機,提供一次風和二次風點燃混合燃料。混合燃料儲存在2個給粉倉中,通過一次風攜帶進入爐膛。混合燃料著火穩定后,逐漸將每側的丙烷燃氣系統熱功率降為25 kW(伴燃熱功率50 kW),此時爐內總燃燒熱功率維持在350 kW。爐內溫度變化小于10 K時開始測量,達到試驗條件穩定燃燒狀態約需1 h。
1.2 火焰溫度測量
爐子側面有30個水平孔,用于測量徑向溫度。燃燒器出口與孔中心線之間的垂直距離用Z表示,由Z=180~980 mm,每2個測量孔之間的垂直距離為160 mm。每個橫截面處,將測量點按徑向布置爐膛中心r=0、20、40、60、80、100、150、200、300 mm處。采用外徑16 mm的剛玉鎧裝S型熱電偶測量爐內橫截面內的徑向溫度,該熱電偶測溫范圍為600~1 600 ℃,基本誤差限為±0.25%t(t為感溫元件實測溫度值,℃)。爐膛頂部煤粉燃燒器的2個噴口間布置一個30 mm的測量孔,從測量孔探入2個外徑8 mm的鉻鎳鐵合金K型鎧裝熱電偶,實現濃、淡一次風側軸向溫度的測量。從燃燒器出口到測量點距離Z=0~930 mm,該熱電偶測溫范圍0~1 300 ℃,基本誤差限為±0.75%t。
1.3 爐內煙氣成分測量
徑向溫度測量完成后,拔出熱電偶,插入取樣管,測量爐子中的徑向煙氣成分。半徑煙氣測量孔沿軸向距離Z=180~820 mm,測量點在每個橫截面處由爐膛中心起分別位于r=0、±20、±40、±60、±80、±100、±150、±200、±300 mm(其中“+”為徑向測點位于一次風濃側噴口下游,“-”為徑向測點位于一次風淡側噴口下游)。每2個煙氣測量孔之間的垂直軸向距離為160 mm。
煙氣成分通過采樣系統(圖3)分析,該采樣系統由水冷式吸氣取樣探頭、纖維過濾器、干燥瓶和煙氣分析儀組成。

圖3 煙氣采集測量系統示意
煙氣采樣過程為:將位于中心的取樣管沿高壓方向插入爐膛,該取樣管由水冷不銹鋼管圍繞,抽取高溫熱煙氣。熱煙氣迅速被水冷卻使煙氣中活性組分反應終止,并依次經過飛灰過濾器、干燥瓶,然后通過GASMET DX-4000便攜式FTIR氣體分析儀進行干煙氣成分在線分析。所測氣體種類包括O2、CO、CO2、NOx(NO、NO2),氣體組分測量范圍內精度為±2%,煙氣分析儀所測各組分在測量前已由標氣校準。
1.4 燃料特性和試驗運行工況參數
試驗選取褐煤(HM)、煙煤(YM)、次煙煤(LRA)分別與神木半焦(SC)摻混形成混合燃料(摻混比為50%,摻混比為混合燃料中SC的質量分數)。不同揮發分煤種與神木半焦的工業分析和元素分析見表2。將燃料分別研磨至細度均為R90=9%,利用激光粒度儀對燃料進行粒度分析,得到煤粉細度的粒徑分布如圖4所示,在攪拌機中混合均勻后送入爐內。

表2 不同煤種與神木半焦工業分析和元素分析

圖4 試驗煤粉細度的粒徑分布
由于Vdaf是衡量煤質是否易于燃燒的重要指標,Vdaf高,表示煤易著火,也易燃燒穩定和燃盡,因此本文將混合燃料的Vdaf作為試驗工況劃分的重要依據,根據收到基與干燥無灰基的換算因子,得到混合燃料的Vdaf,具體見表3。

表3 混合燃料性質
每種試驗工況的主要操作參數見表4。由于混合燃料熱值不同,給煤速率不同(本文試驗條件差異引起的微小變化將產生較小影響)。確保每個工況中混合射流的燃燒均已達到連續穩定狀態,達到穩定燃燒工況的判斷方法為:① 試驗過程中各測溫點溫度變化均小于10 ℃;② 試驗過程中煙氣組分,如O2及CO在一個相對穩定范圍內波動;③ 通過爐膛壁面上預留的視窗觀察煤粉射流及火焰情況,確保著火燃燒穩定。

表4 試驗工況主要參數
2 結果與討論
2.1 不同揮發分含量煤種對混合燃料著火和穩定燃燒的影響
2.1.1對混合燃料著火溫度和著火距離的影響
對于混合燃料射流,本文通過爐膛軸向溫度變化反映其著火特性[14-15],不同揮發分含量煤種混合射流濃、淡側火焰軸向溫度分布如圖5所示。由于對每一工況的軸向溫度進行了2次測量,故可在圖5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測點增加誤差棒,表示2組數據與平均值之間的最大偏差,可發現誤差范圍較小,且經過計算得到軸向溫度的相對偏差均小于2%。

圖5 不同揮發分含量煤種混合射流火焰軸向溫度分布
由圖5(a)可知,濃側射流著火時,隨著軸向距離增加,混合燃料軸向溫度變化趨勢相似,在混合射流還未相交至中軸線前,軸向溫度均逐漸升高,之后由于2股獨立射流開始在爐膛中軸線上相交混合,軸向溫度有所下降,最后混合燃料不斷卷吸周圍高溫煙氣進行強烈的對流換熱作用,同時吸收爐膛內壁的輻射傳熱,軸向溫度均急劇增加直至著火。在低溫區域(定義Z<500 mm),HM+SC混合射流始終具有較高的軸向溫度,這是因為其揮發分最高,在著火初期率先被點燃,迅速釋放大量熱量,將煙氣加熱到足夠高的溫度,從而在較短軸向距離內引燃焦炭,此時O2濃度仍很高,該區域內軸向溫度增幅較大,能快速達到燃燒穩態。隨著混合燃料揮發分縮減,反應釋放熱量減少,焦炭著火距離延長,同一截面處軸向溫度逐漸降低,分析認為所有混合射流的著火區間在 90~240 mm。從試驗煤樣的著火距離區間之后至500 mm,軸向溫度均繼續增加,混合射流的燃燒更劇烈,但LRA+SC混合射流溫升速率相對最快,這是因為次煙煤水分較大,對射流的初期著火產生了抑制的負效應[16],造成著火初期燃燒較弱,消耗O2也相對較少,但水蒸氣對混合射流后續燃燒會產生促進作用[17],使燃燒變得更加劇烈。在高溫區域(定義Z>500 mm),所有混合射流燃燒已基本穩定,軸向溫度變化趨于平穩,分析認為焦炭燃燒是該區域的主要反應,但著火初期混合射流揮發分燃燒消耗較多O2,使高溫區O2含量相對不足,焦炭燃燒程度較低。
由圖5(b)可知,淡側射流著火時,不同煤種的溫度變化趨勢基本一致,與濃側射流相似:在Z<60 mm,軸向溫度均逐漸升高,Z=60~90 mm,軸向溫度均逐漸降低,Z>90 mm后軸向溫度均急劇升高,但出現明顯溫差,具體原因與濃側射流著火相同。對2側前期著火進行對比分析,發現同一截面處淡側軸向溫度均低于濃側,這是因為淡側射流燃料濃度低,煤粉顆粒間距較大,釋放熱量少且散熱相對較大,火焰較弱不連續,導致燃燒不強烈,溫度較低[18]。
根據謝苗諾夫臨界著火條件,將軸向溫度增加最快位置定義為燃點,即圖5曲線某個轉折點(d2T/dl2=0)[19],并結合著火距離區間排除不合理點,對應點的軸向距離即為著火距離。對圖5(a)中HM+SC混合射流的溫度曲線求二階導可得其著火距離,如圖6所示,其他混合燃料的著火距離計算方法相同;從圖5找到著火距離處對應的溫度即認為是著火溫度,具體如圖7所示。

圖6 濃側HM+SC混合射流對溫度求二階導得著火距離

圖7 混合燃料濃淡測射流的著火距離和著火溫度及其數據點回歸曲線
由圖7可知,各工況下濃淡側著火溫度相近,隨著混煤揮發分的增加逐漸降低。但各工況著火距離隨混合燃料煤種揮發分增加大幅下降,而3組工況其他試驗參數均相同,可以確保混合射流在相同軸向距離處吸收的輻射熱和對流熱相似,且揮發分的促進作用是混合燃料著火的關鍵,因此著火距離的不同主要是由于混合燃料揮發分變化引起的。由于混合燃料的著火首先從揮發分開始,因此隨著煤種揮發分的增加,混合燃料射流著火模式可能由最初的均相-異相聯合著火向均相著火轉換。對比濃、淡兩側射流著火距離,可以發現同一工況淡側著火距離相對濃側增加,特別是在燃用低揮發分煤種時,淡側著火距離較濃側增加幅度較大,這是因為淡側著火初期燃燒較弱,燃料吸收熱量不充分,揮發分釋放量較少,對混合燃料著火不利,使著火延遲,著火距離增大,因此,濃淡燃燒方式將對低揮發分混合燃料射流的著火穩定性強化效果更為明顯。
2.1.2對混合燃料穩定燃燒的影響
1)不同揮發分煤種對徑向溫度分布的影響
除了軸向溫度分布,爐膛徑向火焰溫度分布(圖8)也可以反映混合燃料的著火燃燒過程[18]。由圖8可知,HM+SC工況下,徑向溫度分布左右不對稱,濃側射流整體溫度水平要高于淡側,射流中心偏向淡側煤粉射流對應的-20 mm處,其特點是:Z=180 mm處,射流中心溫度明顯低于外圍區域,表明點火首先發生在射流四周,這是因為丙烷燃燒產生的高溫煙氣首先接觸射流外圍部分,從射流的邊緣點燃燃料,隨后高溫區域向射流中心發展,最后整個射流著火;Z=270~450 mm,徑向溫度急劇增加,可能是發生了由揮發分燃燒到焦炭燃燒的轉化;Z=630 mm后徑向溫度增幅減小,紅色高溫區域緩慢擴大,表明焦炭燃燒已處于穩定狀態;Z=810 mm時,徑向溫度基本穩定,此處O2消耗殆盡且濃度低,焦炭燃燒速度減低。

圖8 不同揮發分含量煤種混合射流徑向溫度分布
對于YM+SC混合射流,Z=360 mm前,徑向溫度變化趨勢類似于HM+SC射流,說明混合燃料也會首先發生揮發分著火,區別在于Z=630 mm處才出現紅色高溫區域,這是因為其著火距離相對較長,焦炭穩定燃燒區域隨之向爐膛下游移動,但由于混合射流后續氧量充足,且固定碳更高,故放熱增加,燃燒更為強烈。混煤燃燒過程中存在促進和抑制作用2種明顯的交互作用,共同影響混煤燃盡特性[20]。前者產生的主要原因是高揮發分煤揮發分產率高,著火及燃燒快,提高了局部溫度,促進低揮發分煤的著火和燃燒,這與HM+SC混合射流最先出現紅色高溫區域的結論一致;而后者產生的主要原因是高揮發分煤會搶先與氧氣反應(即“搶風現象”),消耗大量氧氣,使低揮發分煤燃燒處于欠氧狀態,阻礙了低揮發分煤的燃盡,試驗中表現為HM+SC射流后續燃燒較YM+SC射流更弱。Z≥630 mm時,火焰逐漸充滿爐膛中心靠右區域(-50~+110 mm),燃燒穩定性逐漸加強。
對于LRA+SC混合射流,Z=360 mm處徑向溫度增幅依舊很小,這說明混合燃料盡管已在Z=360 mm前被點燃,但著火較弱,火焰穩定性較差,這可能是因為混合燃料中揮發分較低,著火初期焦炭亦被點燃,發生均相-異相的聯合著火。Z=720 mm后出現紅色高溫區域,表明焦炭穩定燃燒位置進一步向下偏移。以上結果表明隨著混合燃料揮發分降低,著火延遲,穩定燃燒區域隨之向下游偏移,但YM+SC射流后續燃燒更為強烈。
2)不同揮發分煤種對徑向煙氣分布的影響
燃燒區徑向O2、CO、CO2氣體濃度分布也可以反映混合燃料的著火過程,如圖9~11所示。測量誤差較小,經分析得3種氣體濃度相對測量誤差均小于2%。Z=180 mm處,O2濃度在中心處最高,然后濃度從r=0逐漸減小到r=±60 mm,這是由燃燒器噴口導致,火焰區域由噴口處擴大,火焰鋒面上O2濃度最低,表明點火最初發生在射流的外圍部分。Z=340 mm處,O2濃度在r=0~60 mm下降最快,形成一個低谷,這表明點火區域主要位于射流中心以外,在該部分反應仍然較弱,點火不穩定;且濃側O2濃度相對淡側更低,濃側混合射流燃燒更加劇烈,這與徑向溫度的結論一致。此時CO濃度依舊很低,這是因為混合燃料噴入爐內后,吸收熱量溫度不斷升高,揮發分不斷釋放,著火燃燒消耗O2并產生較多CO2,燃燒前期O2充足,故基本不生成CO。

圖9 不同揮發分含量煤種混合射流Z=180~820 mm處的O2濃度分布

圖10 不同揮發分煤種混合射流Z=180~820 mm處的CO濃度分布

圖11 不同揮發分煤種混合射流Z=180~820 mm處的CO2濃度分布
Z=500 mm處,O2濃度谷值與CO濃度峰值均偏向r=+40 mm處,且隨著混合燃料揮發分降低,O2濃度增加,CO和CO2濃度減少,即燃燒強度隨之減弱。還可以發現在r=0~80 mm O2濃度小于4%,CO濃度超過1%,CO2濃度超過16%,這是由于軸向距離340 mm后處于焦炭燃燒階段,中軸線上O2濃度大幅降低,缺氧氣氛中焦炭燃燒生成了大量CO,表明燃料已被徹底點燃并穩定燃燒。Z=660 mm處,對于HM+SC混合射流,r=40 mm附近O2濃度接近0,且r=-20和+100 mm時,O2濃度依舊小于4%,表明混合射流的燃燒更加穩定,反應區繼續擴大,這充分發揮了半焦摻燒高揮發分易燃煤種的優勢;所有混合射流在此截面濃側CO濃度最高,取YM+SC混合射流,可以發現CO峰值濃度在Z=660 mm處為3.68%,Z=820 mm處為3.28%,CO峰值濃度下降,這是由于缺氧還原性氣氛下CO大量還原已生成NOx,研究表明,在高溫缺氧環境中存在的CO是重要的NOx還原物質[21]。相比Z=660 mm處,Z=820 mm處所有射流的O2濃度均發生少許變化,表明混合燃料均處于穩定燃燒階段且反應在濃側還原氣氛中進行,有利于大量還原NOx。
2.2 不同揮發分含量煤種對NOx排放的影響
氮有多種氧化物,包括N2O、NO、NO2、N2O3、N2O4和N2O5等。燃燒過程中生成的NOx幾乎全是NO和NO2。天然氣、重油、煤炭等天然礦物燃料燃燒生成的NOx中NO占90%以上,其余為NO2。燃料燃燒過程中NOx的生成一般有熱力型、快速型和燃料型3種類型。快速型NOx是煤燃燒時空氣中的氮和燃料中的碳氫離子團(如CH等)反應生成的NOx,一般情況下,對不含氮的碳氫燃料在較低溫度燃燒時,需重點考慮快速型NOx的生成,對大型煤燃燒設備,快速型NOx占比很小,通常忽略不計。熱力型NOx基本上是在燃料燃盡后的高溫區N2和O2反應產生,影響熱力型NOx的主要因素有溫度、過量空氣系數和煙氣停留時間:熱力型NOx在溫度低于1 350 ℃ 時生成量很少,在溫度高于1 500 ℃時生成量較顯著[22];在過量空氣系數稍大于1的條件下,其大量生成;熱力型NOx隨煙氣在高溫區停留時間的延長而增加。試驗中,溫度控制在1 350 ℃以下且溫度場分布比較均勻(圖5、8),避免了局部高溫區的存在;試驗中的配風控制削弱了適宜熱力型NOx生成的過量空氣系數條件(表4),熱力型NOx生成占比較小,可認為本試驗中產生NOx主要是由燃料中N元素轉化成的燃料型NOx。
主燃區距噴口不同軸向距離處NOx徑向分布如圖12所示。可知測量誤差較小,經分析測得NOx濃度相對誤差小于2%。Z=180 mm處,NOx濃度很低,Z=340 mm處從軸向中心外圍逐漸增加,且峰值偏向r=20 mm處,濃側NOx濃度高于淡側。所有混合射流的NOx濃度均在Z=500 mm處達到峰值,表明該截面的燃料燃燒最為強烈,且Z>500 mm時,混合射流NOx較之前部分減少,這是因為此時氧濃度低,還原性氣氛和焦炭存在下NOx被大量還原,NOx濃度下降。Z=660 mm處,徑向NOx濃度峰值偏向r=-20 mm處,對比徑向溫度發現此處為實際射流中心,故認為濃側NOx濃度較淡側更高。Z=820 mm時,混合燃料的煙氣成分穩定,可將其作為主燃區出口,在此截面處,HM+SC、YM+SC、LRA+SC混合射流中心的NOx濃度分別為473、462、532 mg/m3(6% O2下,下同),可以發現YM+SC射流主燃區出口中心NOx排放最少,且對于HM+SC、YM+SC混合射流NOx濃度差值較小;摻燒低階煤種時隨著混合燃料揮發分增加,NOx濃度降低。試驗范圍內推薦適合混合燃料的Vdaf不低于16%,考慮到近幾年我國優質燃煤市場日益緊張,發電成本不斷增加,認為熱解半焦摻燒高揮發分易燃低階煤(摻混比50%)即可。

圖12 不同揮發分煤種混合射流Z=180~820 mm處的NOx濃度分布
3 結 論
1)隨著混合燃料揮發分含量減少,著火性能變差,混合射流濃側的著火距離從134 mm增至202 mm,著火點溫度從946 ℃升高至976 ℃,淡側著火距離較濃側更大,但增幅較小。
2)燃燒器出口與穩定燃燒區的距離隨混合燃料揮發分含量的減少而增加,但對于YM+SC混合射流延遲效果不明顯,且后續燃燒更為強烈。
3)YM+SC混合射流主燃區出口中心的NOx排放最少,但對于HM+SC與YM+SC混合射流,差值僅為11 mg/m3,LRA+SC混合射流NOx排放水平最高達到532 mg/m3;摻燒低階煤時隨著混合燃料揮發分增加,NOx濃度降低。推薦適合混合燃料燃燒的Vdaf不低于16%,考慮到我國對優質煤炭需求與煤炭儲量之間的矛盾,采用熱解半焦大比例摻燒高揮發分低階煤種(摻混比1∶1)的方式完全可行,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發電成本,緩解燃煤市場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