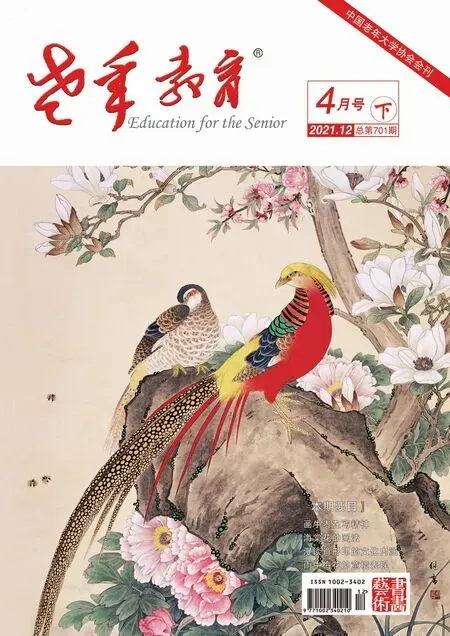“工”的無限
□ 徐惠泉

工筆畫之稱雖流行于西學東漸的清末民初,自身卻是從中國繪畫體系里化育衍生出的傳統品類。工筆人物畫也一直承襲以線立形、隨類賦彩的古典表現手段。但曾經“細畫”“工畫”的稱謂,都旨在表述“繪制工細”的局部概念,其中所蘊含的理性創造力往往不被重視。唐宋“水墨之變”后工筆畫與水墨畫并峙,最后水墨后來居上,在以筆墨韻致為中心的評判系統中,“工筆”因致力于繪畫性的建構而被長期置于“寫意”的對立面。
20世紀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革,源遠流長的士人文化隨之瓦解,作為中國畫水墨精神代表的文人畫也日漸式微。現代教育背景下美術專科學校的興起,重建了基于理性自覺之上的新學院傳統,呈現出主動的藝術改造訴求。蔣兆和、徐悲鴻、潘天壽等人倡導的教學體系,通過在工筆畫的線描造型中引入西畫的科學寫實,強化寫生與速寫訓練,有力改善了中國畫古典技法無法塑造現實人物的難題。“新年畫運動”所提倡的工筆畫與年畫的結合,也讓許多工筆重彩畫家積極投入,通過對現實生活、歷史事件以及英雄人物工謹細致的刻畫,悄然完成了現代性意義上的突進,奠定了工筆人物畫作為現實主義中國畫主力軍的地位。
在入選全國美展的中國畫作品中,工筆人物畫長期占據著半壁江山。改革開放后,當代工筆畫和水墨畫同時興起,也都傾向于獨立個性和自由觀念的表達。相比水墨畫在這一階段熱鬧非凡的實驗性創舉,工筆畫則步法堅實,投射出“以現代意識召喚中國藝術傳統創造精神復蘇”的平和心態。

《紅襖》 徐惠泉
當我們熱烈探討工筆畫何以成為今日中國主題性美術創作的重要組成之余,也必須冷靜直面它在數字圖像的高速生產與傳播中滋生出的不良傾向。面對西方色彩體系的嫁接和當代繪畫求新求變觀念的語境,怎樣重新認識民族文化技藝的獨立特性,是當今工筆人物畫發展進程中必須克服的難題。
在現代工筆畫蓬勃發展的當下,“寫意精神”早已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課題。然而最近幾年在各大中國畫展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極為工整富麗的人物肖像、群像,但也僅限于對“細”“密”的追求。大量概念化、同質化的少數民族題材、農民題材、城市女青年題材充斥其中,寫實主義的精工細作不過是“畫皮”,內里空洞膚淺的人物精神將作者寫意基本功的貧弱暴露無遺。
得益于市場經濟與信息傳播的大繁榮,當代工筆人物畫的形式語言已不局限于“三礬九染”“十八描”的傳統筆繪制作,而是衍生出勾勒、涂染、拓印、噴灑、貼箔、打磨、堆積、厚涂、拼貼等多種手法。這一彰顯生機與活力的多元創新局面固然令人欣喜,可表層語言一旦無法無度地擴張,象外之象、形外之形的表達就必然遭到忽視。這種只顧追求工具和材料的搭配變化得來的花樣翻新,已形成“為制作而制作”的不利局面,不但作品本身在視覺傳達上很難和諧統一,作為工筆畫家本應具備的筆墨與渲染功夫也日漸衰退。
顯而易見,工筆人物畫在當代的嬗變是多元化的,但繁榮與多樣并不一定意味著成熟。從當代創作生態中暴露出的問題,皆可總結為一句話:“寫形不難,寫心唯難。”中國繪畫在千百年的歷史演變中,有一個亙古不變的主題,即對人文本質的渴求。當代工筆人物畫要超越歷史、超越現狀、超越唯美主義,就必須賦予作品以精神深度。如果失去了內在精神的支配,無論技法如何高妙,畫面形象也只是近似標本的存在,無法與觀者達成心靈上的對話。
在歷經東方、西方、傳統、現代多重碰撞的百年之后,工筆畫所蘊含的精細不茍的審物精神和借物抒情的微茫詩意,逐漸固化為一種恒久的視覺經驗。而廣袤的當代生活圖景,又引發了對視覺新質的持續探求,旨在應對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社會變化所帶來的時代命題。“工”的“無限”,也是“意”的“無限”,是求索精神與創造張力的“無限”。只有找到古今和東西方人文精神的一致性,為時代塑造出具有個體生命價值的鮮活形象,方為中國工筆人物畫當代發展的突破路徑。

《獨坐黃昏后》何家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