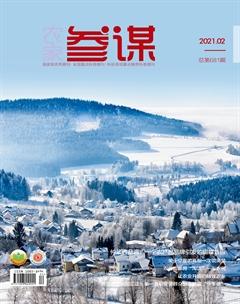喝一碗臘八粥——過年啦
肖于
我家插蠟梅的罐子是個粥罐。前年臘八節(jié)的傍晚,有朋友快遞了臘八粥給我,盛器就是這個罐子。當時,我驚訝于臘八粥的瓷罐太奢華,沒想到后來派了插花的用場。其實,蠟梅和臘八粥本來就是有交集的。蠟梅暄香遠溢,臘八粥溫暖豐足,都是肅殺冬季里的甜和暖,都是辭舊迎新的喜和光。
《禮記》中把冬季的祭祀稱為“臘祭”。漸漸地,臘祭的農歷十二月被稱為“臘月”,這個月份開的花是“臘梅”,腌的魚肉是“臘魚”“臘肉”,下的雪是“臘雪”,初八這天煮的粥是“臘八粥”。
在江南,農歷十二月正是蠟梅花開、臘肉晾起來的時節(jié),這個光景可能會遇到雪,也可能沒有雪,不管雪會不會飄飄灑灑落下來,一碗溫暖的臘八粥總會如期到來。
在杭州,男女老少都很愛臘八粥,這碗粥承載了美好的祝愿和安慰,親友們會相互贈送。靈隱寺、永福寺、香積寺、財神廟、胡慶余堂、張同泰、方回春堂……各大寺廟、老字號藥房都會施粥,撫慰大家疲憊一年的身心。臘八節(jié),施粥的人是心懷善意的祝愿,領粥的人則是納福和感恩。隆冬的杭州,凌晨四五點,很多杭州人走上街頭陸續(xù)排隊。趕到天光漸漸亮起,百米長隊也形成了,這哪里是為了吃碗粥,這是一份莊重甜蜜的儀式。盡管今年根據疫情防控要求,改變了往年集中發(fā)放的方式,而是由專人派送將罐裝的臘八粥送到轄區(qū)敬老院、志愿服務站以及個別居民的家中。但不變的是,在肅殺的冬日,因為有了這碗臘八粥的點撥,也變得甜美又生動。
南宋周密在《武林舊事》中記載了當時制作臘八粥的原料:“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類做粥,謂之臘八粥。”而現在各地臘八粥的用料不同,杭州流行的口味是軟糯香甜的甜味。花生、紅赤豆、蓮子、桂圓、紅棗、蜜棗、蕓豆、白果,加上糯米、糖桂花和白砂糖是靈隱寺的經典配方;常見的米、豆之外,加了人參、陳皮、枸杞、薏苡仁、枸杞的滋補款,則是胡慶余堂的偏好,講究個藥食同源。寺廟的寓意是積福,藥房的則重在溫補。
江南也有咸口的臘八粥,比如蘇州、揚州、常州等地,會以大米、黃豆、青菜、芋艿、花生仁、豆腐干、油豆腐和著稻米煮成,想來又是另一種風味。蘇州人的鮮咸臘八粥,要用大米、山藥、栗子、銀杏、香菇、胡蘿卜、青豆、開洋、火腿、姜絲,佐以料酒、鹽、胡椒粉熬煮,只看材料也讓人口水直流。
不論甜咸,臘八粥總歸是富足圓滿。老底子里煮粥也很講究,一般要臘月初七夜里開始做,各色米洗凈、泡紅棗桂圓,樣樣耐心處理,夜里用微火燉上粥,直到第二天早晨。現在的人雖然沒這么講究,但煮臘八粥終究要花點時間,從泡發(fā)到熬煮,慢火細燉中格外有儀式感。
為什么要吃臘八粥?版本不一。寺廟煮粥源于佛教始祖釋迦牟尼在臘八這天成道。佛教徒在這天供香燭,熬“佛粥”以供佛,還會散發(fā)給老百姓。臘八粥好味道,又有好意頭,吃了寺廟的臘八粥,讓人感覺會得到菩薩保佑,自然就廣受喜愛。說起來,胡慶余堂施粥的傳統(tǒng)已經有100多年了。清同治十三年,胡雪巖就在臘八節(jié)向杭州人奉粥祈福。不知道是不是從那時起,杭州人就有吃藥房臘八粥的習俗。
不只老百姓喜歡這碗臘八粥,出身貴胄的唐魯孫曾在文章中講過臘八粥,清朝宮廷不僅煮臘八粥,還會把粥分發(fā)給有功臣僚:“雍正藻飾增麗特地完制了一批白地青花的粥罐,賞給近臣內戚。嘉慶步武前朝,也做了一批五彩實花描金的粥罐賞人,后來被人發(fā)現這些兩朝特制的粥罐,如果用來養(yǎng)植矮枝芍藥,每天換水,要比一般古瓷的尊晷,可以耐久四五天之多。經人相互傳說,雍年、嘉慶時代窯燒的瓷罐,都成了古玩鋪的瑰寶啦。”
清朝皇帝賜粥,連粥罐也是格外定制的寶貝。至于盛粥為什么用罐子,不用碗,唐魯孫也做了解釋:“習俗流傳供佛祭祖的臘八粥,一律用粥罐上供,不用碗筷,雖然老媽媽論說不出所以然來,遙想當年佛祖未成道以前托缽乞食,自然是不用碗筷的,既然是追念圣哲,缽不易得,只好以罐來代替了。”
在他的記憶里,百多年前臘八粥供佛祭祖之后,也會讓家里小孩拿著臘八粥,在家中前庭后院、樹木花叢,都要澆上一勺臘八粥,也是祈愿春回大地、花木蔥翠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