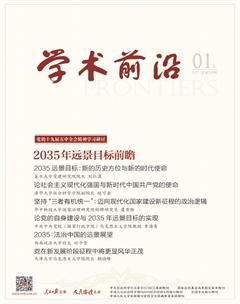17世紀~19世紀初英國海上商船保護政策調整
【摘要】由于島國的地理特點,英國從事海上貿易的歷史非常久遠,其海上商船保護問題亦可追溯至諾曼征服之前。19世紀初以前,英國海上商船的保護政策主要經歷了“結伴航行—商船自愿基礎上護航—強制性護航”的調整歷程,英國亦采取了一些其他輔助性保護措施。這一時期,隨著英國海外殖民地不斷擴張和對外貿易日益繁榮,海上貿易的暢通對英國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使得英國商船在海上航行時可能遭遇更多危險,除了成為海盜船等進行財富掠奪的目標外,其在局勢緊張抑或戰時也易成為敵對國家實施貿易攻擊戰的打擊對象,這令英國國家力量對該問題的介入越來越多。
【關鍵詞】英國? 海上貿易? 海上商船? 保護政策
【中圖分類號】K1?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1.014
由于島國的地理特點,英國從事海上貿易的歷史非常久遠,其海上商船的保護問題亦可追溯至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之前。英國海上商船保護政策的發展歷程可以概述如下:17世紀中期以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英國商船主要依靠結伴航行保護途中安全;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護航成為英國主要的海上貿易保護政策;19世紀中后期,隨著工業革命深入開展、蒸汽動力在船艦上的使用,種種新情況出現,使英國傳統護航政策的有效性飽受質疑,英國開始探討在蒸汽時代如何更有效地保護海上商船的安全,逐步放棄了護航政策[1],在20世紀初形成了以“爭奪制海權”為先決、以“沿戰時航線駐扎艦隊”為特點的保護政策[2];20世紀以后,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重拾護航政策。針對英國海上商船保護問題,國內學界對19世紀風帆時代邁入蒸汽時代以后的歷史時期關注較多,如探討“二戰”期間盟國商業護航問題的《護航大海戰》[3]《二戰大西洋破交/護航作戰經典系列》[4]等論著,筆者的文章《從護航到封鎖攻擊:19世紀后期英國海上商船保護政策再探討》[5]和《20世紀初英國對戰時海上貿易保護政策的探討》[6]等。然而,對19世紀初以前的相關政策尚未有長時段的系統探討。本文擬對19世紀初以前英國海上商船保護政策的調整歷程進行系統梳理,并探析推動其政策調整的原因。
17世紀中葉以前的古老慣例與結伴航行
早在諾曼征服之前,英國就已出現進行海上貿易的商船。那時英國海外貿易范圍非常有限,主要向歐洲大陸運送羊毛等貨物,從西歐的佛蘭德斯(Flanders)地區[7]運回紡織品,從法國西南部的加斯科涅(Gascony)和阿基坦(Aquitaine)的葡萄園運回酒等[8]。在此時期,對于貿易商船保護實行一個古老慣例,即在需要時,國王會號召沿海岸各城鎮提供船只和水手來護送貿易商船。例如,1204年由于菲利普·奧古斯塔斯(Philip Augustus)從英國國王約翰手中奪走了諾曼底,通過海峽的英國貿易不再像以往那么安全,英王便采取此慣例對商船進行保護。[9]除此慣例外,船東們會在自己的商船上采取一些增強船只防御性能的措施,并要求每一位水手配備護甲和武器,以便在需要時為船只安全進行戰斗。[10]
英王愛德華三世在位期間(1327~1377),行駛在海上的英國商船面臨非常嚴重的被劫掠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愛德華三世下令禁止英國商船單獨出海,要求其在海上必須多艘結伴航行。但這項命令并未被商船嚴格遵守,以致“越來越多的商船處于令國王和國家蒙羞的危險之中”。所以,1336年愛德華三世再次頒發條令,稱“為了他們(商船)自己的安全及維護國王和國家的榮譽”,出海商船先要在指定位置集合,從泰晤士河以西出發的商船的集合地為樸茨茅斯,從泰晤士河北部港口出發的商船的集合地為奧威爾,而后由國王派遣官員統一安排和檢查商船的武裝、食水供給等。之后,商船將以“大規模船隊的形式”往返;如果商船在途中擅自脫離船隊,其船長將會受到嚴重處罰。同時,英王愛德華三世還命令駐商船目的地的英國官員,當船隊到達后負責集結商船,以便其結伴回程。
此后直至17世紀初,結伴航行成為保護英國海上貿易商船安全的主要辦法。1576年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在位期間,因與西班牙的戰爭導致的海上危險,英王頒布“船只結伴航行條令”(Articles of Consortship),進一步強化官方對于結伴航行的規定,稱“為了更好地保護商船安全,抵制侵擾和劫掠,為了使海洋在混亂和戰爭危險中仍能保持秩序,同一船隊中的船只和人員,必須結伴航行、互相保護、集體合作,不能擅自離開,直至抵達目的地”[11]。這一時期結伴航行的基本情形為:商船對本船進行武裝,而后結伴出航,并從商船船長中推舉出臨時指揮官[12]統領整個船隊。此外,需要時船隊也可出資雇傭額外的護送船只,這種情況在14世紀時較為常見。
在商船結伴航行中,英國官方擔當起管理者和監督者的角色,在確保船隊安全、有序航行上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作為如下。
第一,英國官方為結伴航行制定出種種細則。例如,官方規定,參與結伴航行的每艘商船都要根據其水手人數裝備槍支等武器;如遇危險,商船必須并肩作戰,如有商船臨陣脫逃,船隊返程后,其船長將受到懲罰。[13]此外,官方還規定,從英國本土出發的商船先要在官方指定地點集結。例如,在伊麗莎白時期,來自倫敦、伊普斯威奇(Ipswich)和哈里奇(Harwich)的商船集合地點是泰晤士河口。之后,商船根據目的地各自組成船隊,并選舉出臨時指揮官。而后,船隊中的所有人,包括所有船長、商人、水手等,要在官員面前發誓[14],保證在航程中會行為良好、聽從臨時指揮官的號令等。最后,他們將結伴起航直至到達目的地。若在本土以外,當商船完成交易后要繼續航行或返航時,需在指定地點等待商船集結到一定數量后,選舉出臨時指揮官并按照慣例進行宣誓,而后結伴出航。例如,在伊麗莎白時期,從安達盧西亞(Andalusia)、巴約訥(Bayonne)等地等待返航的船只先要在加的斯灣(the Bay of Cadiz)集合。直布羅陀(Gibraltar)及其附近港口的船只則在直布羅陀的錨地集合。若集結船只數量不少于8艘,就可推舉出一位船長擔任最高指揮官,并發誓在到達目的地之前,除非是不可抗拒的天氣原因,否則他們將不會破壞結伴航行,而后便可結伴出航。若船只數量不足8艘,按照官方規定,必須繼續等待其他船只的到來。[15]
第二,英國官員為商船出航前的宣誓行為擔任見證人。如前所述,在商船船隊出航前,參與航行的所有人員,都要在政府官員面前為自己在即將開始的航程中的行為宣誓。例如,1542年,一支船隊前往西班牙之前,商船船長們在海軍部官員面前宣誓。來自倫敦的“幸運瑪麗”號商船船長托馬斯·林奇(Thomas Lynche)發誓他的船只將跟隨克里斯托弗·貝內特(Christopher Bennett,這只船隊的臨時指揮官)直至到達目的地,并保證當他完成在西班牙港口的交易后,仍將結伴“向前航行或者返回”。“瑪麗·凱瑟琳”號商船船長則發誓道:他將不會對臨時指揮官進行任何欺騙,除非指揮官有令,否則他不會擅自改變航線,也不會擅自停靠任何港口,并保證將用他所有的“力量、知識和經驗”,向指揮官和所有“結伴航行的英國船只”提供幫助,并保證將命令他的手下們同樣服從。[16]
第三,英國官員為商船結伴航行時發生的糾紛擔當裁決者。如在航行途中遇到危險,誓言的約束力其實極其有限,當因違反誓約引起糾紛時,官方便會擔當起裁決者角色。例如,1416年,有一支從波爾多返航的運酒船隊,在回國途中,其臨時指揮官約翰·夏普(John Sharpe)的“克里斯多夫”號商船遭到幾艘法國武裝船只攻擊,按照誓約同行其他商船應提供援助、共同作戰,但事實上其他船只棄他而逃,最后“克里斯多夫”號被俘獲,船上裝載的240桶酒也成為對方的戰利品。事后,“克里斯多夫”號商船船主向議會遞交了一份申述書,聲稱船只的損失對他們來講是“毀滅性的災難”,也是“國家的恥辱”,同行的其他商船應對他的損失負責。之后,下議院將申述書呈遞給國王亨利五世,國王下令傳喚所有在場者,并在幾位法官陪同下一起聽取證詞,最后作出如下裁決:與“克里斯多夫”號同行的其他商人和船長要負責賠償“克里斯多夫”號的損失,并被處以監禁。
結伴航行在保護貿易商船安全方面的作用很難被具體量化,但正如英國歷史學家歐文·拉特(Owen Rutter)所評論的:“至少,商船結伴航行要比單獨航行安全得多。”[17]
17世紀中葉以前,除結伴航行外,英國還曾對海上的劫掠船采取主動打擊措施,以降低商船航行時的危險。例如,亨利五世逝世后,劫掠船對英國商船的掠奪活動一度非常猖獗。這些劫掠船并非完全來自國外,有相當一部分是英國本國的“冒險者”,他們同本地貴族勾結,分享劫掠的戰利品。到15世紀后期,這種情況不斷惡化,一位大臣向國王這樣描述:“許多海盜船、私掠船、被流放者和歹徒罪犯們的船只,裝扮成軍艦模樣,每日在海上忙于襲擊、劫掠、損壞我們忠誠臣民們的船只,成為制造恐怖的事物,我們國王的尊嚴被蔑視,這是難以忍受的恥辱,它傷害了我們的臣民以及向我們求助的其他商人。”[18]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打擊劫掠船的猖獗活動,英王采取了兩項措施。其一,限制本國商船從事海盜活動。1484年,英王理查德三世向各海港發布了一項公告,要求商船船長先要簽訂契約,保證自己的船只在海上會“行為良好”,并且繳納一定的保證金,才能夠被放行。這項條令長期有效。[19]其二,派遣船隊主動清理海上的私掠船。例如,1511年英王就曾命令大臣約翰·霍普森(John Hopton)率領一支船隊去清理海上的私掠船。[20]
但需要認識到,17世紀中葉之前的絕大多數時間內,英國商船的海上安全還是依靠船隊協作和自身武裝,官方力量尤其是軍事力量的介入非常有限。究其主要原因,應是此時英國經濟基本自給自足,海上貿易于英國而言只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因此,英王認為他只需在必要時刻給出幫助即可。
17世紀中期~18世紀后期商船自愿基礎上的護航
從17世紀中葉開始,英國官方開始在需要時向商船提供軍艦護航,以加大對海上商船的保護力度。英國采取這一舉措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隨著英國殖民勢力擴張和海外貿易范圍延伸,海上貿易給英國帶來豐厚利潤,成為英國財政收入和國內原始資本積累的重要資金來源。大約從16世紀后期開始,隨著國內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對重商政策的普遍尊崇,英國積極致力于拓展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貿易。伊麗莎白一世(1558~1603)的重臣雷利曾對當時海上貿易的重要性作出評價:“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貿易,而誰控制了世界貿易,誰就控制了地球的財富和地球本身。”[22]到17世紀中期,英國的貿易觸角已經逐漸深入到世界各地,與俄國、東印度、非洲西北部和西部地區、美洲殖民地等國家和地區都有貿易往來,并通過俄羅斯公司、東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等特許貿易公司進行壟斷性貿易。這給英國國家帶來了豐厚收益。據英國經濟學家查爾斯·達維南特(1656~1714)估算,英國國家財富在1600年是1700萬鎊,在1630年是2800萬鎊,1660年已增至5600萬鎊,到1688年則高達8800萬鎊,而且對外貿易是該時期英國財富增值的最主要來源。他還指出,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1640~1688),雖然英國國內經濟狀況不佳,但國家財富總額仍實現了年均增值200萬鎊,其中約90萬鎊來自英國與其殖民地之間的貿易收益,約60萬鎊來自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收益,約50萬鎊來自英國與歐洲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收益。[21]國家財富的積累,為日后英國向工業強國發展提供了重要資本保障。
第二,新型劫掠船的出現,對結伴航行的有效性提出嚴峻挑戰,使英國海上商船的安全面臨嚴重威脅,這種情形迫切要求英國增強對其海上商船的保護力度。17世紀之前,由于造船水平低下、造船技術發展緩慢,船只間的性能差別并不明顯,劫掠船也只是裝備上武器的商船,因此,結伴航行的商船船隊憑借自身武裝便能對付劫掠船。但是,在伊麗莎白一世(1558~1603)統治末期,佛蘭德斯的一些港口開始建造一種被稱為“敦刻爾克船”(Dunkirkers)的新型船只,它專為劫掠商船設計制造,裝備更強大的武器、速度更快、動作更靈活,普通商船既難以與之抗衡,也難以從它的追擊中逃脫。這些“敦刻爾克船”出現后,在英吉利海峽和北海海域對英國商船造成嚴重威脅,商船船東們為此曾多次請求英王提供軍艦護航。
第三,英國海軍將領的提議。17世紀初期,英荷關系日趨緊張,戰爭危險加劇,英國海軍將領在探討戰時海軍戰略時曾提出護航建議。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英國海軍將領威廉·蒙森(William Monson),他在《英荷戰爭爆發后英國作戰的前景》中提出,在戰爭中,英國應對運煤船進行護航。文章說道,如果英荷戰爭爆發,為了確保運煤船安全抵達英國,必須要采取以下措施:建造運煤船時在甲板上留下足夠空間,以安放艦炮等軍備設施;運煤船要結伴出航;要派遣訓練有素的軍艦護航;運煤船應緊靠海岸航行,如受到攻擊,應駛向港口,以獲得來自海岸的幫助。[23]
第四,英國海軍實力的發展,令英國官方具備了向商船提供護航的力量。由于戰爭和海外擴張的需要,亨利八世(1509~1547)和伊麗莎白一世(1558~1603)都對海軍建設給予很高的重視,英國海軍在軍艦數量、武器軍備、適航性、行政管理、水手素質及戰術等方面得到長足的進步,并在1588年擊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17世紀,英國軍艦的建造技術得到進一步發展,建造出更大噸位、能夠裝載更多士兵和武器的軍艦,而且新型軍艦所載艦炮的攻擊力得到較大提高,能夠打碎敵方船只的船殼。[24]英國海軍實力的發展,使英國官方具備了向商船提供護航的可能性。在諸多因素的推動下,1652年英國開始向商船提供軍艦護航。其具體情形如下:17世紀中葉英國內戰結束后,1649~1653年,英國經歷了一個短暫的共和國時期。1652年,由于北非海域海盜船活動猖獗,英國海上貿易遭受嚴重損失,英國政府決定撥款194,000英鎊,派遣一些軍艦在阿爾及利亞附近海域巡航,并向往返于英國和黎凡特地區(Levant)之間的商船船隊提供軍艦護航。[25]這項措施標志著英國海上商船保護政策的一個重要變化,即英國官方軍事力量開始正式介入對海上貿易的保護。之后直至19世紀前期,護航一直都是英國最為主要的海上貿易保護政策。
17世紀中期至18世紀后期,英國護航政策的基本特點概括如下:在戰爭時期,國家一般會主動向商船提供護航;在和平時期,通常為商船在需要時向官方提出申請,官方視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提供護航;為加強護航旅程的安全性,起航之前,負責執行護航任務的海軍將領要將本次航程的信號、暗語等內容形成護航秘密條令,發放到每一位商船船長手中[26];在護航官兵履行職責方面,官方有較為嚴格的紀律,但商船一方是否愿意聽從將領指揮,是否愿意跟隨護航編隊,基本上靠其自覺性,如其違反海軍將領的命令,也不會對其進行處罰[27]。概言之,這一階段護航最顯著的特點是:護航對商船來講并非強制性的,如果商船船長不愿聽從護航將領的指揮、不愿跟隨護航編隊,他們將“自己承擔被劫掠的風險”,但不會因此受到任何懲罰。[28]
18世紀后期~19世紀初強制性護航
強制性護航政策出現,主要因為日益加劇的戰爭危險和法國等國對英國進行的貿易攻擊戰[29]。由于海軍實力相對薄弱,早在18世紀初期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期間,法國就已開始偏重對英國進行貿易攻擊戰。在這場戰爭中,法王積極鼓勵私掠船行動,船東在繳納6000英鎊后,便可獲得“合法掠奪”的授權書。法王將大量主力艦閑置,促使大批海軍官兵轉到私掠船上服務,他還將一些小型軍艦出租給個人或公司從事私掠行動,甚至他本人也和許多大臣一樣向這項事業里投資了大量資金。[30]在官方的積極鼓勵和參與下,“法國私掠船數量的增長快得就像一陣風”,而且已經具備相當的組織性。英國歷史學家歐文·拉特曾將這時期的法國私掠船稱為“一種海軍民兵部隊”,“法國私掠船經常3、4艘或者6艘船組成一支船隊,在經驗豐富的海軍人員的帶領下,在海上巡航;他們主要從瀕臨英吉利海峽的港口特別是敦刻爾克和圣馬洛出海,裝載著優良的武器裝備,搶劫遇到的商船;為了迷惑獵物,他們航行時經常懸掛其他國家的旗幟,使其經常能夠順利接近獵物而不會引起對方警覺,而后發起突然攻擊。一些私掠船負責對付護航軍艦,另一些私掠船則負責劫掠戰利品”。[31]
這一時期,面對法國發動的瘋狂的貿易攻擊戰,英、荷兩國在海上航行的商船幾乎沒有一艘是安全的,英國穿越地中海的貿易航路被切斷,往來于英國與東西印度之間的船隊持續遭到攻擊,英國的海上貿易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損失。
在18世紀末開始的英法戰爭中,法國的貿易攻擊戰進一步升級。1793年2月,法國對英國及荷蘭宣戰,一個月后對西班牙宣戰。交戰雙方的海軍力量對比如下:英國135艘軍艦,荷蘭49艘,西班牙76艘,總計260艘,而法國只有80艘。所以,戰爭開始時,英國就曾推斷,由于法國海軍力量薄弱,法國將會重啟貿易攻擊戰。事實證明,英國的預測是正確的,戰爭開始后不久,“法國的私掠船便擠滿了海峽”。而且,不僅是英國商船,運載英國商品的中立國船只也成為法國私掠船劫掠的目標。
1794年,法國督政府上臺執政,認為以法國的海軍實力,不可能在艦隊戰斗中取得勝利并控制海洋,所以法國海上戰略的重心應傾向于摧毀英國的海上貿易。用當時英國一位議員的話說:“它(法國)的政策是放棄艦隊戰斗而去進行貿易攻擊,……其目的是導致英國陷入破產的丟臉境地。”之后,法國除了繼續加強私掠船的行動,還派遣小型海軍艦隊攻擊護航力量較為薄弱的船隊。例如,1795年9月,9艘法國軍艦在直布羅陀以西150英里處,攻擊了一支從黎凡特返航回國的英國護航編隊,該編隊有31艘商船,被3艘軍艦護送。法國軍艦俘獲了所有的商船和1艘英國軍艦。
此外,督政府還將目標指向運載英國商品的中立國船只。其通過一項法律,禁止英國商品進入法國和法國占領的地區,并為此關閉了比利時、荷蘭、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港口。但是,各國對英國商品的需求之大,致使仍有船只冒險去運載英國商品,其中有許多是中立國船只;他們將英國商品帶到歐洲大陸的各個港口,而后,其中一部分將被直接或間接帶到法國。督政府進而聲明:在海上發現的每一艘載有英國貨物的船只,都將被視為“合法的戰利品”,無論英國貨物占其貨物總量的比重是多少,也無論這艘船的國籍歸屬。也就是說,哪怕法國在一艘中立國船只上只發現了一件英國生產的襯衫,這艘船上的全部貨物和船只本身,都可以被“合法”沒收。在官方鼓勵下,法國在海上的劫掠行動變得更加肆意。[32]
在此情況下,英國政府認為,應該對商船實施強制性護航,以減少因商船獨立航行而造成的損失。正如英國名將納爾遜所言:“所有商船,無論是快的還是慢的,大的還是小的,都應該一直在護航下航行。”[33]
1804年12月,西班牙參戰對抗英國,進一步增加了英國海上商船的危險。而且,在特拉法加海戰(Battle of Trafalgar)中,英國徹底摧毀了法國和西班牙的海軍,也粉碎了拿破侖從海上侵略英國本土的夢想,拿破侖決定“更加兇殘地攻擊英國的財富來源(指海上貿易)”。[34]之后一段時期內,對英國商船來說,英法周邊幾乎沒有安全海域。其中,北海和英吉利海峽是最為危險的海域。在這里航行的英國商船將面臨來自布洛涅(Boulogne)、加來(Calais)和敦刻爾克的私掠船的威脅。在1794年和1795年法國占領歐洲西北部沿岸低地國家[35]的港口之后,這種危險更甚。英國南部的大西洋海域是往返于英國本土與東西印度之間英國商船的必經之地,因為在這一海域英國駐扎有海軍并經常派軍艦巡查,所以,從法國瀕臨大西洋諸港口駛出的私掠船噸位更大,適航性更強,裝備的武器軍械更優良、在海上停留的時間更長。“波爾多”號是這些法國私掠船中成績斐然的一艘,它擁有220名船員,軍備先進,雖然它在1799年被捕獲,但在此之前,它已捕獲了160艘英國商船,為其投資人贏得了價值超過100萬銀幣的收益。[36]在加勒比海域,私掠船擁有一些得天獨厚的條件——平靜的海洋、規律的季風和難以攻陷的基地,如馬提尼克島(Martinique)、瓜德羅普(Guadeloupe)等島嶼。加之,在戰爭期間,英國對途經此海域的商船提供的護航力量更為薄弱,除了運糖船隊等定期往返的貿易船隊外,一些更小型的零散貿易商船有時甚至在無保護的情況下航行。
面對這一時期法國對英國海上貿易前所未有的瘋狂攻擊,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頒布了一系列法案條令,建立起強制性的護航體系[37]。與之前商船自愿基礎上的護航政策相比,強制性護航體系下的商船在享受軍艦保護的同時,還有服從護航將領命令、遵守護航相關規定的義務。強制性護航體系構建的具體進程如下:1792年,面對日益加劇的戰爭危險和法國對英國海上貿易進行瘋狂攻擊的可能性,英國頒布了一項法案以規范護航編隊航行途中商船的行為。自此,英國開始明確在護航中商船應承擔的義務。1798年,英國議會通過了“第一次護航法案”,首次立法規定了商船必須在軍艦護送下航行。這項法案標志著護航政策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即以往在商船自愿基礎上的護航轉變為強制性護航。1803年英法戰爭爆發,英國政府頒布了“第二次護航法案”,進一步豐富了“第一次護航法案”的內容。之后,為應對法國私掠船的激烈攻勢,英國海軍部出臺了一系列關于“皇家海軍海上服役”的法令。這些法令從法律制度層面規范了護航官兵、商船船長及船東的行為,為英國護航體系奠定了法律基礎,其中一些條款在之后長期有效。[38]
概言之,從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前期,護航是英國最為主要的海上貿易保護政策。這一時期,除護航外,英國還采取了一些其他保護措施,主要有兩項:第一,派遣軍艦在某一海域巡航。當然,保護途經該海域商船的安全往往只是巡航軍艦的任務之一,甚至只是其一個次要任務。這一時期,英國巡航軍艦的常規任務更多是攻擊敵國的貿易商船、封鎖或攻擊敵國的艦隊等。例如,在第一次英荷戰爭期間,英國曾派遣艦隊在英吉利海峽和西部通道海域[39]巡航,其任務是保護途經本海域的英國商船和攻擊荷蘭的貿易商船。第二,對劫掠船進行威嚇或剿滅。當劫掠船的活動特別猖獗時,英國還會直接威嚇或剿滅私掠船。例如,1677年,為了威嚇來自奧斯坦德(Ostend)的劫掠船,英國海軍在奧斯坦德周邊海域進行了一次示威性的海軍演習,以“說服他們賠償在非法掠奪行動中對英王臣民所造成的損失”。四個月后,由于“那個地方的人們對英王已經變得更加尊敬”,英國海軍撤回,但一支艦隊仍奉命在奧斯坦德周邊海域巡航,以捕獲他們所遇到的任何私掠船。[40]
結語
綜上所述,19世紀初以前,英國海上商船的保護政策主要經歷了“結伴航行—商船自愿基礎上護航—強制性護航”的調整歷程,當然這一時期英國亦采取了一些其他輔助性保護措施。
英國是一個島國,對外貿易只能通過海洋進行。整體看來,這一時期隨著英國海外殖民地不斷擴張和對外貿易日益繁榮,海上貿易的暢通對于英國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使得英國商船在海上航行時可能會遭遇更多危險,他們除了是海盜船等進行財富掠奪的目標外,在局勢緊張時期或戰時也易成為敵對國家實施貿易攻擊戰的打擊對象。為了保護其海上商船安全,英國國家力量的介入越來越多,對海上商船實施有效保護也逐漸成為英國海軍的一項重要職責。進入19世紀后,在20年代希臘獨立戰爭之后至60年代,英國沒有再對海上貿易保護問題予以專門關注,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這一時期英國所處的國際局勢相對穩定,其海上貿易也處于相對安全的狀態,雖然在19世紀50年代英國卷入克里米亞戰爭,但在這場戰爭中,英國的海上貿易并未遭受嚴重攻擊和劫掠;第二,伴隨蒸汽動力在軍艦上的應用,英國朝野籠罩在“‘蒸汽橋噩夢”[41]之中,其戰略重心也因此放在對本土海岸的防御上。然而,進入19世紀70年代后,隨著英國海上貿易重要性的日漸提高、國際局勢的日趨緊張、工業革命的深入開展、蒸汽動力在船艦上的應用、造船技術等的不斷提高,種種新情況出現,英國當局開始重新對海上貿易保護政策展開積極探討,試圖尋找在蒸汽時代更有效的保護方式。[42]
(本文系2020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9世紀英國歐洲大陸政策的困境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0BSS050)
注釋
[1][5][42]杜平:《從護航到封鎖攻擊:19世紀后期英國海上商船保護政策再探討》,《社會科學研究》,2021年第1期。
[2][6]杜平:《20世紀初英國對戰時海上貿易保護政策的探討》,徐藍主編:《近現代國際關系史研究》(第十三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7年。
[3]王志強:《護航大海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程紀實系列叢書),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年。
[4]《二戰大西洋破交/護航作戰經典系列》是發表于2003年和2004年《國際展望》的一系列文章,具體包括:《二戰大西洋破交/護航作戰經典系列 名狼之夜 HX.72護航船隊之戰》《二戰大西洋破交/護航作戰經典系列 壯烈的22分鐘 “賈維斯灣”號輔助巡洋艦和HX.84護航船隊之戰》《二戰大西洋破交/護航作戰經典系列 冰海浩劫 PQ.17護航船隊的悲劇》《二戰大西洋破交/護航作戰經典系列 最后的防御性護航 ONS.154護航船隊之戰》《二戰大西洋破交/護航作戰經典系列 獵潛英豪 二戰英國著名護航指揮官沃克上校戰記》。
[7]佛蘭德斯(Flanders),是西歐的一個歷史地名,泛指古代尼德蘭南部地區,位于西歐低地西南部、北海沿岸,包括今比利時的東法蘭德斯省和西法蘭德斯省、法國的加來海峽省和北方省、荷蘭的澤蘭省。中世紀初期,毛紡織手工業在佛蘭德斯發展起來;11世紀它發展成歐洲最富有的地區,居民從英國進口羊毛,紡成面料賣給歐洲大陸;13至14世紀時它成為歐洲最發達的毛紡織中心之一。
[8][10][11][15][17][18][20][23][25][31][32][34][36][40] Owen Rutter, Red Ensign: A History of Convoy, London: R. Hale Ltd., 1943, pp. 10, 12, 24, 24-25, 16, 21, 19, 34-35, 38, 59, 94, 102, 104, 89, 42, 53, 55.
[9][33][37] John Winton, Convoy: The Defence of Sea Trade, 1890-1990, London: M. Joseph, 1983, pp.12, 14, 15-16.
[12]臨時指揮官的數量一般視船隊規模而定,大規模船隊一般設兩位臨時指揮官,英王分別授權其為第一指揮官和第二指揮官,小規模船隊一般選舉一位臨時指揮官。臨時指揮官從船隊商船收取一定費用作為酬金,開始時數額較高,在伊麗莎白時期已降至所護送貨物每桶收取1便士。Owen Rutter, Red Ensign: A History of Convoy, p. 24.
[13][16][19]Smith, H. A., The Law and Custom of the Sea, London: Stevens, 1959, pp. 205, 261, 152, 173.
[14]大約到16世紀前期,水手們不再被要求參與發誓,但他們必須對臨時指揮官和同行伙伴忠誠,這已成為當時約定俗成的慣例。
[21][英]查爾斯·達維南特:《論英國的公共收入與貿易》,朱泱、胡企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160、161、236~238頁。
[22]T. K. Rabb, Enterprise and Empire: Merchant and Gentry Investment in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575-1630,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5.
[24]Jon Tetsuro Sumida, In Defence of Naval Supremacy: Finance, Technology and British Naval Policy, 1889-1914,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 4.
[26]Henry Teonge, The Diary of Henry Teonge: Chaplain on Board H.M.'s Ships Assistance, Bristol, and Royal Oak, 1675-1679, London: G. Routledge, 1927, p. 27.
[27]A.T. Mahan, The Life of Nelson: The Embodiment of the Sea Power of Great Britain, New York, N.Y.: Haskell House Pub. Ltd., 1969, p. 32.
[28]此階段英國護航政策的具體情形,參見杜平:《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早期英國的商業護航》,《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6年第11期。
[29]貿易攻擊戰(英語Commerce Raiding,法語Guerre de Course)是一種重要的海軍戰爭形式,指在公海通過攻擊敵人的商業船運來摧毀或中斷敵方的后勤保障和物資供應,或從中獲得對增強己方作戰能力有利的東西。執行貿易攻擊任務的船只主要有三種類型:私掠船、武裝商船和軍艦。一般而言,貿易攻擊戰往往被一個海軍實力相對弱小的國家選擇,用來對抗一個海軍實力更強大的國家,或被一個擁有很少海上貿易的國家用來對付擁有大量海上貿易的國家。Arne Roksund, The Jeune ?cole: The Strategy of the Weak, Leiden; Boston: Brill, 2007, pp. 13-15; Norman Friedman, Seapower as Strategy: Navie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pp.48, 83-87; Donald W. Mitchell, A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Sea Power, London: A. Deutsch, 1974, p. 194.
[30]除了打擊英國的目的外,法王積極鼓勵私掠船的行為還由于他能從中獲得豐厚的收益,因為這時期私掠船戰利品的收益分配如下:10%交于國王,5%交于教會,其他投資人和參與者分享剩余部分。Owen Rutter, Red Ensign: A History of Convoy, p. 59.
[35]低地國家(the Low Countries),特指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因其海拔低而得名。這一地區于英國有著重要戰略意義,因為如果這一地區被入侵,英吉利海峽的安全將受到直接威脅。
[38]強制性護航體系的具體情況,參見杜平:《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早期英國的商業護航》,《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6年第11期。
[39]西部通道海域(Western Approaches),是指位于英國西海岸外的一個矩形海域(南北長,東西短),其南北邊界以英倫三島南北所轄的海域為界,東部邊界就是英國的西海岸,西部邊界大體接近冰島附近。英國的許多重要港口都位于這一海域,幾乎所有進出英國的貿易商船都要穿過這片海域,所以,西部通道海域一直都是英國戰略防御的重點區域。http://en.wikipedia.org/wiki/Western_Approaches,訪問日期:2012年5月1日。
[41]“蒸汽橋”噩夢(the "Steam Bridge" Nightmare),是指在維多利亞時代早期和中期,英國對法國蒸汽軍艦將穿越英吉利海峽侵入英國本土的擔憂。1849年,法國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以蒸汽機為主動力裝置的軍艦“拿破侖”號。英國開始思考,法國積極建造蒸汽軍艦在未來可能發生的英法戰爭中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以韋林頓和帕默斯頓為代表的英國官員認為,以蒸汽為動力的法國軍艦將不再受潮汐和季風限制,能夠在任何季節從任何方向到達英國本土的任一處海岸,包括以前從未被成功入侵過的地方,如海峽群島等。正如帕默斯頓所說:“英吉利海峽已不再是屏障,蒸汽軍艦已經在風帆時代軍隊難以跨越的海峽上架設了一座‘蒸汽橋。”在整個維多利亞時代的早期和中期,這種“蒸汽橋噩夢”一直籠罩著英國人,他們一直擔心一批法國蒸汽船將會載著一支陸軍在英國某處海岸登陸。因而,19世紀中期的一段時間,英國對陸軍建設和本土海岸防御給予了相當的重視。D.M. Schurman, Imperial Defence, 1868-1887, London;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0; C. J. Bartlett, Great Britain and Sea Power, 1815-185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p. 158.
責 編∕郭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