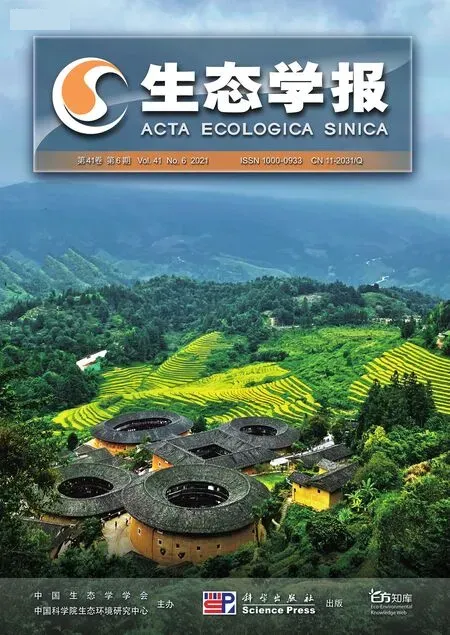騰格里沙漠東南緣固沙植被區生物土壤結皮及下層土壤有機碳礦化特征
謝 婷,李云飛,李小軍,*
1 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沙坡頭沙漠研究試驗站, 蘭州 730000 2 中國科學院大學, 北京 101408
植被恢復與重建是干旱沙區退化土地修復的有效途徑,是該區生物土壤結皮(Biological Soil Crusts,BSCs)發生與發展的關鍵影響因素[1- 2]。固沙植被建立后,沙丘表面逐漸趨于穩定,以藍藻為優勢的生物土壤結皮開始拓殖,爾后隨著植被恢復過程中生物和非生物環境的進一步改善,藻類結皮逐漸向著以荒漠藻類、地衣及蘚類等為優勢的生物結皮類型演變[3]。BSCs占干旱區地表活體覆蓋的40%—70%,是該區地表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土壤碳循環的主要參與者[4- 6]。已有研究表明,BSCs的年固碳量可達11.36—26.75g C/m2[7],而結皮呼吸釋放的碳占其固碳量61%[8]。在半干旱草地生態系統中,BSCs呼吸可達土壤呼吸總碳釋放量的43%,遠大于植被和裸地斑塊土壤呼吸的貢獻[9]。因此,BSCs的拓殖和發育在干旱區碳循環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土壤有機碳礦化是陸地生態系統到大氣碳通量最大的組成部分,對維持土壤肥力和養分釋放、緩解溫室氣體的增加及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至關重要[10- 11]。沙區固沙植被建立后,伴隨著植被的演變,BSCs的物種組成、蓋度、生物量、理化性質、微生物屬性及水熱因子等均發生了顯著的變化[7,9,12- 15]。BSCs的這種變化使其本身參與的生態水文過程發生顯著變化,進而可能影響其碳循環過程[5- 7,9,12]。因此,BSCs演變對碳礦化的影響逐漸受到關注。如楊雪芹[16]等研究發現,BSCs在由藻類為優勢到經藻類和蘚類混生向以蘚類為優勢的結皮演變過程中,其碳礦化速率由0.03 g kg-1d-1增加到0.04 g kg-1d-1,累積可礦化碳量的比例在4.7%—6.9%之間。李云飛等[17]通過對不同發育階段的BSCs研究發現,有機碳的瞬時及最大礦化速率均表現為蘚類結皮>地衣結皮>藻類結皮土壤。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側重于BSCs自然演替過程中碳礦化的變化,而對固沙植被演替引發的BSCs生物和非生物過程演變對土壤碳礦化的研究較缺乏,這使得我們對沙區人工植被建設對土壤碳庫動態變化及土壤質量的影響機理認識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對固沙植被的生態學效應的準確評價。
擬通過對騰格里沙漠東南緣不同恢復年限固沙植被區BSCs及其下層土壤碳礦化特征,及其與水分和土壤理化性質之間關系的研究,揭示固沙植被恢復過程中BSCs的拓殖和發育對土壤碳礦化過程的影響,闡明BSCs對荒漠生態系統碳循環的貢獻及關鍵影響因素,為全面認識干旱區BSCs的生態功能提供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實驗區位于騰格里沙漠東南緣,中國科學院沙坡頭沙漠研究試驗站包蘭鐵路以北的人工固沙植被區(37°32′N,105°02′E)。該區為荒漠化草原向草原化荒漠的過渡帶,也是沙漠和綠洲的過渡帶。平均海拔1339 m,年均氣溫為9.6℃,最低氣溫-24.5℃,最高氣溫38.1℃;年均降水量約為186 mm,且80%的降水集中在5—9月;年潛在蒸發量為3000 mm,年平均風速為2.8 m/s,最大風速19 m/s,大于5 m/s的起沙風每年有200 d左右。
為了確保包蘭鐵路沙坡頭沙漠地段的暢通無阻,科研人員于1956年開始在流動沙丘上設置1 m×1 m的麥草方格沙障并種植油蒿(Artemisiaordosica)、檸條錦雞兒(Caraganakorshinskii)和花棒(Hedysarumscoparium)等旱生灌木,爾后在不同年份按照相同方法進行擴展,在包蘭鐵路兩側形成了南北寬約700 m,長16 km非灌溉人工固沙植被防護林體系[2,18]。該區的主要草本植物有:小畫眉草(Eragrostisminor)、霧冰藜(Bassiadasyphylla)、刺沙蓬(Salsolaruthenica)、狗尾草(Setariaviridis)和茵陳蒿(Artemisiacapillaris)。人工固沙植被區建立后經過60多年的演變,植被—土壤系統發生了深刻的演變,BSCs也逐漸形成并發育,該區BSCs的主要優勢生物成分為藻類、地衣和蘚類[19]。不同恢復年限固沙植被區結皮層和下層土壤的理化性質見表1。
1.2 實驗設計
2019年5月,分別在1956年(63a,恢復年限)、1973年(46a,恢復年限)、1987年(32 a,恢復年限)和2011年(8 a,恢復年限)建立的人工固沙植被區和流沙區(0 a,恢復年限)設置10 m×10 m的樣方各3個。固沙植被區每個樣方中隨機選取10個采樣點,分別用直徑為5 cm的土鉆采集結皮層及結皮下0—5 cm層土壤樣品;流動沙丘采用同樣的方法采集表層0—2 cm土壤和下層2—7 cm土壤。同一樣方中同一土層不同采樣點樣品混合成一個樣品帶回實驗室,共30個混合樣。采集的土樣在室內自然風干,去除殘留的枯枝落葉后過2 mm篩。將風干土分為兩份,一份用于測定土壤理化性質,另一份置于4℃冰箱,用于有機碳礦化的測定。
1.3 測定指標及方法
土壤pH值用pH計法(水∶土=5∶1)測定,土壤電導率采用電導儀(Cole-Parmer Instrument Company, Illinois, USA)測定,土壤顆粒組成采用采用激光粒度儀(Microtrac S3500, Microtrac, Montgom-eryville, USA)測定,利用壓力膜儀(5bar壓力膜儀,1600和15bar壓力膜儀,1500F1,USA)測定水分特征曲線,并計算田間持水量。土壤全氮用FOSS凱氏定氮儀測定,土壤有機碳采用重鉻酸鉀氧化-外加熱法測定[20]。
土壤有機碳礦化采用室內恒溫培養-堿液吸收法測定。取出4℃條件下保存的樣品,分別稱取50 g置于250 mL的可密封廣口瓶中,把廣口瓶中土壤的水分用蒸餾水分別調節至土壤含水量的5%、10%和20%,再放入20℃的恒溫培養箱中進行5天的預培養,預培養完成后即正式開始培養實驗。分別在正式培養的第2、4、7、12、17、27、37、47天和第57天將盛有10 mL 0.2 mol/L NaOH溶液的25 mL的小燒杯置于廣口瓶中,用于吸收有機碳礦化釋放的CO2,廣口瓶加蓋密封24小時后取出裝有NaOH溶液的小燒杯,用濃度為0.2 mol/L的HCl溶液進行滴定,計算培養過程中土壤碳礦化的累積釋放量(mg C/kg)和礦化速率(mg C kg-1d-1)。
1.4 數據處理
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法分析土層、恢復年限和水分對土壤有機碳礦化瞬時速率和累積釋放量的影響,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土層、恢復年限和水分對最大礦化速率和平均礦化速率的影響,利用最小顯著差異法(LSD)進行顯著性檢驗,顯著性水平為0.05。土壤有機碳礦化最大速率、平均速率及累積釋放量和土壤理化性質及土壤水分含量之間的相關性的冗余分析用Canoco 5.0軟件實現。采用 SPSS 17.0進行數據統計分析。用 Origin 9.0擬合曲線并作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土壤有機碳礦化速率
整個培養期間,土壤有機碳礦化速率為培養前期快速下降,后期逐漸下降并趨于平緩。且同一土壤水分含量下,不同恢復年限固沙植被區碳礦化速率表現為63 a>46 a>32 a>8 a>0 a,同一植被區表現為BSCs >下層0—5 cm土壤(圖1)。土壤水分含量的增加顯著促進了土壤有機碳礦化的速率(表2,P<0.001),土壤水分含量從5%增加到20%時,不同恢復年限BSCs有機碳化的平均速率及最大速率分別增加了1.48—2.08倍和1.60—2.00倍,下層0—5 cm土壤增加了1.36—2.08倍和1.21—2.00倍(圖1,圖2)。
不同恢復年限、水分和土壤層次對土壤有機碳礦化的瞬時速率、最大速率影響顯著(表2,P<0.001);且恢復年限、水分與土層的交互作用的影響也顯著(表2,P<0.001)。
2.2 土壤有機碳礦化累積釋放量
整個培養期間,不同恢復年限固沙植被區土壤有機碳礦化累積釋放量為隨培養時間的延長呈不斷增加的趨勢。同一土壤水分含量下,不同恢復年限固沙植被區表現為63 a>46 a>32 a>8 a>0 a,同一植被區表現為BSCs >下層0—5 cm土壤(圖3)。土壤水分含量的增加顯著促進了土壤累積釋放量(表2,P<0.001),土壤水分含量從5%增加到20%時,BSCs累積碳礦化量增加了1.48—2.08倍;下層0—5 cm土壤累積釋放量增加1.21—2.00倍(圖3)。

表1 不同恢復年限固沙植被區BSCs及下層0—5 cm土壤理化性質

圖1 不同培養時間和水分條件下生物土壤結皮和下層0—5 cm土壤有機碳礦化速率Fig.1 Soil organic carbon mineralization rate in the biological soil crusts (BSCs) and the 0—5 cm subsoil under different incubation time and water conditions

圖2 不同土壤水分含量下BSCs和下層0—5 cm土壤有機碳礦化最大速率Fig.2 The maximum rate of soil organic carbon mineralization in the BSCs and the 0—5 cm subsoil under different soil water content不同大寫字母表示不同土壤水分含量間差異顯著(P<0.05),不同小寫字母表示不同恢復年限間差異顯著(P<0.05)

表2 土層、恢復年限和水分含量對土壤有機碳礦化瞬時速率、平均速率、最大速率和累積釋放量的影響

圖3 不同培養時間和水分條件下BSCs和下層0—5 cm土壤有機碳礦化累積釋放量Fig.3 The cumulative release amount of soil organic carbon mineralization in the BSCS and the 0—5 cm subsoil under different incubation time and water conditions
2.3 BSCs和下層0—5 cm土壤有機碳礦化之間的關系
BSCs有機碳礦化的瞬時速率、平均速率、最大速率、累積釋放量與下層0—5 cm土壤瞬時速率、平均速率、最大速率、累積釋放量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圖4,P<0.001)。

圖4 BSCs和下層0—5 cm土壤在有機碳礦化的瞬時速率、平均速率、最大速率、累積釋放量的關系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tantaneous rate, average rate, maximum rate, and cumulative release amount of organic carbon mineralization in the BSCs and the 0—5 cm soil under crust
2.4 土壤有機碳礦化與土壤理化性質間的關系
冗余分析結果表明,有機碳礦化與土壤水分含量及土壤理化性質密切相關,不同因子對有機碳礦化的解釋程度有著較大的差異,結皮層第一軸和第二軸分別解釋了有機碳礦化變異的94.05%和1.56%,下層0—5 cm土壤分別解釋了79.27%和3.76%(圖5)。其中,結皮厚度、生物量、電導率、有機碳、全氮、粉粒、粘粒、全氮、田間持水量和土壤水分含量與有機碳礦化的最大速率、平均速率和累積釋放量顯著正相關(圖5,P<0.01),而與pH和沙粒含量顯著負相關。結皮層中生物量、電導率、厚度、黏粒含量和有機碳是影響有機碳礦化的主要因素,下層0—5 cm土壤中有機碳、電導率和黏粒含量是影響有機碳礦化的主要因素。土壤電導率、有機碳和黏粒含量是影響有機碳礦化的主要影響因素(圖5)。

圖5 BSCs和下層0—5 cm土壤有機碳礦化與土壤理化性質之間的相關性Fig.5 Correlation be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 mineralization and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in the BSCs and the 0—5 cm subsoil
3 討論
不同恢復年限固沙植被區BSCs和下層0—5 cm土壤碳礦化速率為培養前期快速下降,后期逐漸下降并趨于平緩(圖1),表明微生物作用下土壤的有機碳礦化過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土壤中養分的供應[21- 22]。培養前期,土壤中大量可被微生物分解利用活性有機物質等逐漸消耗,隨著培養時間延長,微生物開始利用較難分解的復雜有機物,但這種過程緩慢[22- 23],因此土壤有機碳礦化速率逐漸減小后趨于穩定。這種有碳礦化速率先快后慢的變化趨勢在很多研究中均有報道[17,21- 23]。
同一土壤水分含量下,BSCs有機碳礦化的瞬時速率、平均速率、最大速率和累積釋放量均顯著大于下層0—5 cm土壤(表2,P<0.001),不同恢復年限固沙植被區土壤機碳礦化的瞬時速率、平均速率、最大速率和累積釋放量均表現為63a>46a>32a>8a>0a(圖1、圖2和圖3)。這與周玉燕等[23]和Su等[24]在旱地的研究結果相類似。說明隨著恢復年限的延長,土壤的結構,所含養分含量等因素發生了變化[23]。有機碳礦化過程受植被類型及凋落物、根系分泌物的性質和數量、參與碳礦化過程微生物數量和活性的直接影響,同時也受土壤碳庫的豐缺狀況、pH值等的間接影響[25]。不同恢復年限下地表植被類型、蓋度及多樣性及土壤理化性質發生變化,從而使土壤有機質、土壤氮含量及微生物群落的結構及活性存在差異,進而影響土壤有機碳礦化速率。此外,本研究冗余分析表明土壤有機碳礦化的最大速率、平均速率和累積釋放量與土壤的理化性質顯著相關(圖5,P<0.01),其中電導率、有機碳和黏粒含量是影響有機碳礦化的主要影響因素。
本研究認為植被恢復過程BSCs的演變也是其碳礦化差異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隨著BSCs的演變,其蓋度和粗糙度逐漸增大,捕獲和富集大氣降塵的能力逐漸增強,從而使結皮的厚度、土壤細顆粒物質和養分含量逐漸增大[26](表1),此外,BSCs還能夠改善微生境土壤的水熱因子,使得結皮層的代謝活性增強[9,12]。(2)隨著BSCs的演變,其蓋度和生物量顯著增加[7,9,12](表1),從而使結皮層單位面積CO2交換速率顯著提高[5,7,9,12]。(3)隨著BSCs的演變,BSCs的類型(藻類、苔蘚、地衣)的構成比例發生變化,從而影響碳礦化速率。通常與地衣和苔蘚相比,藻類結皮具有較低的生物量和葉綠素含量[5,7,12],以及更加有限光穿透力[27],因此使得固碳能力相對降低[7,9,12]。比如,干旱區以具鞘微鞘藻為主的生物結皮的固碳速率約(1 μmol CO2m-2s-1)顯著低于地衣和苔蘚為主的BSCs的光合速率(10 μmol CO2m-2s-1)[28-29]。(4)BSCs的不同演替階段具有不同的微生物組成和群落結構[30],對其碳礦化影響也不同。已有的研究報道了相似的研究結果[30- 31]。此外,本研究冗余分析表明結皮層生物量、電導率、厚度、黏粒和有機碳含量是影響有機碳礦化的主要因素(圖5)。
結皮層和下層0—5 cm土壤的各種有機碳礦化特征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圖4,P<0.001),說明下層土壤各種碳礦化特征隨著BSCs各種碳礦化特征的增大而增大。BSCs和下層0—5 cm土壤有機碳礦化速率和累積礦化量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圖1、圖3),但BSCs的碳礦化速率和累積礦化量均顯著高于下層0—5 cm土壤(表2,P<0.001),其他類似研究中也發現了相似的規律[17]。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首先,同一植被區,隱花植物的凋落物、分泌物、殘體以及大氣降塵等不斷在土壤表層積累和分解,有效促進了生物土壤結皮有機質、養分含量的增加,使得結皮層及下層土壤有機碳含量存在一定的差異(表1),這也是生物土壤結皮層及下層0—5 cm土壤碳礦化差異的主要原因。此外,不同土層的微生物數量和活性是影響碳礦化差異的另一個原因。BSCs微生物量熵大于下層土壤[32],這顯然為土壤碳礦化提供了微生物基礎;另一方面,BSCs在獲得充足的養分的同時,首先顯著改善BSCs土壤的理化性質,這為微生物的生存提供了適宜的條件,而下層土壤,除了BSCs所提供的養分很難到達外,理化性質變差也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本研究(表1和圖5)也證實了這一點。最后,BSCs是干旱沙區土壤碳和氮輸入的重要來源,這有利于結皮層養分的聚集。研究發現,隨著BSCs的發育,BSCs有機碳含量增加較為突出,10年以上的蘚類結皮土壤有機碳含量可高達20.9 g/kg[33- 34],BSCs通過固定大氣中的氮進而增加土壤氮輸入量,達2—15 kg N hm-2a-1[35],這均為BSCs的碳礦化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得BSCs土壤和下層土壤的碳礦化過程存在一定的差異。
BSCs和下層0—5 cm土壤有機碳礦化瞬時速率、平均速率、最大速率和累積碳釋放量均隨土壤含水量的增大而增大(圖1,圖2,圖3),其他旱地研究中發現了相似的規律[12,24]。表明土壤碳礦化過程主要與微生物的調節有關[36]。土壤含水量增加會使微生物的活性顯著提高,進而加速了有機質的分解[37],另一方面,高的土壤水分能改變土壤養分的擴散速率,通過釋放更多的土壤活性來提高土壤微生物基質的利用率[38]。此外,水分對不穩定有機碳組分含量和頑固性有機碳化率產生影響[39],土壤質地也可能影響微生物群落及細菌、真菌對土壤呼吸的貢獻[40]。表明水分對碳礦化的調控作用不僅受到微生物活性的影響,也與土壤質地、有機碳組分等密切相關。因此,水分對有機碳礦化的作用機理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4 結論
不同恢復年限固沙植被區土壤機碳礦化的瞬時速率、平均速率、最大速率和累積釋放量均表現為63a>46a>32a>8a>0a,且同一植被區表現為BSCs >下層0—5 cm土壤,且其碳礦化過程主要受電導率、有機碳和黏粒含量的影響。土壤水分含量從5%增加到20%時,BSCs土壤有機碳礦化平均和最大速率及累計釋放量分別增加了1.48—2.08倍、1.60—2.00倍和1.48—2.08倍,下層土壤分別增大了1.36—2.08倍、1.21—2.00倍和1.36—2.08倍,表明水分促進了固沙植被恢復過程中土壤有機碳礦化過程。由于本研究著重探討的是不同恢復年限固沙植被區BSCs及下層土壤在不同水分條件下的碳礦化特征,為了更深入了解植被恢復過程中BSCs演變對土壤有機碳礦化過程影響,還需要BSCs的蓋度、生物量及微生物屬性等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