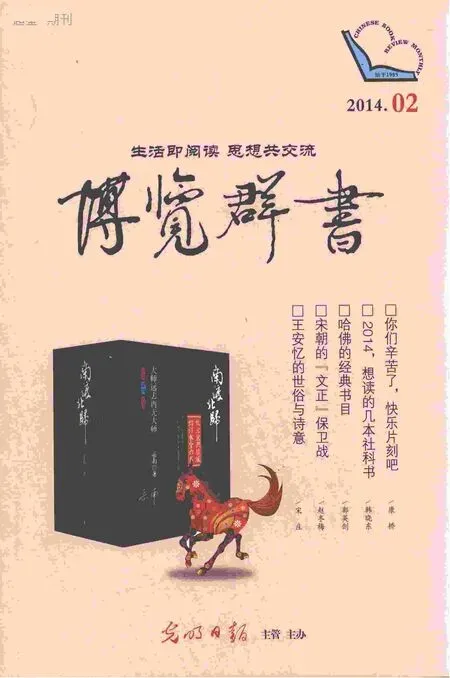豆腐與氣質
周巖壁
上一個春節,疫情隨著新春,突然而至。本來是回家過年,一下子逼得人足不出戶,非要你變成足不下樓、目不窺園的董仲舒!在家里窩了兩個月,百無聊賴。看到書房里那套72冊的《全宋詩》,灰頭土臉,拿下來翻翻吧。里面的風花雪月,應接不暇,真是連篇累牘。可惜在下,本是農家子,領略不了那種搔首弄姿的風雅,頗難共鳴。那么就一無所得嗎?不然!所謂不賢識小——全宋詩中,竟然只有兩首豆腐詩。
準確地說是,只有兩首詠豆腐的詩。一首是以豆腐為題,朱熹作的,是《蔬食十三詩》之一;這組詩是晦庵唱和其師劉子翚的,老師的組詩中并無豆腐。就是說,這是晦庵在和詩中增補的。詩云:
種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
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
這首詩只20個字,但涵義頗深。大致是說:像陶淵明那樣辛辛苦苦地種點豆子,用盡心力,秋天收成并不好;如果早早就學會做豆腐的技藝,不用筋疲力盡,安安穩穩地坐著,也能賺不少錢呢。
另外,《全宋詩輯補》第七冊,收南宋末陳達叟《啜菽》一首:“禮不云乎?啜菽飲水。素以為絢,瀏其清矣。”這是《蔬食二十品》之一。蔬食,就是素食。要了解這首詩,我們先要知道什么是啜菽。這是《檀弓》中孔子的話:“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孫希旦引王注:“熬豆而食曰啜菽。”(《禮記集解》卷十一)就是說,家里很窮,吃不起大米白面,只好把大豆煮熟或炒熟了當飯吃,渴了就喝點水,生活很艱難。陳達叟的意思是說:吃不起豆腐——雖然此詩不是詠豆腐,但陳達叟在南宋末年,應該是知道有豆腐這位食品的——,只好像孔子所說的那樣吃豆子,喝水;但精神上很充實,有情操。
我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后漢書》載:周黨見節士閔仲叔,“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李賢注引皇甫謐《高士傳》說:周黨送給仲叔生蒜,是看他沒有下飯菜,給他作菜的。仲叔說:“我欲省煩,今更作煩邪?”所以受而不食。這表明,秦漢以來,窮人日常生活就是啜菽飲水,聊以果腹罷了;哪里見得到細米白面?
與朱熹有過交際的陸游,在《鄰曲》中說:“濁酒聚鄰曲,偶來非宿期。拭盤堆連展,洗釜煮黎祁。”自注:“蜀人以黎祁名豆腐。”馬廷鸞《謝毛子文見壽》:“苜蓿黎祁湯餅會,一洗眊臊強持杯。”把又名黎祁的豆腐看得很尋常,但我們要注意,它都是在家庭宴會上吃的。所以,當時窮人家里,未必經常吃或吃得起豆腐。而且朱熹在上引豆腐詩中自注:“世傳豆腐本乃淮南王術。”我們認為,這個說法是靠不住的。大概是劉安發明了豆漿,把泡脹的豆子磨成細末,這比干吃豆子要好受得多。西漢劉安既然發明豆漿,東漢的節士為什么還啜菽呢?不是仲叔自找苦吃,實在是需要勞力,干什么都要人力畜力的時代,磨杯豆漿喝并不容易!至于由豆漿而豆腐,需要有礦物加入,外力干預,產生質變,民間所謂“點豆腐”。我們看李時珍豆腐造法:
水浸硙碎,濾去滓,煎成,以鹽鹵汁或山礬葉或酸漿、醋淀就釜收之。又有入缸內,以石膏末收者。大抵得咸、苦、酸、辛之物,皆可收斂爾。(《本草綱目》卷二十五)
這豈是西漢可能做到的?所以,綜合考慮起來,豆腐是五代才有的。這樣唐詩、北宋詩歌中都沒有提到,也就可以交代過去。南宋時,豆腐在民間流傳漸廣。由朱熹和陳達叟等人的詩,我們知道豆腐在南宋并不普遍,因為它需要勞力,精細加工。雖是蔬食,價格還比較昂貴。經濟拮據的,蓬門篳竇,只好還煮或炒豆子吃——豆子這樣吃起來,是粗食,有點剌嗓子。它還可以磨成豆面,但必須和白面摻和才能做成面條,才好吃;純豆面沒有彈性,而且吃起來不夠細膩潤澤,令人難以下咽。
不過,宋末已有人終生以磨豆腐為業了。度宗咸淳年間(1256-1274年),有個賣豆腐的王老頭,他去世時86歲,留下一首絕命詩:
朝朝只與磨為親,推轉無邊大法輪。
碾出一團真白玉,將歸回向未來人。
(《全宋詩》第57冊)
我們開頭說全宋詩里有兩首豆腐詩,一首是朱熹的,另一首就是這個王老頭的。它對自家磨豆腐的一生,做了生動、真切的概括;把一生升華為一首詩,閃爍在歷史灰暗塵埋的雜亂里,不容易啊。
隨著元明歷史的展開,豆腐的生意也越來越紅火。元代王禎《農書》中首次出現“黃豆可作豆腐”,這樣明確的斷言。(《農書·百谷譜集之二》)豆腐也進入元明平頭百姓的日常生活:這在元曲中就有反映。《西廂記》中普救寺僧惠明抱怨叢林生活清苦,“酸黃齏爛豆腐”,吃厭了咸菜豆腐。(楊緒容《王實甫〈西廂記〉匯評》,人民出版社,P106)《看錢奴》中賈仁只舍得拿一個銅錢賣半塊豆腐,是不夠一個人做下飯的;也就是說,兩個銅錢可以買一塊豆腐,那就湊合夠一個人當菜吃一頓。可見,元時豆腐已經隨處可得,價格便宜。
明初有兩首豆腐詩,寫得不錯。蘇平《詠豆腐》云:
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
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
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
個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說淮南王劉安發明豆腐,就像說倉頡發明文字一樣,在詩歌里是認不得真的,只是作為一個典故為詩人吟詠提供便利。孫大雅《菽乳》:
戎菽來南山,清漪浣浮埃。轉身一旋磨,流膏入盆罍。
大釜氣浮浮,小眼湯洄洄。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花皚。
青鹽化液鹵,絳蠟竄煙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口,不畏老齒摧。
(《列朝詩集》甲集第十五卷)
這首詩用賦體描寫豆腐的制作過程,是前引李時珍說明文的詩化,給豆腐賦予審美價值。孫大雅還嫌豆腐的名字不好聽,改成菽乳;菽乳未必好聽,而且就字面意思看,菽乳是豆漿。詞不達意,不免畫蛇添足,弄巧成拙!竭力給豆腐提升審美境界的,還有清代的查慎行。他有《豆腐詩四首》,我們摘句如下:
凝來石髓風猶軟,點出春酥露未干。
倒篋易償鄰叟值,顧名原合腐儒餐。
半爿土灶燃萁火,一頃山田種豆詩。
饔子貧家先染指,廚娘纖手并凝脂。
滑可流匙勝冷淘,不爭舌在齒牙牢。
比查慎行晚點的袁枚,是個著名的美食家。在他的《隨園食單》里,列舉了九種豆腐的吃法,大都需要大蝦米或雞湯、鰒魚、火腿、雞丁分別來配。我們很奇怪,袁枚在詩學上是提倡“性靈”的,在豆腐制作上怎么如此變態?這些葷菜幫襯出的豆腐,性靈安在,還有豆腐味兒嗎?倒是《隨園食單》的補證者夏曾傳說得好:“豆腐吃法甚多,不可枚舉。夏日吃生豆腐,則麻油鹽拌。”
半閑堂主說他最愛吃又最省事的,就是這種麻油調豆腐,俗話所謂“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做法如下:新鮮豆腐一塊,清水去塵,淋去水。把豆腐切成小塊,用切成小段的蔥,撒細鹽,拌芝麻油,即成。吃起來,干凈得真味;看起來,一清二白。
查慎行《豆腐詩》:
行廚亦可咄嗟辦,下箸唯聞鹽豉香。
須知淡薄生涯在,水乳交融味最長。
與此類似,特多豆豉耳。一清二白,這正是不求聞達、潔身自好、甘于貧賤的傳統文人氣質之象征。
總結一下,豆腐的原料是大豆,大豆是一種中國谷物,所以豆腐是純粹的中國食物。它是在五代出現的,此前處理大豆的方式,就是炒熟或煮熟,相對精細的吃法是磨成豆面,更講究的是磨成豆漿飲用。豆腐在南宋并不常見,但很得讀書人喜愛。元明時,隨著技術進步和制作方法的完善,豆腐漸漸普及。在清代詩歌中,豆腐成為傳統文人潔身自好品格的象征;二者相得益彰。
(作者系鄭州師范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