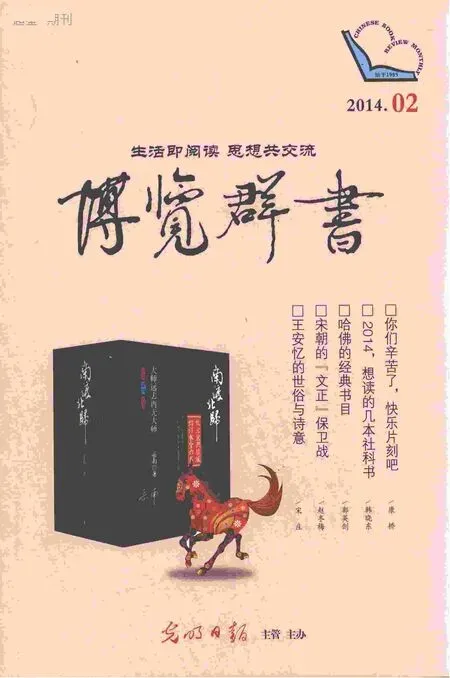由此進入那些士大夫的心靈
霍志軍 楊成凌
唐代文學一直是古代文學研究的“熱門”領域之一,中唐文學又是整個唐代文學研究的重點,多年來已經積淀了許多研究成果,已臻精耕細作之境。近二十年來,唐代文學研究日新月異,特別是新資料的發(fā)掘和整理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新的觀點、選題也層出不窮。不少學者感嘆唐代文學研究目前已經很難找到新的選題了。田恩銘教授《元稹和中唐士人心態(tài)》(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以下簡稱《元稹研究》)則是近年來中唐文學研究的可喜進展。全書以元稹這一中唐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入手,從政治形勢、社會環(huán)境、思想流變、生活風尚等方面揭示整個中唐士人群體的心理狀態(tài),為了解特定歷史時期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新途徑,拓寬了研究視野。
研究視角:舊話題與新思路的融合
《元稹和中唐士人心態(tài)》一書首先將陽城故事作為本章之基,通過探討儒道思想結合下,作為士大夫階層典范的陽城對隱與入的選擇,揭示元和士風駿發(fā)的起點。陽城在貞元時期引領一時之士風。元稹、白居易以“詩筆”展現(xiàn)史才,稱頌陽城之德行,伸張士人的直正風氣,推動以陽城事跡入史。尤其是元稹的《陽城驛》,以史傳筆墨入詩,以史家詩筆寫人。由于元稹是中唐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在整個中唐文學發(fā)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從元稹切入,實是審視中唐文學的一個極佳視角。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人多有體會,好的選題乃成功之半,從元稹切入,具有一種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之效,中唐文學家的相互交往、相互酬唱,他們彼此的文學交游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關系,中唐文學發(fā)展的脈絡等等,都可以從元稹這一具體的人物身上管中窺豹。
這部著作注重梳理元稹的文學交游空間,考察以元稹為中心中唐士族文學交友群落的形成,完成研究士風與文風之意圖,并梳理出元、白等胡姓士族與其他文學家族所構成的文學群體與唐代文學風貌的關系。不同的地理空間會影響作者的人格氣質、審美選擇。元稹宦游各地,其詩章自然浸染了不同地區(qū)的文化景觀。不同文化區(qū)的對比,使元稹吸納的區(qū)域文化特征就多了,可資利用、選擇的文化資源就豐富起來,不同文化區(qū)文化特征的相激相蕩,就有可能激發(fā)出一種新的精神境界、一種新的審美方式。作者從古代文學的實際出發(fā),深入到元稹一生所游走的中原、巴蜀、浙東等不同文化區(qū)中,去探討元稹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變化,將不同區(qū)域文化背景與詩人的心理相聯(lián)系,得出的結論就較為公允,復合中唐文學演進的實際情況。總之,《元稹研究》一書選擇的是“舊話題”,采取的研究視角卻不失新穎和獨到,細微處常常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研究方法:“小群體社會學”方法的成功運用
美國的西奧多·M·米爾斯認為,在社會地位和角色關系上或多或少相互依賴的一組人,他們具有共同的價值規(guī)范及彼此協(xié)調一致的社會行為。人們之間的關系更多受到小群體內交往的相互影響。以元、白為中心形成的唱和群體是以唱和交往為活動中心集結的小群體,這些詩人擁有相似的創(chuàng)作理念、文學宗旨和藝術情趣,相互影響,并推動了古代詩人流派的形成。著者以元稹與盧氏兄弟、“四李”、竇鞏及白居易的文學交游為中心,分析元稹在交游中的心態(tài)變化,并以元、白之唱和及交往為重點進行論述。
元稹在貶往江陵途中作《思歸樂》給白居易,白居易以《和答詩十首》和之;而元稹收到白居易被貶江州途中所作《寄微之三首》,亦以《酬樂天赴江州路上見寄三首》相和,來寬慰好友,互訴情志。這些以貶謫為中心的酬唱呈現(xiàn)出二人守直而遇挫折的應對態(tài)度:弘揚直道,反映出中唐士人群體的一個側面。元、白人生階段的重疊創(chuàng)造了彼此之間頻繁交游的客觀條件,政治理想、詩歌創(chuàng)作理念的一致也讓情感的交融增加了理性的意為。元和十年,元稹被貶通州,作《敘詩寄樂天書》一文。闡述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過程、對詩歌分類的觀點以及立言的看法。其后,白居易作《與元九書》回復元稹,著意闡述自己的文學觀念,創(chuàng)作經驗,詩歌理論。二人各自闡發(fā)文學主張,相互探討,唱和活動進入巔峰。在頻繁的酬唱中,元、白相互借鑒、各自改創(chuàng):元稹在《放言五首》中一反之前的激憤之情而表現(xiàn)出內心的曠達,而白居易的《放言并序》也以同樣的起興開始,可見白詩受到了元詩的影響,元稹《陽城驛》對陽城故事的敘述也受白居易“意太切而理太周”的影響。但二人創(chuàng)作風格在融合之后仍保持自己的底色,以蘄進益。到長慶時期,元、白交誼集中,二人文學觀念也逐漸已定型,《元白酬唱集》也結集于此時。元、白唱和小群體創(chuàng)作主張為后世創(chuàng)作者所接受,在批判中得到繼承與發(fā)揚,逐漸形成“元和體”。在古典文學研究中,該書在研究方法上,成功借鑒了“小群體社會學”的理論,理論運用圓通自如,結論自然更具說服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可圈可點之處,相信這一點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顯示出來。
該書以精密的考證見長,憑借著者對文史資料的準確把握與深刻領會,爬梳剔抉。作者每論述一個問題都以嚴謹?shù)氖妨蠟榛A,重視對原始資料的梳理、考證,注重文史結合但未囿于史料之內,而是對相關史料進行了詳細篩選,以嚴謹?shù)恼撌鰧⑾嚓P材料統(tǒng)一起來,且論述獨到,不發(fā)空論。《元稹研究》從身份意識出發(fā),論述元稹的仕宦經歷及其對文學活動的影響。依托《舊唐書》《資治通鑒》《唐紀》《元公墓志銘并序》等文史資料以及元稹現(xiàn)存的詩文,對元稹三個主要的文官身份進行考證,并認為諫官身份使元稹具備了濃厚的諫臣意識,奠定了元稹文學創(chuàng)作的政治母題,是貞元、元和時期諫諍風氣的一個縮影;御史官身份催生了元稹的反思意識,對因直被貶的反復思考,以任職經歷為中心,職事活動為素材完成了對政治母題的集中書寫;任翰林學士期間完成了制誥改革,文學才能亦因此得以擢升,迎來其詩歌傳播的高峰期。同時文官職位與地方官職位交錯,使元稹形成對文學的疏離與刺激:任職時文學與政事分離,以家人、朋友為抒寫中心,政事伏于其中;任畢,政事再浮出水面。文學與政事的交互作用下,文學文本的內涵也更加豐富,形成了以政事為中心的主題書寫。
對元稹文學交游、唱和的考論,以精密的考證為基礎,展現(xiàn)心態(tài)變化中士風與文風的關系。有據(jù)而言,論從考出,使結論更具可靠性、說服力。在論述元稹與“四李”的交游中,對其交往活動進行了精密的考證。如在考證元稹與李景儉交往時,按照元稹與李景儉的交往為線索對史料進行梳理、論述。著者先據(jù)《舊唐書》本傳、溫呂《唐故太子舍人李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志銘并序》等文獻對李景儉為人狷狂、不屈居人下的記載,認為李景儉為士大夫中有風骨者,通過對其人、其才、其德的考論,展現(xiàn)了貞元至長慶時期一位狂狷的士大夫形象。在論述二人交往時,根據(jù)元稹《酬別致用》所載元稹、李景儉被貶江陵時,交誼漸深,終“交定生死”的史實,以及元稹《葬安氏志》、《敘詩寄樂天書》等篇目對李景儉勸元稹再娶、收集詩作的記載,認為二人不僅在生活中、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均有密切交往,元稹第一次對自己的詩作編集,就是在李景儉的勸導下,這為元稹文學觀念的生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此后,元稹的《酬李六醉后見寄口號》《哀病驄呈致用》《飲致用神曲酒三十韻》《江邊四十韻》等詩作頻繁提及李景儉,并在《與李十一夜飲》《憑李忠州寄書樂天》中盡情抒寫自己對李景儉的思念、傾吐貶謫之苦,著者即從詩文的角度對二人的交往過程進行考論。以《舊唐書》本傳、卷一百二十一,元稹《別毅郎》等材料為依托,論述元稹與李景儉定“生死”而能終之,充分證明元稹實乃重情重義之君子。
接受視野:三維空間下的文學接受史觀
《元稹研究》從文學接受史的角度探討元白并稱及元稹的文學家形象與士人形象的關聯(lián)。雖然王拾遺、卞孝萱、楊軍等學者對元稹的研究日漸深入,卻依然未將元稹及其作品從依附狀態(tài)中解脫。元稹的樂府詩在文學史中一直處于附屬的地位,元稹也為白居易的光輝所遮掩。《元稹研究》一書從元稹樂府詩的接受史入手,就元白并稱,將兩人置于文學史的洪流中進行對比。在文學通史中,元稹自唐以來就趨于第二梯隊,能跟“新樂府運動”沾邊已是幸事;而白居易則位列中心。在唐代文學史中,元稹的樂府詩多被劃入“新樂府運動”、或成為白居易樂府詩論的腳注。對其樂府詩的評價普遍偏低,或以元不如白,更有甚者直接貶斥,僅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學史》、吳庚舜、董乃斌的《唐代文學史》中,對元稹樂府詩專門論述,且態(tài)度較為公允。在唐詩史中對元稹樂府詩的評價,在內容上與文學通史相類,在敘述格局上甚至不如唐代文學史。在域外文學史中,對其樂府詩持不認可的態(tài)度,與白居易并稱時,即使提到也是一帶而過。著者將古今中外的文獻史料一一梳理,分別論述不同史料中呈現(xiàn)的對元稹樂府詩的接受情況,通過實證輯考,構建接受維度。
元稹既是文壇的領航者,又是官場的顯宦,卻落得有才無德的定評。唐代對元稹的評論以文學視角為主,中心議題圍繞“元和體”及其創(chuàng)作展開,聚焦于元稹文學家的形象。《舊唐書》的傳記文本由此產生。傳記文本從采擷文章入傳,對元稹文學才能多方贊譽的書寫傾向,文后“論贊”的評價傾向三方面,突出了元稹文學家的形象。五代至北宋對元稹形象的接受由文向人轉變,五代時期專門論述元稹文學成就的文章極少。唐宋思想轉型所形成的文化轉型直接導致了北宋史學家對元稹“巧宦”行為的貶斥,至李綱、張九成筆下,元稹的“巧宦”形象到已成定論。南宋時期對元稹形象的接受呈人文分論的狀態(tài)。總體而言,宋人對元稹普遍評價不高,以巧宦形象為主。作者對于元稹形象的后世傳播與接受以及元稹形象的復雜性等論述,有自己的創(chuàng)獲;對元稹詩歌創(chuàng)作的總體成就及特色及其對整個中晚唐文學的影響等文學話題用筆較少,此點或與選題有關。
關于古代士人心態(tài)研究的著作要以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tài)》影響最大,左東嶺、劉懷榮、王德權、田安等學者均有相關的著述問世,這些著述將焦點人物放在具體時代語境中,以小社會群體為觀照對象,形成跨學科綜合研究的熱點。從宏觀上看,這一研究如何繼續(xù)推薦,與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交叉建士人心態(tài)、與地域、族群相互融合富于創(chuàng)新性的領域;就文學研究看,如何與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文學理論結合起來,構建新的文學研究形態(tài),均是需要不斷反思的話題。總之,個人生活在具體的時代中,生活在具有流動性的群體變化中,心態(tài)史研究能給我們建構出屬于特定時代的復雜的精神世界。
(作者簡介:霍志軍,文學博士、天水師范學院教授;楊成凌,天水師范學院古典文獻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