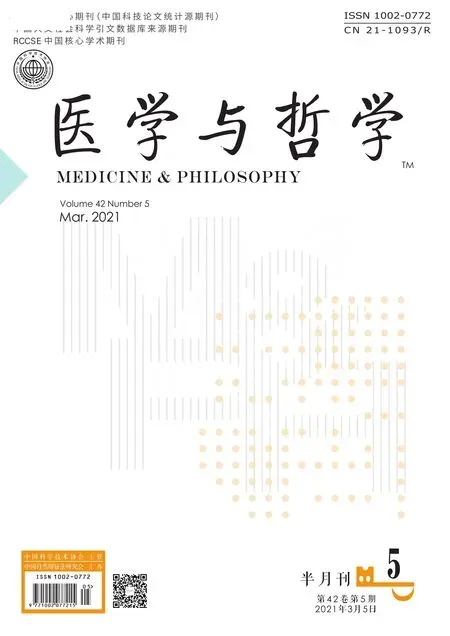軀體化癥狀患者求醫體驗的質性研究*
王艷波 趙旭東 馬希權
軀體化(somatization)被臨床定義為缺乏確定病理證據的生理不適以及由確定病理導致的癥狀擴大化[1]56-57。軀體化患者有迫切的診治需要,但因為無法檢測出確鑿、與臨床癥狀相符的客觀證據,經常被內科醫生拒絕給予生物性疾病相關處理,或直接推薦到精神科室就診[2-3]。因患者本人對癥狀的生物性解讀,及對心理社會歸因的不接納性,導致患者對精神醫學相關診療心存疑慮,而依舊進行反復檢查和各種醫學治療,這給患者帶來了對自身所患“何病”的困擾[4-5]。另外,軀體化患者對病癥通常有自己的解釋,無論這個解釋模型是被證實或證偽[6],多數軀體化患者在就醫過程中體驗到的醫生解釋都是拒絕和否定性的,間接否認了癥狀的真實性,或暗示病癥的想象性,患者常因此與醫生產生沖突,或不接受醫生觀點。這種沖突、醫生不信任等帶給患者被歧視及不公正對待的感覺,也加重了其心理負擔[7]。
在我國,醫生和軀體化患者對于疾病解釋的一致性非常低,患者更傾向于將疾病歸因于“操勞過度”和“免疫力下降”,以及“過去不良的醫療”。而醫生對患者自身疾病歸因模式的關注往往不夠,患者對于醫生“對于病因的看法一致”認同度普遍較低[8-9];Kleinman[10]在1982年的研究顯示,軀體化患者認為工作、政治、婚姻和家庭、考試及學業問題是主要致病原因,而營養、遺傳因素僅占少數。中國臺灣地區[11]和新加坡[12]學者的研究同樣顯示對軀體及精神痛苦的病因性解釋方面,民眾與醫療專業人員存在明顯分歧,在干預方面,除了醫療機構,民眾往往還會通過宗教活動、寺廟祈福、尋求親友等方式緩解和治療病痛。
研究顯示,軀體化患者生活經歷會消極地塑造他們的生活態度,使患者更關注于“存在性承認”(existential recognition),體現在對身體的體驗、感覺、意圖等的確認以及人際互動中的認可及鼓勵;醫生對軀體化癥狀肯定、賦權性解釋則可以讓患者感覺滿意、提升生活質量[13]。事實上,軀體化患者經常感覺到不被信任、不被尊重、對自我認知判斷的不確定、缺乏被認可,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患者的自信心及對癥狀的知覺和應對態度,這些消極體驗與患者低自信、回避性應對方式、應激增高、損害應對能力等相關[14]。
本研究擬通過對軀體化患者就醫過程的深入訪談,探討其在治療過程中對自身疾病的歸因與理解、與醫療相關群體互動過程的體驗。
1 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采用解釋現象學分析法(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IPA)。IPA起源于健康心理學領域,致力于研究人們如何理解其生活體驗[15]1。此方法提倡采用目的性抽樣,以同質性小樣本為研究對象,深入詳盡分析個案,以更好地呈現個體對自身體驗的理解。
1.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招募于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臨床心理科,采用目的取樣法,納入標準:因“軀體不適”來臨床心理科就診,之前未被內科醫生檢查出有器質性疾病證據,經兩名精神科主治醫師評定符合“軀體癥狀障礙、抑郁障礙、驚恐障礙、廣泛性焦慮診斷”患者;排除標準:合并器質性精神疾病、物質依賴、精神分裂癥、雙相障礙、進食障礙患者。本研究獲得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參與者簽署了知情同意書。
研究樣本量按照“資料飽和”原則確定,即以受訪者資料重復出現、且資料分析時不再有新的主題呈現為標準,最終有12名研究對象參與研究,基本資料見表1。為保護被試隱私,登記資料及引用訪談文稿時,均采用P1、P2……P12 進行指代。

表1 研究對象一般資料
1.2 資料收集
采用半結構式深入訪談,每次訪談持續約60分鐘。訪談開始前,研究者先自我介紹,征得對方同意并建立信任關系后進入正式訪談。在獲得參與者同意的情況下對訪談進行錄音,并于24小時內轉錄成逐字稿。訪談主要圍繞如下問題展開:(1)能說說你的主要不適有哪些?(2)你覺得是哪些原因導致你的不適?(3)這些不適對你有哪些影響?最讓你苦惱的問題是什么?(4)你覺得身邊的人如何看待你的身體不舒服?(5)你都嘗試過哪些方法應對你的不適?(6)你去過哪些科室就診,這些科室的醫生如何解釋你的問題?(7)對于接受過的治療,你覺得哪些對你是有幫助的?(8)未來你會怎么處理你的不適?
1.3 資料分析
參照Smith等[15]82-92指南進行資料分析,IPA分析始于單個個案,完成首個文本的詳細分析后,再開始處理下一個文本。具體分析步驟如下:(1)反復閱讀轉錄文本;(2)初步注釋與評析;(3)提出主題;(4)尋找主題間關聯;(5)開始下一個案分析;(6)尋找個案間的主題模式。為避免個人主觀意見及經驗影響,研究結果經2名研究者共同討論分析,并不斷對資料分析結果進行比較和校準,從而確保分析結果的準確性。
1.4 質量控制
所有訪談和資料分析均由兩名研究者完成,他們均有至少5年定性研究經驗。訪談提綱由研究者通過文獻回顧及臨床精神衛生專業人員討論形成。為保證資料分析信度,2人每2周~3周開會討論、比對及回顧編碼思路和結果,最后達成一致的分析結果。同時采用反饋法,將編碼結果反饋給其中2名被試,根據被試反饋意見對結果進行修訂。
2 結果
依據IPA指南對訪談轉錄文本進行分析,獲得如下3個主題,分別是:癥狀引發的困惑與反思、癥狀對個人生活的負性影響以及曲折的治療經歷。
2.1 癥狀引發的困惑與反思
癥狀引發的困擾包含兩個亞主題,即癥狀本身的無法定性以及就診過程中醫療專業人員解釋病癥時帶來的困擾。12名受訪者均因軀體不適開始求醫經歷,9位患者能夠回憶起最初病癥的部位、性質及出現時間,分別是消化系統不適3人、心臟不適2人、頭疼3人、頸椎痛1人,其余3人的初始癥狀是頭暈、乏力、軀體酸痛、內臟不適等非特異癥狀。受訪者大多表現出對病癥發作變幻莫測的不知所措及對醫學專家診斷話語的困惑。
2.1.1 癥狀的多變與不確定
12名研究對象均表示了他們癥狀體驗的多變性,病癥部位、性質、發作等均無規律可循。P1和P5用“神奇”來描述癥狀的不請自來,不可預知。
P5:“病情會隨時隨地出現、沒有任何征兆來訪,神奇的不可理喻。”
研究對象癥狀的描述清晰、細致入微,但找不到可以支撐癥狀存在的客觀證據。如P1和P9體驗到反復胃痛,但胃鏡檢查結果無法支持患者胃痛癥狀;P3和P11體驗到強烈的心前區不適,而心電圖及心超檢查無異常發現;因此內科醫生無法給出明確的軀體診斷。病癥不固定、可以發作在多個系統,如P3 經歷了由頭暈—尿頻—心悸—背部疼痛的病癥挪移,本人也輾轉神經內科、泌尿科、心內科、中醫科、疼痛科等多科室就診。他們對非特異性病癥的不可描述性體驗深刻。
P11:“我是做HR(人力資源)的,表達能力還不錯,但沒有辦法說明白咋個不舒服,就是說不出來的難受……”
病患往往用“脹痛、酸脹、發緊、麻、暈、無力”等語言,來描述自身軀體不適。病癥發生的無規律性(起始時間、癥狀表現、誘發原因等)及無據可循,使得內科專業人員無法解釋并給予相應診斷,最終推薦到其他科室包括中醫、精神醫學相關科室就診。
2.1.2 對醫生診斷話語的困擾
12名受訪者在經歷多科室診療后,最終均被轉介到精神科。按照患者對精神科治療的接受態度歸納,有8人不接受或不確信自己的精神疾病診斷,認為自己病痛源自未查清的生理性機制或其他未明的原因,鑒于治療的有效而接受了精神專業服務,但對治療表現出矛盾、猶疑心態,經常糾結于“用藥-停藥-用藥”的反復過程;或者一邊接受精神治療,一邊仍在尋求其他非精神專業的干預方案,屬“否定矛盾型”。
P9:“不覺得是心理病,明明是身體不舒服,內科查不出來就推給你們(精神科)了……”
雖然獲得了精神科專業支持,并取得很好的治療效果,但精神專業人員對軀體化的解釋不符合受訪者對病癥的解釋預期。
P9:“說不到心里去、不理解那一套說法、不符合自己的想法。”
而內科醫生對其生物性疾病的否定,增加了他們對疾病本質的困惑。來自醫療專業的解釋和自我體驗的“非自洽性”沖突,導致受訪者對病癥本質產生疑問和困擾。
另外4人(P8, P10, P11,P12),不排斥自身病癥的心理社會(非生物性)病因學解釋,接納了精神治療,治療依從性高,屬于“接受型”。其中2人也有同樣的困惑,但他們放棄了探索,選擇相信精神科醫生的解釋。
P10:“醫生說是心理問題,我也感覺跟自己的心理壓力有關,關鍵是抗焦慮治療也挺有效果的,不管如何,還是應該相信醫生。”
2.2 癥狀對個人生活的負性影響
癥狀對個人生活的負性影響,體現在社會功能方面,如日常生活和工作狀態等受到損害。個人也體驗到自我的變化,自我疑慮增多和失去自我掌控感等。
2.2.1 社會功能受損
病癥嚴重影響了受訪者的工作和日常生活,4人因病而調整了工作崗位或離職。
P1: “我之前是坐辦公室的,經常感覺心煩、覺得領導給安排的工作太多,自己沒有信心做好,越擔心越容易出錯,后來跟家人商量了一下,就離職自己做了……”
3人表述自己的工作能力受到損害,工作效率下降。
P2:“每天總想著自己身體不舒服,想著怎么辦,哪有心思好好工作呢?”
6人表示家庭關系和日常生活受到損害。10人表示曾遭遇親友的不理解、誤解、嘲笑、斥責等不友好的經歷,因而體驗到苦惱、痛苦、孤獨,甚至與家人等發生沖突。不敢告知單位同事或朋友自己的病癥,擔憂不被理解,當成“異類”,甚至“神經病”。
P2:“家人感覺我太折騰了,好像沒事找事一樣,工作換了、賺錢少了,還總說自己身體不好,醫院都跑遍了也沒有檢查出毛病,實在是無語……”
2.2.2 對自我失去掌控
10位受訪者直接或間接表示在與病痛抗爭中屢受挫折,自信心受損,自我懷疑增加,以及失去對自我的掌控感。5人訴本來只是身體不舒服,后來產生了情緒問題,如焦慮、恐懼、緊張。3人有驚恐發作的瀕死體驗或失控感。5人表示患病后自己的行動受到影響,不敢獨處或外出,在家或外出均需要人陪伴。
P3:“心總是懸著,好像偷皮夾子被人捉的感覺。”
3人表示對死亡的擔憂讓其無法活在當下,并懷疑自己的生活方式,7人明確提及改變或計劃改變自己原有生活方式,心理上不再認可原有的生活,或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需要家人或專業人員的陪伴或指導。
2.3 曲折的求治過程
包括多個科室的就醫經歷、嘗試民間療法以及對精神科就診的復雜心態。
2.3.1 多科室就診經歷
受訪者均經歷過反復不斷到醫院求證,又不斷被否定拒絕,輾轉于醫院各科室就診的經歷,統計顯示,在來精神科就診前,受訪者到訪過的科室最多達10個,最少3個。中醫科、消化科及心內科是被光顧比較多的科室。
P8:“我幾乎走遍了你們醫院的各個科室,因為家距離你們醫院近嘛,上海另外有名的幾家醫院也都去過了,去醫院是熟門熟路了,估計門衛都認識我了……”
醫療費用支出也非常多,受訪者為了搞清楚自己的疾病,不惜花費重金去做檢查。
P5:“醫生告訴我,××醫院進了最新的PET/CT檢查,全身檢查價格要上萬,而且自費,我不管了,馬上拿錢去做……”
2.3.2 嘗試不同的民間療法
在醫院就診之外,受訪者也嘗試過其他干預,各種民間療法。有5人曾去求神拜佛或算命驅邪,如寺廟拜佛、改名字、請求大師調整風水等。
P7:“我七月半的時候,到楊思廟里祭拜,燒了健康香和平安香,也給逝去的公公和老公燒了兩袋錫箔,希望能有用。”
11人嘗試過傳統中醫保健方法:氣功、針灸、按摩、拔火罐、練五禽戲、服用偏方等。7人試圖通過自我調整,如靜修、呼吸調整、多參與社交活動、定期體育鍛煉、規范睡眠和作息時間等方式應對癥狀影響;此外,6名受訪者表示經常網絡搜索相關疾病的信息或加入“焦慮、抑郁、強迫癥”等病友群,尋找解決病痛的方法。受訪者也表示會受到網絡 “智能推送”碎片化、海量、負性結局取向為主的信息的困擾。甚至懷疑醫生的診斷和治療,造成進一步困擾。
P11:“經常上網搜索相關資料,結果進了一個焦慮病友群,成天發送有關精神疾病的信息,也有病友發言說自己治療體驗的,我也試了試,感覺不合適,信息太多了,搞得我心煩意亂,索性退了群。”
2.3.3 精神科就診的復雜心態
就診于精神科治療后,會形成不同的針對精神治療的態度,分別是接納與成長、猶豫與矛盾,分述如下。
(1)治療有效,接納精神科治療:與軀體病痛作斗爭占用了受訪者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患者往往在嘗試多種方式去緩解身體病痛未果后最終到精神科就診。
P4:“這(精神科就診)應該是我最后一站了,我折騰了3年還是沒有好轉,自己都要崩潰了……”
受訪者中11人服用精神類藥物,服藥同時接受心理治療者3人,1人已停藥。所有受訪者均表示精神治療有效,緩解或者控制了自己在其他內科就診中不曾改善的軀體不適癥狀。3人恢復或者基本恢復了患病前的工作和生活狀態。9人明顯改善了軀體不適,雖未達到病前狀態,但痛苦不再像以前那樣難以忍受。
2位受訪者由家屬建議或自己來精神科就診,另2人是內科醫生轉介而來。患者在保持現有精神治療同時,主動增加自我調節,如學習佛學、自我反思等。部分受訪者會在自我調節中尋找與身體病癥和解的方法,并整合到現有治療中。
P3:“思考自身性格的不足,急躁,情緒不穩定,處理問題方式的不足、功利思想嚴重、調整作息和睡眠時間、學會與癥狀對話。”
(2)對精神科診療的猶豫與矛盾:從治療過程看,部分受訪者,接受精神治療大多是源于他人的勸說,尤其是就診過的內科醫生的轉介。他們關注精神治療的效果,在藥物治療有效的前提下繼續維持精神科干預,表現出效果導向的實用主義態度,但不認可心理咨詢。在治療過程中,他們同時對精神藥物副作用極為擔憂,對精神藥物的“成癮性”心存戒備,因而,自行停用藥現象時有發生,并試圖尋找其他的治療辦法,以替代現有精神治療。此類患者對情緒問題有平常化的解釋傾向。
P2:“人人都會焦慮,但是與身體的不舒服有關系嗎?身體不適就是不舒服,跟心理有啥關系?”
4人會有自主感增強的體驗。
P4:“好像自己變成了醫生。”
多數患者承認心理問題的存在,并努力發展符合自己的調整方式,學會與疾病共存,發展自主性。而否定矛盾者則不然,對病因的困惑和猶疑導致自我的不確信,感覺被藥物控制了,糾結于精神藥物副作用和“看醫而不信醫”的矛盾過程中。
3 討論
本研究探討了12位軀體化癥狀患者的就醫體驗,軀體化癥狀患者的病癥體驗及解釋與醫療專業人員,尤其是精神專業人員的診治話語相沖突,這與之前相關研究結果一致[16]。對服用抗抑郁藥物的男性患者研究發現,患者由于活力及男性相關能力損害,經常導致其自主能力與來自醫生“專業指導”之間出現沖突與張力,進而影響對治療的接受程度和滿意度;患者往往對軀體病癥有自己的解釋,患病之前的社會聯結、年齡、對心理疾病的病恥感、個人既往所持的疾病信念等因素都影響患者尋求精神治療的意愿[17]。
本研究發現軀體化患者對心理(精神)性病因解釋心存困惑或不接納。研究發現,患者對于病因的解釋,更多歸因于生物性、環境壓力等[18]。凱博文[1]62-65從更宏觀的社會文化視角發現,人們對于傷病苦痛的歸因包括心理學化、軀體化、超自然化以及政治化等不同類別。軀體化是更為傳統的文化取向的產物,而心理學化是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結果。在現代生活方式不斷演進的過程中,包括中國人在內的軀體化患者私人病癥體驗和認知方式,也深受宏觀的社會文化、價值規范變遷的影響[19]。提醒精神專業人員在干預精神疾患的過程中應該關注患者病癥體驗的不同側面,尤其是文化相關部分。
大部分軀體化患者在嘗試多種干預方法無效后,被動而不情愿地選擇了精神科治療,但對于精神科醫生的解釋和定義,如軀體化機制、性格及環境應激相關的抑郁障礙、焦慮癥等診斷并不真正認可[6,20],患者是因為“有效”而保持了較好的精神治療依從性。少部分患者在與精神專業人員互動后認可了軀體病癥本質是“精神疾病”的論述,改變并重新建構了自己的病癥認知系統。
楊念群[21]在回顧患者關于自我身份建構中談到,“疾病”作為一種隱喻塑造了患者想象自身與世界的方式,使得人的身體成為現代生物醫療話語制造和包裝的結果,而“靈驗決定一切”的實用性效果又強化了這種身份建構,使患者在此基礎上發展出重新解釋和行為干預系統。本研究同樣提示,精神衛生體系用強有力的實踐效果來說服軀體化患者,使其改變既有對健康與疾病的理解或治療行為,接納現代精神醫療術語并整合到自我的認知體系中。
軀體病癥和體驗是受訪者求醫治病經歷的起點,也是其自我疾病信念及解釋系統的來源,對患者的治療選擇及態度有重要意義。從“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角度看,個體所有體驗和認知都是建立在身體感覺基礎上,并且是不斷生成的過程, 是個體通過身體活動參與到世界中去,在與世界交互作用過程中偶合(coupling)而成[22],這種認知及解釋與患者自身經驗自洽,活動的軀體建構個體的生活經驗[23]。本研究同樣提示軀體化患者的病癥體驗和生活經歷塑造了對病痛的解釋,面對精神專業人員告知的、脫離其身體體驗的抽象心理性解釋和分析并不接納,個體病痛體驗與精神專業解釋系統之間的疏遠、分裂造成了不確定性,削弱了患者的自主性。這提示專業人員在與軀體化患者工作中,既要從宏觀層面考慮患者文化背景與價值傳統,也要關注其具體而微的身體感受,對具有堅硬的“身體性”觀念的患者,在解釋與干預過程中要注意尋找合適的切入點,要尊重其體驗和生活經歷,重視患者自身解釋邏輯的“自洽”性,賦予患者自我解釋權利,靈活采用指導性或合作式干預,增加患者的確定感和自主性。
4 結語
本研究遵循同質性原則進行目的性選樣,樣本均為在精神科接受治療的患者,大部分未接受精神醫學干預的軀體化患者可能有別樣的求醫體驗及治療選擇,因此,研究主題有局限性,而結果需要在不同治療選擇樣本中使用不同方法,包括定量研究加以證實。此外,出于方法學考慮,對訪談資料進行分析時,對不同主題重復出現的頻率進行了歸納匯總,難免導致有價值的微小主題或信息因為沒有達到一定比例要求而被忽略或丟失, 因此,沒有得以呈現,研究方法論的局限有待進一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