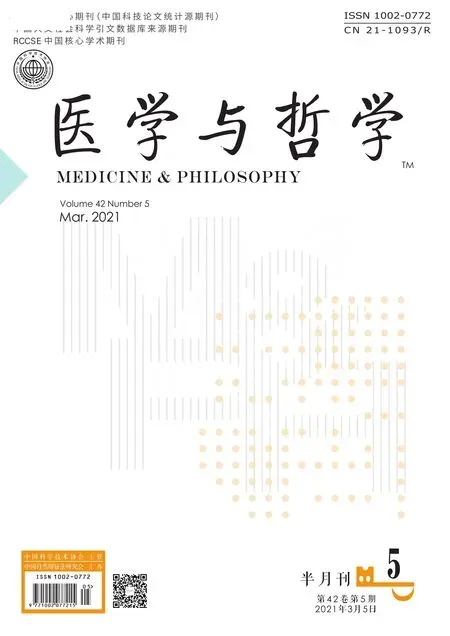醫療漫畫:醫療社會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素材*
賈登紅
19世紀末~20世紀初,漫畫藝術傳入我國,因其具有的詼諧幽默、諷刺隱喻與傳播新知等特點,很快得到普及與傳播,成為一類重要的輿論表達手段。其中,以“醫療”為議題的漫畫作品,又尤具特點,在二維平面用線條勾勒的視覺語言呈現了近代中國繁復的社會生活圖景。它們不僅留存數量可觀,而且還“蘊含了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1],并因漫畫媒介的“跨邊界性”特征,呈現出了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魅力。在既往的醫療社會史研究中,雖對圖像有所關懷,但卻多關注于攝影作品等寫實性的醫療圖像史料,對漫畫這類具有抽象表達特征的視覺圖像關注明顯不足。管窺所見,涉及于此的僅有李培[2]對清末民初報刊醫療漫畫“病夫”現代性隱喻的探討等少數研究成果。
近年來,伴隨著國內外醫療史學界逐漸擴大研究范疇的取向,聚焦于這類曾經被忽視的圖像史料,借助跨學科研究的路徑,不僅有利于拓寬我國醫療社會史的研究范疇,為其提供新的學術增長點,而且有助于我們形象地勾勒出晚清民國時期的醫療視覺閱讀場景,為醫療社會史關涉下的政治、社會文化等課題提供新的詮釋路徑,進而加深我們對這一時段醫療諷刺話語表達與圖像闡釋的理解和認知。基于此,本文試圖將晚清民國時期的醫療漫畫視作漫畫多元主題之一種,挖掘其背后的社會史意義,以期引起學界的重視,豐富醫療社會史研究的面向。
1 作為漫畫主題的“醫療內容”
作為一類圖像媒介,漫畫的優勢在于通俗性與“一圖勝千言”的表意性,相較于其他藝術形式,漫畫的工具性更為突出,表達也更為有力。它宛如一個繩結,將社會生活、經濟文化及大眾觀念等迥然不同的主題纏繞在一起,投射于媒介話語之中,映現了近代中國的時代主題與社會百態。而在這之中,醫療隱喻與敘事始終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議題。
近代以來,“醫療內容”作為漫畫主題的興起,既是漫畫創作者面對晚清民國中西醫對抗沖突、醫療知識亟待普及與社會“病態”叢生等客觀環境刺激下的必然選擇,也是近代中國被蔑稱為“東亞病夫”等話語在漫畫藝術創作領域的自然投射。不過,在既有的漫畫研究中,這類主題往往被湮沒在時事政治、日常生活等類別之下,并未形成氣候,更遑論對其從醫療社會史視角切入的研究與探討了。
當下,隨著醫療社會史研究的興起與拓展,視覺史料日益被激活與利用,醫療漫畫從時事政治等類別下躍出已然是一種水到渠成的行為。具體而言,“醫療內容”作為漫畫的一種主題,在近代中國呈現出了多元的敘事路徑,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剖析,也必然有著不同的理解。在此,若聚焦于醫療社會史的視角,不難發現,醫療漫畫的構圖內容至少應涉及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對疾病本身的呈現與刻畫,多圍繞病態的身體展開敘事;其二,是對治療手段、醫療機構與藥品等“生生之具”的勾畫,以“醫療技術”與“醫療藥物”為構圖基礎元素;其三,是對近代衛生教育隱喻敘事下的醫療科普與啟蒙言說。對此,我們很難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也無需糾纏于定義,秉持以“多研究問題,少下定義”的態度,本文在此重點關注以下三點內容。
1.1 疾病中的“可見”與“不可見”
作為一類被言說的對象,疾病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醫療問題,它有著復雜的社會面相,且因關涉于大眾生命之健康,必然也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對疾病的概念的認識,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社會文化的產物。這就使疾病不僅只是屬于醫生注意的對象,還會引發醫生專業之外的業外人士的關切;也正因為疾病不僅是器質性的,且又是社會文化的,因而在一定意義上說,那些所謂‘外行’的認識,有時反而會顯得更加重要。”[3]如美國學者班凱樂(Carol Benedict)就認為“19世紀末中國有關鼠疫的歷史圖像不單是生物學現象,也是文化現象,充分強調了國家權力全面介入公共衛生事務的必要性”[4]31。
可以說,在每一幅醫療漫畫中,都激蕩著社會與個體“疾病”的回聲。也正是因為這一回聲,借助于漫畫圖像,我們才能更真切地深入與“聆聽”近代中國的社會生活,走進視覺語言與線條符號所搭建的“醫療現場”。對此,我們在研究醫療漫畫時,務必要重視漫畫敘事的“疾病之外”,即它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勾連,要注意對它可見背后的不可見的觀察;要注意到漫畫的創作,必然扎根于一定的文化土壤,富含一定的社會訴求,鑲嵌著時代的表征。
1.2 “生生之具”
藥品與醫院等“生生之具”作為人類對抗疾病的必要手段,“也就是維護生命的方法”,一直在不斷演進。如“中國歷史上的醫家或醫者,大致可按三大階段分作三種類型,上古混同于巫,戰國至李唐通合于道,宋代以下攀援于儒。當然,這是很概括性的分法,但多少可以反映一點不同時代的社會風氣”[5]。延至近代,又凸顯為中西醫之間的碰撞與融合,極大地拓展了“生生之具”的范疇。限于篇幅,在此我們僅從近代醫藥廣告作一論述。
得益于近代繁榮的報刊業,我們可以從大量醫藥漫畫廣告中窺視到晚清民國時期“生生之具”是如何借助于圖像敘事而達到“廣而告之”目的。如圖1[6],是一則民國年間“兒安氏補肺圣藥”廣告,畫面運用太陽、救生圈、溺水的人群等元素,以藥品為視覺中心,襯托以太陽的光芒,顯著地標識了藥品名稱。漫畫中,溺水的人群與救生圈交相呼應,暗示了藥品的“救命”之用,救身圈上所寫的“良藥濟世,功同此圖”更是點題之語。海岸之“堤壩”與圖外的配文,則直白地言明了藥品的功效和商家地址。該廣告可以說饒有趣味,通過對現實社會生活的精妙“構圖”,賦予了藥品極強的說服性。

圖1 “兒安氏補肺圣藥”廣告
1.3 衛生教育
作為一種公共衛生教育方式,醫療漫畫是一種強有力的宣教藝術。在這方面,漫畫家始終進行著各種努力,開拓著與“疾病”的對話空間,概略言之,大致有兩點:一是對疾病本身的介紹,二是對人類各種醫治手段、人與疾病之間關系認知及防疫知識的宣傳。其中,又以第二點為重。這是因為自近代以來,在西醫的傳播過程中,始終夾雜著國人對其的懷疑、恐懼、抵觸與誤解態度,可謂阻礙重重。其時,雖然中國社會已發生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但在醫療知識方面,傳統迷信等觀念仍牢牢地統治著民眾對醫療的態度與認知。對此,有人曾說:“我國鄉村中任何事業均落后,政府對于防疫無有效之組織與設施,人民知識淺陋,對于疫病由細菌傳播之說都不置信,歸諸鬼神天數,聽信巫言,枉費金錢,故疫病一發生,死亡甚眾。”[7]而這些顯然是需要醫療漫畫進行關注與迫切“解答的所在”。
如《疫癥之由來“蒼蠅”》一圖,便是宣教蒼蠅與疫病之間關系的漫畫。畫面中一人正在吃飯,而桌上的飯菜滿布蒼蠅,甚至畫中人的頭頂、身體周遭,乃至剛剛夾出的食物上都有蒼蠅在叮咬。只見他滿頭大汗,張大嘴巴,不知是無法下口還是要發泄什么,暗示了蒼蠅與疫癥傳播之間的關系[8]。這在今人看來是理所當然的知識,但在清末民初,卻尚未被人們普遍的認知與建立聯系。余新忠[4]105對此曾論述道:“概略言之,清人對瘟疫病原的認識主要有鬼神司疫和疫氣致疫兩類。”直至近代西方衛生知識與細菌學說輸入后,蚊蠅等蟲媒介的傳染性才引起一般民眾的注意。
醫療漫畫的表達必然因循其所扎根的社會文化的土壤,而鑒于疾病與社會之間呈現的復雜關聯,醫療漫畫內容也必然不可能局限于以上所論述的三個方面,它還展現出多元的指涉,如醫師形象、公共衛生政策、健康保健、病患等問題,不一而足。這些勢必會極大地擴展我們的研究興趣與范圍,為藝術史、醫療史與社會史的研究提供堅實的資料基礎,為跨學科路徑的開展提供有利的素材。
2 漫畫里的“醫療表達”
正如有學者所論述的“漫畫能否成為史料,不在于它的圖像形式,而在于其類型、形成過程、作者依循的思想路徑和理性原則以及我們所要建構的歷史對象。”[9]作為漫畫之一組成部分的醫療漫畫,其社會史的史料意義亦在于此。我們對它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將醫療作為漫畫圖像來理解,而是試圖通過考察漫畫圖像中的“醫療表達”來加深我們對醫療社會史的理解,窺視漫畫所依托的歷史時期的社會圖景與文化隱喻。要做到這點,就需要研究者對醫療漫畫保持敏銳的感覺,對其層層剝離,循聲覓跡地去挖掘漫畫圖像背后的“不可見”,進而建構起圖像土壤之上的“醫療社會史”。
2.1 知識的傳播與啟蒙
漫畫一經傳入我國,就承擔了傳播知識與啟蒙民眾的功能,而當其與醫療內容碰撞時,又添加了別樣的意義。這是因為醫療雖是專技之學,“但由于涉及人的生活和生命,它的基本理論往往也簡化為人們的日常觀念,塑造一般人的心態”[5],進而也實現了對民眾的啟蒙。
圖2[10]原圖共有12格,囿于篇幅,文內只取每個國家前3格。該漫畫以人腦“解剖”為切入點,通過對日本、俄國、中國三個國家6歲~70歲人腦橫截面 “狀況”的比較,諷刺了國人只知娛樂,求取功名、利祿與享受的思想,最后以致于腦容量越來越小,終至“不可再小”,而日本與俄國人腦中卻裝滿地球,以至“不可再大”。在第一排3個國家民眾6歲~20歲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人的腦解剖圖是科學、軍事,俄國人的是科學、主義,中國人的是連環圖畫,其腦部發育均是“漸大”;第二排20歲~30歲,日本人腦解剖圖呈現的是日本本土及中國的東三省等領土,俄國則是飛機、黨旗、工業與地球,而中國人腦中裝的卻是電影畫報、影院等,日本與俄國是腦部“漸大”,中國則是“更大”;第三排30歲~40歲,中國人的腦部“最大”,裝著畢業證書等,俄國與日本則是“更大”,裝著飛機、軍艦、大炮等;在后續的三排漫畫中,中國的腦部“漸小而尖”“更小而圓”“不可再小”,俄國與日本則“再大”“最大”“不可再大”。作者希冀于通過這樣的漫畫對比,形象地啟迪民眾的智識,激發民眾的進取心,暗示中國若不奮而圖強,則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

圖2 腦的解剖及比較(局部)
2.2 對社會時事的諷刺與隱喻
醫療漫畫諷刺與隱喻功能的實現,一般是通過汲取民眾日常生活中社會文化現象沉淀下來的“幽默與智慧”,將其關涉借用到一些醫療觀念、文化形態與時事政治之中,進而激發起民眾心目中多層次、多向度的觀看意義指涉而達成的,其表現手法多是夸大、借喻,不拘泥于特定的表達界限。就其使用的諷刺與隱喻話語而論,我們可以借用《再造病人》一書中的精彩論述,將醫療漫畫的視覺話語歸納為三點:其一,以身體的病患隱喻“中國的一些風俗習慣的丑陋和低下正影響著中國人的生命狀態”;其二,將“得病的身體作為一種文化的隱喻載體”,通過圖像表征中病態的日益嚴重,“暗喻著中國國土疆界被頻繁侵害”;其三,聚焦時事政治,將“治理社會變成了一種‘醫療’行為”“甚至‘革命’也變成了一種‘治療’隱喻”,進而推動醫療漫畫“變成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主義尋求自衛和發展的一種工具”[11]。
如作于1907年的《中國現狀》一圖,就是對上文第二點隱喻話語的使用。該漫畫以一位男子為構圖人物,只見他頭纏繃帶,左手打著石膏,右手拄拐杖,五官只漏鼻孔和嘴巴,嘴巴大張,似乎在呻吟或訴說什么[12]。漫畫題名“中國現狀”,直白地將漫畫者的意圖表露了出來,呈現了清末中國在列強瓜分下岌岌可危、茍延喘息的社會狀況。這就昭示我們在對此類漫畫進行“閱讀”時,務必要參照社會時事,將醫療漫畫作為社會現象的“視覺體”,在觀看圖像本身話語的同時,窺視到其背后所折射的社會問題與權力關系。
2.3 寫實性的醫療連環漫畫
作為漫畫之一類別的“連環畫”在晚清民國時期也極為盛行,此類漫畫多為一種圖文結合的藝術形式,畫與畫之間具有很強的連續性,一般采用多幅連續的漫畫來敘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圖畫之間有一定的銜接和連貫,沒有明顯的斷裂、脫節和跳躍之感”[13],具有較強的敘事性。聚焦于此類漫畫的研究,能夠讓我們較為完整、系統地認知一個醫療故事或醫療活動。
圖3是由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山西汾陽傳教站所創辦的純英文刊物《汾州》(Fenchow)雜志上的一個連環漫畫的截圖[14]。該圖共有6格,寫實性地記錄了山西省會太原府一位軍隊長官,在兒子不小心摔傷后,驅車一百多公里前往傳教士所建汾陽醫院求醫的故事,暗示了西醫對地域社會醫療生命史的影響與改變。圖下配有文字,詳細地講述了每格的故事與內容,如第一格圖下寫道:“第二天早晨,陽光還沒有落在山尖的積雪上,一輛汽車就在通往汾州的路上飛馳著,太原的兩座寶塔很快就變成了地平線上的斑點。八點鐘的時候,汾州城就出現在他的視線范圍里了。”其中,“兩座寶塔”是指太原地標雙塔寺內的雙塔,而山尖的積雪則表明了天氣和山西的地形地貌。可以說,均很寫實,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為我們提供了地域社會醫療史的“全息影像”。

圖3 前往汾陽求醫
當然,對于此類圖像的解讀和觀看,需要研究者“進入”到圖像創作與傳播的各個階段,對圖像所依存的社會土壤中的語言、制度、形象、行為甚至儀式等有充分的掌握。唯有如此,研究者才能破解漫畫中的“代碼”,進入到附著于漫畫之上的醫療故事,才會為自身的研究奠定扎實的史料依據。
3 結語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索象于圖,索理于書”的傳統,講求對圖像的解讀,闡明其蘊含的意義。近來,醫療圖像史的研究雖日漸勃興,但也存在著對醫療漫畫資料的忽視問題。漫畫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就是大眾公共輿論的歷史,它具有強烈的“證史”功能。對此,我們有必要重視醫療漫畫這一題材,立足于漫畫圖像的本體,從其所處的時代,給予“同情之理解”,看見醫療史可見之外不可見的歷史與社會,進而激發與拓展醫療社會史研究的新領域,為延展多學科的跨領域對話提供一個契機和平臺,同時,也能為后世的醫療漫畫創作提供豐富的素材。
此外,在具體的研究中,我們既要深入醫療漫畫,又要跳出醫療漫畫,“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5]。一方面,我們要深入漫畫中,在圖像的表達與“觀看”之間尋找意義的痕跡,豐富醫療社會史的知識;另一方面又要跳出漫畫看漫畫,看到圖外的人、事、物,乃至國家與世界,以小見大。與此同時,跳出漫畫,也意味著研究者應持有一種“開放之心態”,廣泛吸收跨學科的理論,借鑒學界已有的女性漫畫、政治漫畫等研究路徑,豐富醫療漫畫的社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