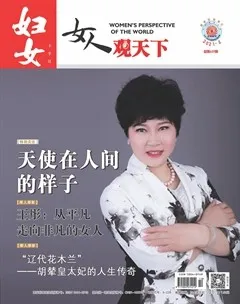“得寸進尺”效應
心理學中有一個“登門檻”效應,也稱為“得寸進尺”效應。一個人一旦接受了他人一個微不足道的要求,為了避免認知上的不協調,或想給他人以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這是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弗里德曼與弗雷瑟從“無壓力屈從——登門檻技術”的現場實驗中提出的。
他們派人隨機訪問一組家庭主婦,要求她們將一個小招牌掛在她們家的窗戶上,這些家庭主婦愉快地同意了。過了一段時間,再次訪問這組家庭主婦,要求將一個不僅大而且不太美觀的招牌放在庭院中,結果有超過半數的家庭主婦同意了。與此同時,派人又隨機訪問另一組家庭主婦,直接提出將不僅大而且不太美觀的招牌放在庭院里,結果只有不足20%的家庭主婦同意。
去年底,我家附近一個新的商業綜合體開張。每天從附近經過,總會遇到身材不錯的年輕人在路邊發宣傳冊,一看就知道是健身房的推廣活動。我們已有另一家健身房的年卡,日常又喜歡戶外跑步,因此每次都禮貌而堅決地拒絕接受宣傳冊,直到那個傍晚。
和家人約好在附近的餐館吃飯,我早到了幾分鐘,站在路邊等。一個小伙子拿著健身房的宣傳冊走過來。我搶在他開口之前,笑著對他擺手:“謝謝,我有健身卡,不用了。”小伙子眉清目秀,也笑著對我說:“我一看就知道姐是經常健身的,身材保持這么好。”
我發誓,我并不是因為這句贊美放棄警惕的。這兩年周圍開過好幾家健身房,我已被這類“糖衣炮彈”轟炸過多次。何況我家確實不必再辦任何健身卡。為預防小伙子繼續向我推銷,我主動告訴他以上實情,他笑著表示理解。
至此,他一句都沒對我提過辦卡,我卻已經接連拒絕了他兩次,心里開始暗暗愧疚。家人還沒到,于是我繼續和他聊天。他告訴我,他是游泳教練。我有些驚訝,他穿著外套,但仍能看出身材清瘦,和以往印象中的健身教練有區別。
“你看著我很瘦是吧?”他聽了我的疑惑,笑著把胳膊伸過來,“你掐一下就知道了。”我猶豫了一下,被好奇心戰勝了,隔著衣服輕輕捏捏他的手臂,全是肌肉。
他讓我猜他有多重,在我報出的估算數字上加了十公斤。接著他告訴我一些其實我早已了解的健身常識,我也順便咨詢了幾個關于游泳的技術問題,他都熱情地解答了。這時家人到了,我向小伙子致謝道別,他提出了一個小小的邀約。他們健身房有一套先進的測試設備,只要站上去一分鐘,就可以得到身體狀況的綜合數據。“測試是完全免費的。”小伙子誠懇地告訴我。
“可我們要去吃飯了……”其實我的遲疑不在于此,“而且剛才告訴過你,我們不可能辦卡的。”“沒關系,辦不辦卡不要緊。”小伙子說,“不瞞姐說,你們進去哪怕不做測試,只是轉一圈,看看我們的環境,也能計入我的業務量呢。”
我還能說什么呢?如果再拒絕這樣一個小小的要求,連我自己的良心都過不去。“姐能留個聯系電話嗎?”接下來,一個又一個小小的要求,就這樣一步步實現。吃過晚飯,我們走進健身房,在小伙子帶領下,參觀了健身房的整體環境,測試了身體狀況,得到了改善訓練的方案,充值辦了家庭年卡,被安排了各自的健身教練,建立了更直接具體的人際連接。
等我們帶著兩張家庭健身年卡,暈暈乎乎離開健身房時,我深刻反思,自己究竟“栽”在哪一步?不該接受小伙子的邀請去捏他的肌肉?不該答應跟小伙子進健身房參觀?不該接受免費的身體綜合測試?不該留下聯系電話?
“其實這些都晚了,第一級門檻應該是小伙子叫的那一聲‘姐’!”我忽然醒悟,“可我怎么能拒絕一個陌生卻眉清目秀的小伙子禮貌地叫我‘姐’呢?”“接下來,就看你能不能守住底線,堅決不買私教課了。”家人調侃我,“畢竟你一向很節儉。”
昨天我又去上私教課,教練安排我練臀。練臀需要大重量,每組都練到我力竭。
“教練,為什么每組動作你從一數到十以后,就開始五、四、三、二、一倒著數?”喘息的間隙里我問教練。
“讓你知道快結束了,你就能咬牙堅持到底了。”教練告訴我。
“為什么你開始跟我說這組動作練三次,練著練著變成了四次?”我又問。
“一開始嚇到你,你就不肯練了呀。”教練笑著說。
為什么我們要學一點心理學?因為生活中處處都是心理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