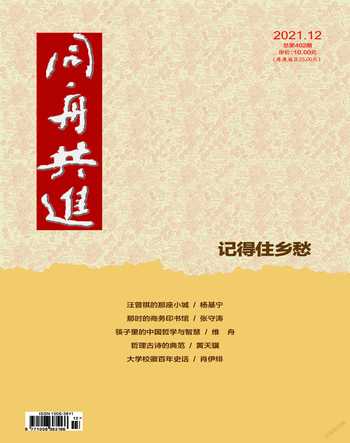“將軍本色是詩人”
散木
1961年4月,著名詞人及詞學家、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夏承燾先生從杭州赴北京出席教育部召開的高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據事后夏承燾的日記,他與陳毅在會上有過一番談話:
晨九時方欲下電梯,得陳毅副總理秘書來電話,云陳副總理欲邀予與郭老、錢、馬諸君敘談,因告郭老諸君,候汽車來迓。不料十時許予方解衣據案寫家片(家信),服務員來報副總理來。去年文代會聽其報告,風采如舊。謂讀過予所著《唐宋詞人年譜》諸書。遍詢予四人年齡,自謂今年六十,在此不能稱老大哥。予聞其所作詩詞,謙謂新舊雜糅,時時在改乙中。因縱談最近在日內瓦作盧騷(盧梭)湖各詩;笑法國代表不讀書;謂在日內瓦、巴黎買盧騷全集不得;謂盧騷回歸自然之語,由聞法國傳教士誦陶潛復得返自然之詩而來;謂政治由業務表現,學校必須重視業務,每日必有六小時工夫學業務……縱談至十二時去,謂昨陪巴西古拉特副總統來滬,在京時于北京晚報所載消息知予等四人在此,百忙中抽暇來訪,明日即離滬,將來有新著新詩幸相示云云。
當時夏承燾、郭紹虞、錢仲聯、馬茂元等學者正在上海科學會堂出席古典作品選討論會,陳毅從《北京晚報》上得知此四人恰在上海開會,遂利用接待外賓的機會與眾人聚談。陳毅在會見夏承燾等人時的這一段話,迄今不曾見諸其它文字,但內容十分豐富和珍貴,如他自評其詩詞創作特別是在出席日內瓦會議時所作之作品、笑談西方談判代表之窘態、縱談盧梭文學及其來源等,均顯示出陳毅元帥的風貌以及其時中央開展調整工作的方針和原則等。
三年之后,1964年12月,夏承燾先生專程赴北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會議期間,他與眾人余暇時討論詩詞寫作,討論毛澤東、陳毅等共和國領袖的詩作。
毛澤東和陳毅都是共和國領袖中著名的詩家,當時也都有作品問世,特別是毛主席的詩詞,自此前1957年元月在《詩刊》創刊號上發表了18首詩詞之后,成為中國詩詞界最大的熱門。及至翌年即1958年7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詩詞十九首》,在《詩刊》發表的18首詩詞之外,又增加了他在1957年新填的《蝶戀花·答李淑一》。隨即1959年文物出版社在此基礎之上,另增加了毛主席新發表的《七律·送瘟神》(二首),出版了線裝本的《毛主席詩詞二十一首》。至1963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又以線裝宣紙本、毛邊紙本、平裝甲種本、平裝乙種本等四種形式出版了收錄有毛主席37首詩詞的《毛主席詩詞》。一時間,毛主席詩詞大熱,而“注家”也行動起來,特別是夏承燾先生這樣的詩詞研究大家,更是關注備至,傾注了極大的心力。
至于陳毅,素有“一代儒將”“元帥詩人”之美譽,無論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還是在縱橫捭闔的外交場合,他往往揮筆書寫瑰麗詩篇,抒發豪情壯志,從未輟斷,而自1957年1月新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詩歌雜志《詩刊》誕生后,他便在多種場合甚至外事活動的間隙,不僅予以過問,而且徑直提出意見,還將自己的作品交給《詩刊》發表,以示支持。他的這些作品也迅速在讀者中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如《贈郭沫若同志》《莫干山七首》等,“將軍本色是詩人”,博得了眾多讀者的喜好。
1959年4月,全國政協及人大召開會議,陳毅聽說借此次文藝界人士來京開會之機,“詩刊社”在南河沿文化俱樂部召開詩歌座談會,陳毅當即表示自己也要與會,并在開會時謙遜地一再請別人先發言,隨后以一位詩人的身份談了一些關于詩詞創作的看法,如議及詩詞創作的藝術表現,他用了一個形象的說法:“三分人才七分裝”,即須注意表現形式,他希望大家都來“勤學苦練”,即“無論新老作家,都要從基本練習入手”等;在討論到如何評價“五四”以來詩歌的創作時,陳毅既充分肯定了“五四”以來新詩的成績,但又認為其“反映革命,反映得還不夠;反映生活,反映得還不夠”,至于其流弊,則是“重視外國的,輕視中國的;重視古人,輕視今人”。在談到詩的用韻時,陳毅以為“詩的平仄和用韻是自然的,廢不了的。打破舊時的平仄,要有新的平仄;打破舊時的韻,要有新的韻。我不同意反對平仄和用韻。詩要通順流暢。有韻的,注意了流暢的,朗誦起來效果就好些。形式問題,可以幾種并舉,各做實驗”。所謂“舊瓶裝新酒”,陳毅主張詩詞創作可以不廢舊的形式。此外,他特別反對庸俗地理解和欣賞詩詞,并以毛主席的詩歌為例,他說:
藝術就是藝術,寫詩就是寫詩。上海有人在毛主席詩中尋找戰略思想,就有些穿鑿附會。毛主席詩詞有重大政治意義,但還是詩。有人問毛主席:“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是不是超過了歷代所有的人?”毛主席回答:“作詩就是作詩,不要那么去解釋。‘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兩句,完全是說,這支軍隊得救了,將要勝利到達陜北了。”
不久后的1962年,為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0周年,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曾舉行了一個詩歌座談會,陳毅又在會上有所主張,并現身說法:
寫詩要寫使人家容易看懂,有思想,有感情,使人樂于誦讀。
我寫詩,就想在中國的舊體詩和新詩中各取其長,棄其所短,使自己所寫的詩能有些進步。
后來毛主席在《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中表述了相同的看法:
又詩要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
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蠟。
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
1964年12月21日,夏承燾參加政協會議的教育界小組座談會,隨即列席人大第三屆大會,“再見到毛主席”,是夜,他竟“夕夢與毛主席論詞,甚奇”。翌日,夏承燾列席人大會議之后,又與陳毅有一番難得的聚會,并聆聽了陳毅的又一番詩論。夏承燾在日記中寫道:

七時夕餐后上樓,小方同志見告,陳毅副總理來看予,頃在馬湛翁(即馬一浮)房,八時會于小客廳,自六一年夏間見于上海國際飯店后四年矣。問郭、錢、馬(即郭紹虞、錢仲聯、馬茂元)近況,尚了了不忘。云已見予《龍川詞箋》,謂少予一歲,今年六十三矣。
予問毛主席詩詞,謂早年在軍中見其作品約百首左右,今僅存廿余首,殆久已忘之。主席好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好蘇(軾)、辛(棄疾),亦好秦(觀)、周(邦彥)詞,不喜夢窗(吳文英)、草窗(周密),不主純用白描,好象征性。嘗聞其在馬上誦“飛絮落花時節怯登樓”,亦時哼“酒趁哀弦,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諸句。主席自謂少時不為新詩,老矣無興學,覺舊詩詞表現感情較親切,新詩于民族感情不甚合腔,且形式無定,不易記,不易誦。
陳(副)總理謂早年亦曾為新詩,后好為舊詩詞,曾問郭老能背自作新詩否,郭曰不能。又謂公事稍閑,必讀唐宋詩詞,數十年不廢。
主席少時古典文學工夫深,詩文詞能背誦者多,書法尤其素好,今尚以此自娛,大草好臨懷素。予問是否懷素《自敘》?曰然,尤多臨懷素之《秋興》八首。予自喜億(臆)中。
又問(副)總理所作革命詞,謂約有百首左右,當抄出請教于方家。當時以腹腿負傷甚重,不能隨軍長征,留在江西大庾山中,聯系地下工作,被蔣軍、日軍圍困,嘗一度絕糧,又不能舉火,摘楊梅及蛇充饑,故所為望江南詞有“三月過,肉味不曾嘗,烹蛇二更長”之句。地民不得送糧,只能于衣袖中裝少許炒米相饋。予問“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句何時作,謂當時只二衛士共生死(其一今已當將軍),互約如被困當拼死數人,決不作俘虜。幸深山草盛,有時只隔數十步,卒未被發現。其后轉入敵后,得人民群眾力,日本鬼子變成瞎子,便甚便當。因念文天祥在江西全無群眾,故數日即被俘。解放軍與群眾是骨肉之親,當時作詩有“你是恩情親父母,我是戰斗好兒郎”之句,當時惟聞長征軍西上不利消息,甚為憂慮。
……
談作新詞,謂須往農村與老農同生活,自能得到許多書本上得不到的學問。

不久后的30日,夏承燾又記錄了陳毅的一段談話:
午陳毅同志招宴于政協禮堂第三會議室,馬一浮、熊十力、沈尹默、褚保權夫婦、平杰三(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傅抱石同席。
與尹默初識,其雙目幾失明,出所書詞數首與陳,自謂于詞為外行,陳謂內行不出,亦成外行。此謔語亦有意。
陳又謂川劇有《滿江紅》等詞,不知與詞樂有關否。以詞體反映新現實,有生命力,嚴四聲則無意義。
又談及榆生,嫌其胸襟不大,囑予與熊翁勸其多多出行,看看新社會,不必死鉆宋詞。
一時宴散,與馬、熊兩翁同車歸,陳于兩翁亦有莫“抬扛”之謔,兩翁不以為忤。
上述陳毅的講話,涉及詩詞創作、古今詩詞的評論(特別是對毛主席詩詞的評論),以及自己的一些詩詞的寫作背景,還有對幾位詞家的關懷(沈尹默、龍榆生),可謂親切有加、光風霽月。值得一說的是,夏承燾不僅與陳毅有詩詞之交,他還通過陳毅多方了解了毛主席的詩詞創作之源和詩論,后來他還與主席秘書胡喬木談論過毛主席的詩詞。
夏承燾的這些日記,為我們了解共和國領袖們的“文學側面”,提供了珍貴史料。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