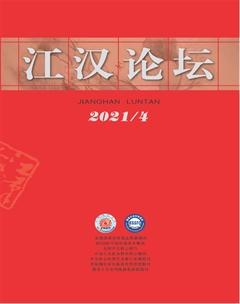虛擬文化空間場景維度及評價研究
陳波 彭心睿



摘要:移動互聯網及物聯網時代,網絡虛擬空間環境不僅拓展了文化空間的內涵,也改變了傳統的文化參與方式,虛擬文化空間的重要性得到極大突顯,其運行特征及場景設計亟待研究。以場景理論為依據,通過設計“在場性”、“體驗性”和“合法性”三大主維度及十八個子維度,可以構建針對虛擬文化空間場景問題的分析框架。運用這一框架對于新冠疫情期間的“云游博物館”進行案例研究,可以發現數字媒介平臺是影響虛擬文化空間中博物館場景變化的關鍵因素,從而證實人們處在不同虛擬場域所感受的社會氛圍及文化內涵差異顯著。
關鍵詞:虛擬文化空間;場景;云游博物館;云展覽
中圖分類號:G250.73?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21)04-0134-11
文化參與不僅是公民文化權利的基礎性內容,也是個體與所在空間產生精神關聯的有效方式。通過文化參與,個體與所處空間及空間中的社會網絡發生連接,進而產生歸屬感、認同感乃至共同價值觀等。文化參與作為一種行為活動,必以明確的時間信息和空間環境為前提條件。在移動互聯網及物聯網時代,網絡虛擬空間環境不僅拓展了文化空間的內涵,也改變了傳統的文化參與方式,使個體文化需求發生重大轉向,越來越多的文化參與行為轉移至以數字化文化設施為基礎的虛擬文化空間。2020年上半年在特定約束條件下,我國居民的文化參與空前依賴于虛擬文化空間,使其成為緩解個體緊張、焦慮等負面情緒的主要渠道。我國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在暫停實體場館開放的同時,也積極以數字化方式持續為廣大公眾提供公共文化服務,虛擬文化空間的重要性得到極大突顯,其運行特征及場景設計亟待更多理論支撐。
一、國內外相關研究梳理
虛擬文化空間研究主要從虛擬空間(賽博或網絡空間)研究中分化發展而來。陳波、陳立豪對國內外“虛擬空間”的概念作了梳理,主要有“虛擬現實技術意義上的虛擬空間”、“在網絡科技基礎上形成的互聯網空間”和“虛擬社會層面的虛擬空間”三個層面,第一層是基于VR技術的微觀理解,第二層和第三層則是宏觀廣義的理解,但區別在于“前者重空間的技術屬性、后者重空間的社會屬性”①。虛擬文化空間的研究則是基于第三層含義展開的,關注網絡空間中由新技術與社會網絡相融合而產生的精神文化空間。
(一)虛擬空間的場景研究
目前虛擬空間的場景研究大致包括三種主流方向。一是基于VR等新技術形成的微觀空間視角的場景研究,該視角聚焦的是微觀VR場景的設計和技術應用問題。二是基于信息技術發展出的媒介場景(situation)、技術場景(context)或應用場景(application scenario)研究。該視角關注的“場景”主要有關網絡的信息傳播、技術功能與人們各類需求的適配問題,相關文獻集中于新聞傳播、計算機、信息管理等領域。三是基于市場目標人群分析的服務場景(servicescapes)或消費場景研究,該“場景”關注社會性要素與空間消費行為之間的關系,相關文獻集中于經濟管理、市場營銷等領域。
媒介場景理論由約書亞·梅羅維茨提出,該“場景”已非實體空間概念,而指由傳播渠道所創造的社會信息環境,且新的媒介帶來了新的信息系統、改變了人們的社會行為②。技術或應用場景重點關注人們的生活在“場景五力”(數據、移動設備、社交媒體、傳感器、定位系統)作用下發生的重大變革③。此視域的研究實則也將“場景”視為一種信息環境,區別在于聚焦技術的發展及應用問題。而Bitner提出的“服務場景”是“服務業依靠人而建立起來的一種有形環境”,強調消費行為不僅受物理環境影響,還與社會環境密切相關④。之后該理論被不斷深化,重在研究影響消費行為的情感氛圍,分析社會要素和象征要素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Harris & Goode將實體環境中的服務場景概念引入虛擬空間,提出在線服務場景及其維度劃分,從審美訴求、功能布局、財務安全三個維度分析網絡消費行為⑤。
以上三類虛擬空間場景研究對人的行為和心理分析都有所涉及,但多以技術或功能為標尺來分析衡量人及人類社會,呈現技術本位傾向。盡管部分研究以精神需求為邏輯起點,但主要仍為實用意義上的功能性分類,并未涉及精神文化及審美層面的細分。然而在科技推動下,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已難分上下,人類社會可能終將進入“數字化生存”⑥ 狀態,數字形態的虛擬空間建構起人類活動的另一平行世界,將日益成為一個全方位的生活場域,而非僅僅以商業為主導的消費平臺。這樣,以獲取經濟效益為首要目標的服務場景理論,盡管關注人群心理分析,但落腳點集中于消費行為,其適用范圍就顯得十分有限。
目前,三大理論性的場景研究也逐漸出現互為借鑒、融合發展的趨勢。如喻國明、梁爽通過綜合傳播學、營銷學等領域的“場景”研究,提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場景”是“社會與個人雙重作用下的被建立環境”,將“場景”類型按界面形式分為“現實性場景、虛擬性場景、現實增強場景”;按功能分為“實用性功能場景、社會性功能場景”⑦。不過,其“社會性功能場景”的維度只是依據馬斯諾需求層次作了粗略功能劃分(社交、尊重、自我實現)。夏蜀通過梳理綜合三個不同層面“場景”的概念,提出數字時代的“場景”是“物質空間與信息空間通過數字技術進行相互連接、切換與融合,進而實現人—機—物互動交流的場域”,以“人、物品、時空環境、文化與情感、數字生態”為“場景”的五要素,以“智慧連接、社群文化和大數據”為“場景”賦能的三個維度,試圖構建“數字化時代場景主義”⑧。然而該研究一是對“場景”的界定過于宏觀,基于其定義的“場景”似乎與“虛擬空間”的內涵較為重疊而難以區分;二是研究立足于商業領域市場分析的視角,在文化方面實際僅關注網絡社群,如其所述是“商業邏輯的場景主義”。
可見,目前關于虛擬空間“場景”研究的遺憾之處在于并未深入關注虛擬世界中人們社會生活的精神文化層面,難以對人們在某一虛擬場域中的社會文化環境有較全面的把握,也未能描繪出虛擬文化空間中的文化氛圍與審美體驗。不過夏蜀的研究已關注到“新芝加哥學派”的場景理論,其間接暗示著虛擬空間的“場景”也可以是精神文化層面的,具有復雜多元的文化內涵。故本文探討的“場景”問題是文化及審美視角的,國內部分研究也稱“文化場景”。
(二)文化空間場景及其維度研究
文化空間場景研究是以Terry Clark、Daniel Silver等為代表的“新芝加哥學派”于本世紀初所建立的場景理論(scenescapes)⑨。該理論認為“場景”是某一地方(place)的整體文化風格或美學特征,一個空間場景并非表現某種單一的意義,而是多重意義的復雜組合。場景理論通過借鑒社會思想理論中的三大經典主題——格奧爾格·齊美爾關于“真實性”、歐文·戈夫曼關于“戲劇性”和馬克斯·韋伯關于“合法性”的論述——創新提出了具有普適性的文化價值分析框架。該理論試圖構建一張“文化元素周期表”,其中的“文化元素”則是來源于文化與藝術研究中一些關鍵性的審美特征,共有三大主維度和十五個子維度。具體到不同場景的分析則運用“舒適物”(amenities)的概念,通過對各類舒適物在各個維度的賦值計算,分析舒適物的組合方式,從而揭示出其不僅具有實用功能,還通過嵌入不同的“文化元素”而組成不同場景,傳遞著不同的文化價值。近十年來,文化場景理論受到國內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與應用,并結合中國社會的特點嘗試融合創新。具體到文化空間場景的維度設計方面,國內部分學者在場景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如傅才武、侯雪言將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場景設計為物理空間、活動空間、機制空間三大主維度,并于各維度下提出了新的次維度⑩。陳波基于場景理論對城市街區公共文化空間的維度進行了設計,主要分為實體空間、機制空間兩個主維度及八個次維度{11}。
上述研究的重要貢獻在于,一是提出了對空間文化內涵進行解構與描述的一套新理論框架及分析模式,可應用于觀察分析不同空間的文化意義與組合方式,進而研究場景維度變化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影響。二是對城市文化空間、農村公共文化空間、街區等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場景研究與維度設計,為不同類型或不同區域范圍的具體空間場景提供了理論指導。但國內外學者關于文化場景及其維度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物理空間領域,還未見論及虛擬文化空間場景及其維度的研究。
二、虛擬文化空間場景及維度
數字時代正在重塑人們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經驗。與以往源于物理空間的生活經驗相比,網絡不僅改寫了“位置”和“空間”的內涵,也顛覆了人的身體對存在環境的認識。在討論虛擬文化空間場景問題之時,實則隱含一個假設,即虛擬文化空間同樣存在不同場景。當人們走到不同實體空間,會感受到不同精神氛圍和審美體驗,而人們也察覺到經由網絡進入某一虛擬場域時,不同虛擬空間聚集了不同的人群,如中學生熱衷于QQ,大學生集中于微信、微博,而中老年群體不僅產生“微信熱”且自我呈現顯得比較理性與保守{12}。這些差異反映出不同的網絡空間位置可能具有不同的文化氛圍。那么不僅物理形態的空間具有不同文化場景、傳遞著不同的審美趣味或文化觀念,虛擬形態的空間也可能存在同樣的現象。故本文的研究對象——虛擬文化空間場景,是虛擬空間中社會網絡某位置的整體文化審美風格及特征。場景理論將真實性、戲劇性和合法性作為三大主要的綜合價值分類,而虛擬文化空間的本質特征則要求一種新的文化價值分類框架及與之適合的維度。
(一)虛擬文化空間場景主維度
首先,簡單以真實與否來衡量評判虛擬世界的種種現象已不再妥當。人類關于“真實性”的理解本是基于物理實體的環境。虛擬世界是對物理世界符號的再現和表征,數字技術使各種符號獲得了更加強大的生命力,跨越更廣泛的時間和空間,觸及更多的人群。在虛擬世界,人們所感知的是符號和形象編織的世界。目前的社會實踐中,大量數字文化產品的設計和生產已將“在場感”(或“臨場感”、“沉浸感”等)置于突出而重要的位置,在技術上成為一項不可或缺的評估要素。但問題在于何為“在場”?
“在場”本身即為哲學中的一個復雜而重要概念,本質上與存在相關。事物在場與否不應簡單等同于物理世界中的位置存在關系和時間存在關系。盡管在物理世界人可以直觀感知某物,但距離與時間客觀上都是可被無限放大與縮小的。多近是為近,多遠才為遠,什么距離或時間范圍才是劃分在場與不在場的界限呢?如果說在物理空間觀察一物,距離五十米和距離五米會有差異,或與放大鏡顯微鏡觀察相比更是截然不同,那么何種距離才謂之真正“在場”?迄今為止我們無法劃定某一距離范圍而斷言超出該范圍則事物不在場,故物理上的距離概念便難以成為判斷在場與否的客觀標準。時間范疇上亦是如此,我們同樣無法劃定某一具體時間范圍而明確界定只有在此范圍內觀察的事物才是在場的。隨著虛擬世界的擴張,界定何為在場更為復雜。例如一處物理空間在場的文化遺址,被人們所直觀感知時,出于保護目的一般須保持一定距離,或觀察視角受限,以致難以看清細節,只能通過他人解釋來獲取其中的信息,人與物實際上并非通常認為的直接而無中介的接觸,這是否必定意味著真實的在場?而數字技術按照高精度三維復制的文化遺址,通過設備與人直接相連接,人們在訪問時實現了一種穿越時空的“虛擬在場”,擁有更多視角、了解更多細節,得到的信息超越物理空間之所感知。“虛擬在場”顯得比物理在場更為“真實”,且隨著技術不斷突破,這種情況將更為頻繁地出現。海德格爾曾提出“上手狀態”是作為工具之事物的存在方式{13}。根據海德格爾的理論,“事物的在場也就是事物的被使用,而當事物無法被使用時,它就不在場”{14}。由數字技術呈現的虛擬形象也應理解為一種對事物的使用,只是人類社會技術進步帶來了利用手段又一次質的突破。一方面,是否“在場”不大能以某一絕對化的物理標準去界定;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使事物的“上手狀態”突破了原本的時空局限,最終通過其虛擬形象實現自身的“在場”。
其次,受數字科技的影響,社會經濟發展逐漸步入新的階段,體驗經濟及注意力經濟日益成為主導形態。在互聯網經濟領域,體驗性成為一大重要特性,網絡已是人們生活中重要的體驗場所。“體驗”究竟是什么?“體驗并不是實證數據,也不是由原子、電磁波、蛋白質或數字組成”,體驗是主觀意識的,有的觀點會將其細分為感覺、情感和想法等,“但事實上一切都是交織在一起的”{15}。在虛擬世界中體驗感被強化,數字時代的互聯網經濟也“不再基于產品上的物質性,甚至也不是技術中的功能性,而在于能給消費者帶來體驗的精神層面”{16}。社會實踐領域已經將激發人們的心理體驗作為產品的重要價值。人們也不再執著于對物質實體的占用和私有,而更在意是否擁有豐富多彩的精神體驗,這些體驗往往是在物理世界難以獲得或無法獲得的。同時,社交媒體的產生和發展為人們自我展示提供了全新的平臺,帶來更加自由而個性鮮明的自我體驗和社交體驗。因而“體驗性”成為虛擬文化空間的一個核心社會文化內涵。
場景理論提出的“合法性”是關于“如何判定孰是孰非”,包括價值取向、道德倫理、是非判斷等方面。一方面,盡管網絡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然而人們對生存意義和人生價值的理解和追求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本質,生活空間形態的變化并不能阻擋人對價值追求的腳步。另一方面,眾多學者已經關注到,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系列新技術給當代社會帶來極大的倫理風險。這些新技術不僅重塑社會網絡關系,也給人類社會已有的價值觀念帶來沖擊;不僅考驗著個體的倫理道德意識,也對社會治理及精神文化建設提出巨大挑戰。因此,虛擬文化空間場景不僅與物理文化空間一樣可以具有“合法性”意義,且虛擬文化空間場景“合法性”值得研究者重視,并以更為審慎的態度對待。人們可以依據不同的標準作出是非和價值判斷。場景理論基于人類物理世界過往經驗總結出若干主要權威類型,如“傳統”、“領袖魅力”(克里斯瑪)、“功利主義”、“平等主義”等。而在價值取向越來越多元化的今天,受到新技術的沖擊,定義合法性的權威也有了新的來源。
(二)虛擬文化空間場景子維度
以上三大主維度僅是針對虛擬文化空間場景分析所構建的一級框架,這一寬泛的分類顯然不足以支撐更深層的討論,我們還需進一步結合虛擬文化空間的特性進行更具體的意義分類,尋找到各主維度下合適的子維度。
1.“在場性”子維度
“在場性”可進一步區分出主體在場和客體在場兩個不同視角。主體是進入虛擬文化空間的人。在網絡中,盡管某種意義上人們的身體不在場,但感官意識是在場的,故主體在場關涉的是自我意識的存在,指主體通過置身于某種環境而確認自我的在場,或是自我存在的感知和自我身份的意識。從主體在場感受內容來分析,“本土”、“族群”、“國家”{17} 是有關主體存在及自我認知的基礎維度,是從古至今形成身份認同的根本力量。而進入現代社會,消費主義盛行。鮑德里亞揭示與批判了“消費社會”的本質,即人們在消費中獲得某種符號認同,消費行為變成了個人身份的編碼行為{18}。“品牌”已成為一種消費社會重要的象征符號,與個體的身份意識緊密相連,越來越具有左右人們定義自我的能力。在以符號編織而成的虛擬文化空間中,“品牌”不再作為傳統企業組織的專屬品,它可以是企業品牌,也可包括個人品牌、工作團體(工作室)品牌、活動品牌、文化品牌(文化IP)等等。此外,主體在場感受內容還具有兩類不同特征:一類是源于知覺、感覺、情緒、情感等方面,另一類則是來自知識、見識、智力、能力等方面。由此可將“智識——情感”作為第五個子維度,關注符號文本所營造的是偏向嚴肅、客觀、理性的智識環境,還是偏向輕松、感性、敘事性強的情感共鳴。
客體在場亦可分兩類:一是自身的在場,二是形象的在場。虛擬世界可謂一個純符號世界,不存在現有哲學意義上事物真實自身的在場,那么虛擬文化空間中的在場基本可視為符號和形象的在場。鮑德里亞把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人類社會以“擬像”的概念劃分為三個階段,而我們所處的當代社會被其歸納為第三階段——“仿真”,這一階段由代碼主導,建立在信息、模型、控制論基礎上,是完全可操作的、超現實的(hyperreal){19}。形象發展到最高階段,已不必再與現實有關,而可以是形象自身的擬像{20}。“仿真”形象不必是現實的鏡像或機械復制,它是現實事物以外的新“事物”,這種由數字技術制造出的新形象不需與現實對應,它非真非假,模糊了現實與想象虛構的邊界,可以將人類頭腦中的想象變為一種“現實”,即鮑德里亞所說的“超現實”,它是運用數字技術對物質現實的重構。如根據專業知識與模型算法對文化遺產進行的數字化修復或重建,最后所呈現的即為數字化仿真形象,它并非真實的,因為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該事物百年千年前真實的原貌,但又難以將其判定為虛假的。數字化的仿真形象只是我們將頭腦中的科學想象變為了非物質性的“超現實”。可見“超現實”是虛擬文化空間中關于“在場性”至關重要的子維度。與之相對是物理現實的鏡像或機械復制(包括二維和三維)。
2.“體驗性”子維度
各類網絡平臺已成為以展示和交流為主導的大眾文化空間,其不斷編織而成的社會網絡關系具有高密度、多對多的網狀結構特征。社交媒體大大提升了信息的傳播速率,而注意力成為數字時代的重要資源,對注意力的爭取則強調不同尋常的特質。“迷人”和“越軌”{21} 作為極易吸引他者觀察和注意的行為風格,在虛擬文化空間中更易被察覺,且“越軌”可用來標識網絡上越來越廣泛而多元的非主流內容。
從網絡社交體驗來看,“體驗性”還可分為至少以下四個子維度:“禮節”“開放”“互動”和“社群”。公眾在網絡中話語自由程度大大超越了現實生活,但并不意味著網絡社交雜亂無章,不同的平臺為用戶設定了不同社交模式,養成了新的社交行為禮節或規范,如發帖規范、“刷禮物”、“三連”、彈幕守則等不同行為表示特定意義。“開放”則關注個體自我展示的開放程度,是否支持和鼓勵更公開、更外向的個人展現,促使個體吸引更多注意力;相對的則是封閉或半封閉的、有所保留的,即通過訪問設置等技術手段避免或降低他人注意力,以保持低關注度。“互動”用來標識用戶分享及互動行為,特別是文化內容生產與用戶之間互動行為直接相關;與之相對則是無需互動交流的、無意分享的,乃至自我獨白式的。“社群”或“網絡社群”特征的強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維度。Howard Rh-eingold將“網絡社群”定義為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接觸或沒有接觸過的人利用網絡媒介進行交流與對話而產生的網絡社會群聚現象。網絡社群成員的交流不必面對面,但屏幕上的內容也完全有能力使人大笑或流淚、喚起憤怒或同情,共同話題就是地址{22}。網絡社群純粹以共同的興趣和話題為連接,即使參與者互不相識、結構松散,實際上卻是長期存在、持續活動的,并且相比現實世界中的社群體驗需要耗費較高的精力和時間成本,網絡社群的社會壁壘和技術壁壘都大幅降低。
3.“合法性”子維度
盡管網絡改變了生活空間形態,但其難以動搖人類社會基本的或普遍的價值追求,如“傳統”“平等主義”“功利主義”“領袖魅力”和“自我表達”{23}。虛擬文化空間中,公眾逐漸從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轉變為文化內容的設計和生產者,從而賦能個體的自我表達。一些網絡平臺還積極支持原創、獨特、自發、個性化、定制等內容。網絡也大大推動了信息、意見、觀點的廣泛自由流動,使得具有特殊魅力和影響力的新人群不斷涌現。網絡達人、網紅大V、流量號等各類自媒體已成為影響人們價值判斷的強大力量,個人魅力的影響力不再局限于傳統領袖人物,更多的“個體魅力”在虛擬文化空間中得到凸顯。
然而,人類社會科技的重大突破常常伴隨出現新價值觀念的沖擊,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Yuval Harari明確將“數據主義(Dataism)”視為自1789年法國大革命后“第一個真正創造新價值觀的運動”,數據幾乎被視為全知全能的。與人文主義的重視個人、崇尚個體價值相對,數據主義將個人變成“巨大系統里的微小芯片”。如果我們將人類在過去歷史長河中存儲積累起的經驗也比喻為算法的話,人腦算法或許只是“初級算法”,且似乎已到達極限,大數據、機器學習和神經網絡等技術不斷產生海量的數據和新的強大算法及運算能力。過去的人文主義呼吁“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而數據主義則崇尚“聆聽算法的意見”,“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轉向以數據為中心的世界觀”{24}。通過記錄、上傳、分享、互動、評論等,個體成為“信息流”或“數據流”的一部分,“數據至上”、“流量為王”等價值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尤其在經濟領域成為價值判斷的主導。
基于以上三個主維度和18個子維度,可構建出虛擬文化空間場景分析框架(表1)。應說明的是,這一框架并非完全解釋框架。正如場景理論多次強調的,場景科學最初的主要目標不在于提取一些維度對場景的內涵作出完全概括,而是在于找到一個合理的綜合分類框架作為切入點及分析工具,對富有符號意義、抽象而復雜的空間場景進行具有科學性的比較研究,使關于文化意義的傳統定性研究可以轉化為具有實證性的量化研究。誠然,這些意義維度分類的邊界可能會存在一定模糊性,但它們之間的差異也是清晰可辨的。
三、案例研究:疫情期間“云游博物館”場景分析及評價
新冠疫情期間,“云游博物館”成為一大熱門的線上文化活動,不僅形成較大的規模,影響范圍也越來越廣泛。“云游博物館”是當下虛擬文化空間中博物館活動的集中體現,其涉及的文化機構、數字媒體、活動形式及內容廣泛而多樣,不以經濟價值為主要目標導向,是較為合適且有重要研究價值的案例。
(一)“云游博物館”的出現
通過百度對“云游博物館”一詞進行主題詞檢索,以2020年1月23日(關閉離漢通道日期)為節點的檢索結果表明,在23日之前未見與主題詞符合的信息。23日之后檢索結果顯示,首次出現與主題詞吻合的內容為1月28日《沈陽日報》的新聞,稱“云游沈陽博物館”的方式得到微博網友肯定。1月30日,江蘇省《新華日報》的一則新聞《宅在家中“云游”博物館》在標題中正式使用了該詞。通過與微博信息檢索結果相參照,使用該詞的大致時間基本吻合。可見,“云游博物館”是誕生于新冠疫情期間的新名詞,大致于2月中旬得到普遍使用并逐漸為人們所熟知。“云游博物館”借用了互聯網領域“云端”的概念,字面意義即通過網絡“云端”參觀游覽博物館。概括其具體內涵則是以數字媒介為載體,組織和利用博物館文化資源,面向廣大公眾,在網絡虛擬空間中開展的文化活動,活動形式包括虛擬展廳、數字展覽、網絡直播、視頻、圖文等。
(二)“云游博物館”場景維度分析
“云游博物館”作為線上系列文化活動,實際上參與舉辦的主體包括全國性數字媒體、地方性媒體、各類公共文化機構等數百家機構。通過對2020年2—6月“云游博物館”活動的持續跟蹤,評價對象篩選考慮了媒介載體、熱門度、知名度、媒體用戶數量、活動內容多樣性以及活動資源可回顧性等多方面的因素。最終確定10個具體項目作為本次研究的評價對象,共涉及6類媒介平臺、6家文博機構:“云游故宮”(Web端)、“云游敦煌”(微信小程序)、“在家云游博物館”(抖音App)的“敦煌研究院”和“中國國家博物館”抖音號、“云游博物館”(微博各端口) 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山西博物院”官微、“國云展”(新華社移動端)的“故宮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專欄、“博物館云春游”(淘寶App)的“敦煌研究院旗艦店”和甘肅省博物館專場直播間。
本次評價根據場景理論“評估者手冊”中物理舒適物的評分流程{25},結合虛擬文化空間場景維度,重新設計評估問題,邀請10位業內專家進行獨立評價。評價過程中,需依次瀏覽評價對象、體驗活動內容,參照評估問題,沿用原理論中量表對評價對象在各個維度的表現以1—5分賦值(1和2表示活動排斥該維度;3表示中立;4和5表示支持強化)。評分表回收后,確認有效應答專家7位,綜合7份評分表計算平均分及變異系數。向專家反饋第一輪評分情況并進行第二輪評分協商確認后,得到最終評價結果(表2)。
觀察十項活動在18個維度的評分情況發現:
1. 存在一致強化的維度
十項活動在本土、族群、品牌、傳統、平等五個維度分值均高于3,一致表現為強化,表明在虛擬文化空間中,文博機構開展的活動主要立足于本土文化和民族特色。在場性方面,顯著的本土、族群和品牌特征實際上與文博機構自身的文化資源密切相關,如敦煌和故宮的文化資源優勢在三個維度上得到明顯體現。同時文博機構在合法性上,普遍體現出顯著的傳統色彩,在秉持平等主義這一原則方面也表現頗為一致,總體上與文博機構作為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自我定位并未發生沖突,與其所強調的主要社會功能也大致符合。
2. 存在一致排斥的維度
各“云游博物館”活動在越軌維度分值均低于3,一致排斥該維度。可見,即便在虛擬文化空間中,文博機構同樣一致地維持著主流文化的傳承者與傳播者的角色。而以新華社移動端為媒介平臺開展的“國云展”,越軌分值不僅是該維度的最低值,也是各項活動所有維度的最低值,可見傳統主流媒體存在加深排斥程度的可能性。
3. 數字媒介平臺影響場景維度表現
通過對比敦煌在不同媒介平臺開展的云游項目,我們發現在原有實體舒適物相同(均為敦煌莫高窟)的條件下,媒介平臺不同,場景差異顯著。三者在任一維度均未見分值相同或極為近似(<0.2)的情況,反而多達八個維度表現為顯著不一致(圖1)。
同時,我們提取出四組對比分析組,每組均由三個項目組成,其中一、二項原有實體舒適物相同、媒介平臺不同,二、三項媒介平臺相同、原有實體舒適物不同。通過比較每組的三項活動在各維度分值變化幅度,記錄平臺之間變化(“媒介1—1”與“媒介2—1”分值變化幅度)大于舒適物之間變化(“媒介2—1”與“媒介2—2”分值變化幅度)的情況。經統計,三組以上(含三組)均呈現上述情況的維度達10個:超現實、迷人、越軌、開放、互動、社群、傳統、功利、自我表達、數據。為進一步排除各項目都具有共性的維度,通過逐一分析各維度、計算每一維度中最高分與最低分之差發現,相差小于兩個量級(<2)的維度共四個:迷人(2.57—3.86)、越軌(1.43—2.71)、傳統(3.57—4.71)、數據(2—3.71)。如前所述,由于十個項目在四個維度大多存在一致性,可暫且將這些維度移出本次觀察范圍。經對比余下六個維度發現,媒介平臺不同表現出的差異均大于由舒適物不同而帶來的差異(圖2)。此外,合法性中的數據主義維度表現為強化的有六個項目,分屬三大數字媒介平臺(抖音、微博、淘寶),其性質皆為社交性媒體,表明該維度上數字媒介平臺聚類明顯。
不僅敦煌云游項目在三大不同平臺的表現差異較大,四個對比組分析結果也顯示媒介平臺因素可以影響的維度占到至少三分之一,且社交性媒體平臺活動數據主義維度表現一致強化。可見,媒介平臺成為影響博物館場景變化的關鍵因素。原實體舒適物相同,媒介平臺不同,整體文化風格可呈現較大差異;而不同的實體舒適物,處于相同的媒介平臺,不少維度表現反而更為接近。
(三)“云游博物館”場景評價
經專家評分及計算分析,我們可運用18個維度對不同項目給人們帶來的文化體驗作出詳細描述與評價,識別出它們之間的差異及各自特點,進而嘗試對“云游博物館”場景進行整體概括。
1.“云游博物館”項目評價
十個項目中,小程序“云游敦煌”占據六個維度最高分值,分別是本土、族群、國家、超現實、迷人、自我表達。六個維度不僅均為正面支持,且幾乎都高于4(除迷人分值為3.86,接近4),表明“云游敦煌”積極強化這六個方面的特征。其中,本土性分值最高(同時是十項所有維度的最高值),表明該項目極其強烈地體現著本土文化風格。十項中,僅“云游敦煌”在超現實和自我表達兩個維度超過4,且與最低值相距跨越兩個量級(>2)。超現實維度的表現主要取決于數字技術的運用,而自我表達維度則關系到活動是否鼓勵參與體驗者的自我表達意識,支持個人創意、個性化表達等內容。實踐中,“云游敦煌”一是在文化資源的數字采集與利用方面,運用數據資源積極嘗試“視覺重構”{26};二是通過動畫劇配音、壁畫填色、絲巾定制等活動內容,使體驗者可按自身想法及偏好取舍,給予參與體驗者一定自我表達空間。因此,“云游敦煌”場景表現可描述為體現強烈本土文化、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具有良好文化品牌效應,呈現超越物理現實的形象特點,展現風格趨于華美,傳承弘揚傳統價值觀念,保持平等主義,鼓勵參與者的自我表達及個人創意。
網頁版“云游故宮”在國家、品牌、智識、傳統四個維度上分值在十項中排于首位,其中傳統維度分值最高(同時是十項所有維度的最高值)。在本次評價中,超現實和迷人兩個維度雖僅次于“云游敦煌”但分值接近。并且,十個項目中僅有“云游敦煌”與“云游故宮”在超現實維度表現為強化,這進一步表明了兩大文博機構多年來在文化資源數字化建設方面取得的顯著成績。總體上“云游故宮”在十個項目中也表現突出,與“云游敦煌”相比主要差異在于自我表達方面。
微博的國家博物館云游項目在開放、互動、社群、個體魅力四個維度分值最高,且均達到4分。開放、互動、社群皆為體驗性方面的子維度,主要用于標識不同的網絡社交體驗。個體魅力雖屬于合法性方面,實則也與社交媒體有密切聯系。國家博物館官方微博自1月24日起便開設了“國博邀您云看展”話題,相比于“云游敦煌”、“云游故宮”等其他項目,其場景主要特點在于體驗性方面,尤其是社交體驗表現突出,而這些維度也與數字媒介平臺本身的功能、特點及優勢密不可分。
淘寶的兩個云游項目均在越軌和功利兩個維度分值最高。盡管十項云游活動皆排斥越軌維度,但淘寶越軌分值最接近中立。相比越軌,功利維度不僅分值顯著高于其他項目,且是本次評價中唯一超過4分的,表明淘寶兩項云游活動體現了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經部分專家反饋,實際直播活動中一些場次文創產品的推介時間占比超過了文化遺產本身的導覽。
抖音云游活動在各個維度表現較為平均,其分值基本介于3至4之間。類似情況還有新華社“國云展”,但其一半以上維度均為排斥,特別是體驗性方面整體呈現消極。
2.“云游博物館”與實體博物館場景之異同
本文從前人研究中提取了美國博物館評分數據{27}和國內博物館評分數據{28},與“云游博物館”十個項目評分結果進行對比(圖3)。通過觀察原本基于物理文化空間的實體博物館在進入虛擬文化空間后場景的轉變情況,發現三者主要存在以下異同點,即無論文化空間形態如何、無論中國還是美國,博物館場景都一致強化傳統維度,且我國博物館場景無論空間形態如何皆一致強化本土、族群、國家、和平等四個維度,一致排斥越軌維度。而美國博物館在這些維度表現中立。之所以如此和兩國文化體制密切相關。博物館在我國是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美國多為非政府主導的獨立運營機構。
虛擬文化空間的“云游博物館”與實體博物館場景顯著差異則表現在兩大方面。一是企業/品牌、迷人、功利三個維度分值顯著高于實體博物館。博物館本身的機構性質,無論國內外皆屬非盈利機構,故在這些維度表現消極;然而進入虛擬文化空間后,其企業性(品牌性)、展現度和功利性顯著增強。一方面由于脫離了物質實體,博物館的文化IP成為核心資源。實體館是以文物或藏品原件之“光韻”為核心資源,本質上將膜拜價值置于首要地位;但進入虛擬文化空間后,原件的缺場及其“光韻”的褪去,不僅使得核心資源轉化為以原件符號意義為基礎打造而成的品牌符號資源,還造成文物藏品資源的展示價值全面超越甚至取代了膜拜價值{29},而數字技術也恰恰使資源的復制、展示與傳播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另一方面,由于數字媒介平臺的介入,這些數字媒體皆為企業性質,不僅自身已具備很好的品牌價值和廣泛的用戶群體,還提供了強大的展示與傳播技術支持,因而也難免造成功利色彩的增強。
二是與國內實體館相比,“云游博物館”在理性/智識維度的表現分值顯著下降,從積極強化轉為中立乃至排斥。相反的趨勢則發生在越軌維度,除新華社“國云展”保持強烈排斥,其余活動上升趨勢明顯,個別項目接近中立值。這兩個維度的變化也印證了我國博物館的社會形象轉變的發展歷程,即從最初精英文化的珍寶庫轉變為具有公共性的知識殿堂,再到當下強調為社會大眾服務的文化機構。而在進入虛擬文化空間后,博物館場景驗證了學者此前的一些觀點,即博物館呈現出兩類視覺內容。一種是遵循實體館舊有的傳統形象——自上而下式的知識權威機構,展示內容是“以在線展覽或虛擬展廳形式出現的有序的形象表征”,“強調連續性、智性與審美”;另一種則是跟隨大眾文化浪潮而產生的新形象——服務大眾的文化休閑機構,重視激發觀眾感官體驗和情感共鳴,展示內容“簡化成了各個形象本身,形象之間并不具有嚴密的承繼關系”,“強調體驗、片斷、即時所見”{30}。
綜合上述分析,“云游博物館”場景整體表現可概括為在場性顯著,體驗性中等,合法性一致突出傳統維度。其中,在場性表現主要取決于文博機構自身文化資源優勢,多為實體事物的鏡像復制。體驗性表現目前主要依賴于社交媒體的平臺優勢。合法性多個子維度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主要視不同數字媒介平臺情況而定。原場景理論分析中,博物館在合法性維度權重為正值,被列為合法性維度的代表性舒適物之一{31}。中、美博物館的專家評分數據也在合法性方面多數維度分值基本一致。然而虛擬文化空間中的“云游博物館”不再同實體館相一致。如排除專家評分結果偏差之巨大,則意味著博物館場景空間轉換后合法性在四個維度上出現大范圍波動。博物館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陣地之一,從世界范圍看也是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與弘揚的重要機構,如何順利實現從物理世界到虛擬世界的空間場景轉換,且不違背博物館本身的功能定位與價值追求,或將成為未來的重要課題。
本次案例研究也存在一些有待改進的地方,如樣本僅限于文博類機構,類型及數量不夠豐富,且分析論證主要基于專家評分數據,結論客觀性需加強等。
四、結語及建議
基于虛擬文化空間場景維度分析與案例研究,我們發現數字媒介平臺是影響虛擬文化空間博物館場景變化的關鍵因素,并且通過運用場景分析框架證實了人們在通過網絡實現文化參與的過程中,處在不同虛擬場域普遍感受到的社會氛圍及文化內涵也不同。虛擬文化空間中的場景不再主要由原實體舒適物自身的文化特質而決定。同一實體舒適物經過資源數字化、載入不同虛擬位置后,其場景不僅難以同原來保持一致,反而可受數字媒介因素影響表現出明顯差異,甚至可能呈現相對立的審美傾向。通過“云游博物館”案例分析,我們還觀察到合法性方面表現波動較大的現象,而合法性的定位關系到今后虛擬文化空間建設導向及質量。物理空間原有的文化舒適物進入虛擬空間后場景的轉換是未來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
隨著個體對虛擬文化空間的需求與日俱增,人們將更為頻繁地利用網絡實現自身文化參與權利。虛擬文化空間場景與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密切相關,根據本文的分析結果,針對原基于實體場館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建議在進入虛擬文化空間時應至少關注以下方面。一是詳細了解和掌握不同數字媒介平臺的功能及特征,在平臺選擇時應根據功能定位、傳播目標與用戶人群特點深入研判。二是對進入虛擬文化空間的場景進行明確規劃及整體設計,尤其在合法性方面需要審慎處理,避免自身理想的合法性表現被數字媒介平臺特征所沖淡甚至消弭,規避陷入自相矛盾的風險。三是鑒于社交體驗作為吸引廣泛文化參與的重要因素,體驗性方面可適當增強對相關維度的重視。最后,本文構建的文化價值框架目前主要作為一種分析框架,如遇到具體文化項目場景實踐問題,并非鼓勵實踐中追求維度表現的多而全,維度正負分值也無絕對化褒貶之義,本文在案例評價中也試圖避免這一導向。我們更多地希望并建議,在項目實踐中根據自身實際與目標找到合適維度及表現,營造滿足人民多元需求而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場景。
注釋:
① 陳波、陳立豪:《虛擬文化空間下數字文化產業模式創新研究》,《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② 參考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參考羅伯特·斯考伯、謝爾·伊斯雷爾:《即將到來的場景時代》,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
④ M. J. Bitner, Servicescapes: The Impact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 on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2, 56, pp.57-71.
⑤ L. C. Harris, M. H. Goode, Online Servicescapes, trust, and Purchase Intentions,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2010, 24(213), pp.230-243.
⑥ 參見尼古拉·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電子工業出版社2017年版。
⑦ 喻國明、梁爽:《移動互聯時代:場景的凸顯及其價值分析》,《當代傳播》2017年第1期。
⑧{16} 夏蜀:《數字化時代的場景主義》,《文化縱橫》2019年第5期。
⑨ Daniel Silver, Terry Clark, Scenescapes: How Qualities of Place Shape Soci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⑩ 傅才武、侯雪言:《當代中國農村公共文化空間的解釋維度與場景設計》,《藝術百家》2016年第6期。
{11} 陳波:《基于場景理論的城市街區公共文化空間維度分析》,《江漢論壇》2019年第12期。
{12} 黃含韻:《社交媒體年齡層用戶差異顯著》,《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6月15日。
{13}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81頁。
{14} 董明來:《符號與在場性: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的分歧》,《中外文化與文論》2011年第1期。
{15}{24} Yuval Harari, 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7, p.107, pp.390-397.
{17} 場景理論中提出Locality、Ethnicity、State三個維度,并將其作為空間場景“真實性”的子維度。
{18} 參考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19} 此處綜合了鮑德里亞先后于兩部著述中有關“擬像”理論的論述,他提出文藝復興后的“擬像秩序(the orders of simulacra)”有三個階段,其中對第三階段“仿真”(simulacra of simulation)闡述為:“founded on information, the model, the cybernetic game”,“total operationality, hyperreality, aim of total control”(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121),“is controlled by the code” (Jean Baudrillard,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p.81)。
{20} 鮑德里亞將形象(image)的發展演變分為四個階段,大致為反映現實、掩蓋現實、掩蓋現實的缺失和與現實無關(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6)。
{21} 場景理論中提出的“迷人(Glamour)”指閃耀華麗富有魅力的,通常與時尚潮流聯系在一起,相對是普通的日常的;“越軌(Transgression)”指反常規、摒棄主流的,相對則是主流的、常規的甚至教條式的。
{22} Howard Rheingold, Virtual Communities-Exchanging Ideas Through Computer Bulletin Boards, Journal of Virtual Worlds Research, 2008, 1(1), pp.1-5.
{23} 場景理論中提出的“傳統(Tradition)”是基于過去歷史文化的固有價值判斷,源于并遵循過去的傳統或歷史先賢典范,與之相對則是反傳統的;“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崇尚人人平等,遵照普遍的、互惠的標準尊重所有人,相對則是特殊化的、特權化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將利益作為合法性來源及價值判斷的標準,相對則是非功利的;“領袖魅力(Charisma)”本是源于韋伯所關注的政治和信仰領袖,場景理論將其范圍擴大至名人名流,相對則是去個人化的、依慣例的或程序化的;“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指合法性來源于自身,實際上意味著信仰自我,相信自己獨立價值判斷,相對則是主張遵循既定的、趨同的或反自我意識的。
{25}{31} 丹尼爾·西爾、特里·克拉克:《場景:空間品質如何塑造社會生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373—379、112頁。
{26} 參見劉派:《視覺重構——文化遺產的數字化重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27} Daniel Silver, Terry Clark, Online Appendix for Scenescapes: How Qualities of Place Shape Social Life. 注:該文檔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網絡出版的電子資源。
{28} 陳波、林馨雨:《中國城市文化場景的模式與特征分析——基于31個城市文化舒適物的實證研究》,《中國軟科學》2020年第11期。
{29} 參考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國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
{30} 殷曼楟:《從中國數字博物館觀眾經驗看用戶交互之路徑》,《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簡介:陳波,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72;彭心睿,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2。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