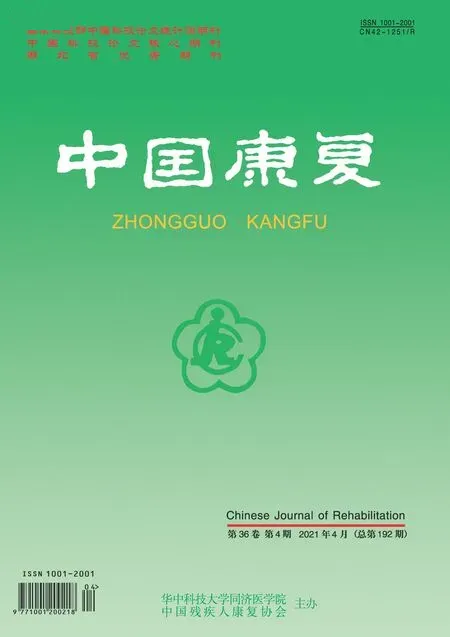原發性震顫患者的平衡功能及相關因素分析
徐從英,王琰萍,吳華,沈宇斐,張曉玲,竺卓穎,吳曉強
原發性震顫(essential tremor,ET)是一種具有遺傳傾向的運動障礙性疾病,發病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整個人群發病率0.9%左右,但是大于60歲人群發病率可以達到2.3%~14.3 %[1],既往多認為ET單純只是一種運動障礙性疾病,但是現在認為,ET同樣存在認知、精神癥狀、感覺異常[2],還存在步態和平衡困難[3-4],共濟失調[5]。盡管這個問題大多數時候影響不大,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很嚴重,并且影響運動功能[5]。究其原因不是特別清楚,但被認為可能是小腦功能障礙所致[6]。對臨床癥狀的充分研究和認識,有助于更準確地診斷和更好地治療患者,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生活質量。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年6月~2019年12月在嘉興學院附屬第二醫院門診就診的ET患者(研究組)和健康志愿者(對照組)各80例,ET符合2009年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運動障礙及帕金森病學組提出的原發性震顫的診斷標準[7]。入組患者均有肢體或/和頭部震顫,生命體征均穩定,意識清楚,可服從指導;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有關節病變或既往有肢體功能障礙的;②排除可能有影響平衡功能的眼部疾病的;③最近一個月有服用安定類或者最近一年之內有服用其它抗精神病性藥物(苯巴比妥、氯硝西泮、地西泮、加巴噴丁、撲米酮等)可能會影響步態和平衡的;④有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的;⑤嚴重心肝肺等基礎疾病的;⑥有認知功能障礙或者其他原因不合作的。一般人口學和臨床資料的收集:收集患者的一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發病年齡、病程、生化分析、甲狀腺功能、血銅藍蛋白、血常規、現病史、飲酒史、既往史、家族史等。臨床問卷為自行設計問卷,包括一般情況、疾病發展、震顫特點(包括飲酒后癥狀變化、既往病史、個人史、神經系統疾病家族史、既往服用藥物與治療效果。2組患者生化分析、甲狀腺功能均未見明顯異常,2組患者年齡、性別、教育程度、銅藍蛋白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有可比性,見表1。
1.2 評定標準 對2組患者采用以下評估方法。急性評估表格中:采用六項平衡信心活動量表(Activities of Balance Confidence,ABC-6)評估患者的平衡信心[8-9],要求參與者在保持平衡或穩定的情況下評估他們在進行以下6項活動中的平衡或穩定的信心(0 分表示完全沒有信心,100分表示完全有信心。最終分數(范圍=0~100),是6個評分的平均值,使用ABC-6量表評估自己在完善以下6項任務時保持穩定的平衡信心,具體包括:①踮起腳伸手拿東西;②站在椅子上伸手拿東西;③在擁擠的人行道上與人相撞;④上或下自動扶梯時扶住欄桿;⑤上或下自動扶梯時不扶欄桿;⑥在結冰的人行道上行走。采用Berg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評估患者步態和平衡功能, 共14個分項,每個分項最高分4分,最低分0分,總分最高分56分,最低分0分,分數越高平衡能力越強,0~20分,提示平衡功能差,患者需要乘坐輪椅;21~40分,提示有一定平衡能力,患者可在輔助下步行;41~56分者說明平衡功能較好,患者可獨立步行,<40分提示有跌倒的危險[10];另外,還收集患者過去的一年中跌倒次數(不包括由于猛烈打擊或者由于肢體無力導致的跌倒)及幾近跌倒的次數。既往安定類藥物種類是指以下藥物(阿普唑侖、舒樂安定、勞拉西泮、氯硝西泮、地西泮、咪唑安定)等;既往抗精神病藥物史是指既往使用以下藥物(奧氮平、氯丙嗪、奮乃靜、舒必利、氯氮平、利培酮、喹硫平)等;采用簡明心理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量表評估患者認知功能。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14項版本評定患者的焦慮程度。按照我國量表協作組提供的資料:總分≥29分,可能為嚴重焦慮; ≥21分,肯定有明顯焦慮; ≥14分,肯定有焦慮;超過7分,可能有焦慮;如小于7分,便沒有焦慮癥狀。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項版本評定患者的抑郁程度[11]。按照我國量表協作組提供的資料:總分≥35分,可能為重度抑郁;21~35分為中度抑郁,8~20分為輕度抑郁; <8分為無抑郁。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采用改良Barthel指數(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共10項,每項0~15分不等,總分100分,<60分為不能自理。

2 結果
2.1 2組之間步態平衡情況比較 研究組ABC-6量表評分明顯較對照組低(P<0.01)。研究組BBS評分總分明顯低于對照組 (P<0.01);研究組在過去一年中跌倒的次數超過對照組 (P<0.01),幾近跌倒的次數也超過對照組(P<0.01);見表2。2組患者MMSE評分、焦慮和抑郁評分、既往服用可能會影響步態和平衡的藥物種類如安定類或者其它抗精神病性藥物上相差不大,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研究組MBI評分較健康組低(P<0.01),見表3。

表1 2組患者一般情況比較

表2 2組患者各項評定結果比較

表3 2組患者MMSE、HAMA、HAMD、MBI評分比較分,
2.2 影響ABC-6評分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由表4可見,ABC-6評分作為應變量,年齡、組別、病程、家族史、發病年齡等作為自變量做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變量采用逐步納入法,結果提示,年齡及組別為患者ABC-6評分的影響因素,見表4。

表4 對影響患者ABC-6評分的多因素回歸分析
3 討論
研究組患者比對照組表現出更多的平衡和步態障礙,這種障礙會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關于ET平衡和步態障礙的機制,目前還未完全明確,對ET病理基礎的研究提示神經通路中連接小腦和丘腦及小腦和大腦皮層的纖維有參與,磁共振和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顯像提示研究組存在著小腦退行性改變[12-13]。浦肯野細胞(Purkinje cell,PC)是從小腦皮質發出的唯一能夠傳出沖動的神經元,尸檢結果提示,ET患者存在小腦浦肯野纖維的丟失,樹突棘細胞腫脹,樹突分枝減少,樹突棘密度降低;軸突增厚,軸突分枝發芽,小腦皮質病變等[14]。一些研究者已經提出[14],ET可能是“浦肯野細胞疾病”。來自死后對照研究的數據支持這種觀點,這些研究顯示:①PC軸突有一定程度的形態變化;②PC位置和方向異常;③一些研究發現PC數量減少;④PC樹突狀分支存在形態變化和減少,伴樹突小棘喪失;⑤在ET病例中,PC界面和PC攀爬纖維界面均發生變化。這種新的提法引起了一些爭議,并引發了其他問題。盡管初步研究表明,ET中可能存在不同的變化特征,但仍需確定在ET中觀察到的系列變化是否不同于在其他小腦變性疾病中觀察到的系列變化。
Louis ED等[15]學者對190例ET患者未受影響的一級親屬和對照組進行了平衡功能比較,結果發現ET患者未受影響的一級親屬在過去一年中跌倒較對照組多,在戶外結冰的人行道上行走時平衡信心下降更加明顯。因此,他們認為:ET患者小腦功能障礙的發生率比以前設想的可能更普遍,這種障礙不僅僅在ET患者自身會出現,在其未受到影響的親屬中同樣會出現。通過對相關文獻進行Meta分析,Rao 等[16]發現ET患者同樣存在步速慢、步幅短、步基寬等特點,因此,他們認為ET患者的上述特點類似于脊髓小腦性共濟失調。
本研究顯示,年齡為患者ABC-6評分的影響因素,隨著年齡的增長,ET患者的平衡功能也逐漸在下降,研究組ABC-6評分(74.5±12.4),高于Louis等[4]的研究結果,他們研究組ABC-6平均得分為(59.7±27.7),本研究的評分相對較高,可能與我們選取的病例年齡(66.5±6.7)較他們選取的(75.7±8.3)小有關。Rao 等[16]的分析的結果也顯示,ET患者平衡和步態功能障礙與患者年齡有關。同大多數研究一樣[3-4,17],本研究并沒有發現平衡功能和病程有關。上述研究結果均提示,ET患者平衡和步態功能障礙非常普遍。認知功能下降會導致判斷失誤,影響患者的平衡功能,導致既往跌倒次數增多[18],我們入選的患者認知功能相差不大,未能進一步評估認知因素對評定結果及對步態本身的的影響,對ET患者的平衡功能評估可能有所欠缺;但是正是由于本研究的患者認知功能相差不大,才在病史可靠性方面得到保證,尤其是在回憶過去一年中跌倒及幾近跌倒的次數等容易遺忘的病史方面。情緒因素(抑郁和/或焦慮)會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影響患者的平衡功能,同時,既往的口服安眠藥物及抗精神病藥物對平衡功能也有影響,本研究中2組患者焦慮和抑郁評分及既往口服藥物無統計學差異,避免了情緒及藥物因素對平衡功能及平衡信心評定結果的影響。
由于平衡功能障礙,導致ET患者協調性差,因此在一系列執行功能性任務(如從椅子上坐起來、床椅轉移、從地上撿東西、雙足交替踏等)等方面表現差,導致患者不光減少功能性活動,還會不自覺地減少體力活動,導致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從而導致更加嚴重的平衡問題。本研究中,研究組BBS評分較對照組差,ABC-6評分也較對照組差,提示患者平衡信心及平衡能力均有下降,跌倒及幾近跌倒的幾率也大于對照組,與文獻報道相符[4]。Ulanowski等[19]報道,一名接受腦深部電刺激的61歲的ET患者接受了14場個性化康復訓練,其中包括平衡訓練和運動功能訓練,訓練后的結果表明,患者的平衡和運動功能均有改善。上述結果提示,我們在關注ET患者震顫的同時,還應該加強對患者平衡功能的評估,尤其是年齡大的患者,可以指導患者加強平衡功能訓練,將BBS評分中的功能性任務貫穿到患者的日常功能性訓練中,以避免患者平衡信心下降,避免跌倒,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ET患者步態和平衡功能障礙會影響患者執行功能,增加跌倒風險,這個發現具有潛在的臨床意義。首先,對ET的認識不應該只局限于震顫,我們應該考慮對ET患者進行平衡功能的評估,并且這種評估是否應成為臨床實踐常規的一部分,而不是僅限于實驗室研究的環境。其次,我們需要考慮對ET患者進行平衡功能及步態訓練(即康復治療),觀察通過康復鍛煉之后,ET患者的平衡功能、平衡信心及靈活性是否可以得到改善。第三,目前現有的許多改善ET震顫的藥物是抗驚厥藥,新的ET藥物的臨床試驗應該在關注藥物療效的同時,還應該評估這些藥物對步態及平衡功能的影響。
本研究優勢在于通過多個量表評估患者的平衡功能,評估比較全面客觀;其次,我們還分析了既往一年中跌倒和幾近跌倒的相關指標,這些指標可能更能體現患者平時健康狀況;最后,我們的病例來自于門診,平衡功能受既往治療的影響較小。但本研究也有局限性,我們評估了可能影響ET平衡功能有關的藥物,但藥物劑量不同對平衡功能的影響可能會有所不同,我們沒有進一步深入研究。另外,患者既往使用的藥物中,除了抗驚厥藥物及安眠藥物之外,可能還有其它藥物對平衡功能有影響,本研究也沒有深入統計分析。今后可能可以通過擴大樣本量,詳細記錄患者用于治療ET的抗驚厥藥物和安眠藥藥物種類及劑量,評估患者的認知功能和情緒因素,在允許條件下,結合功能磁共振進一步研究患者平衡功能的特點,指導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