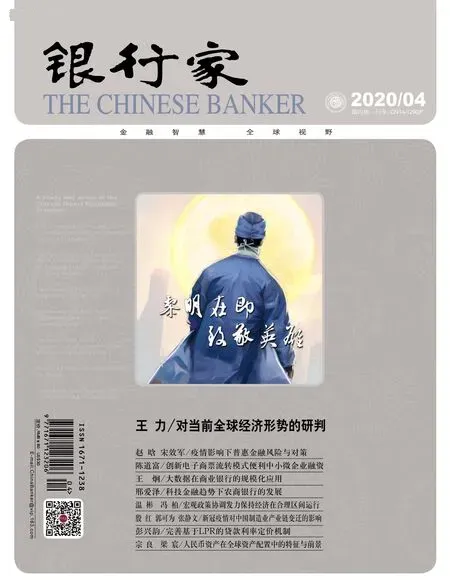新興市場國家跨境資本流動風險防范實踐
朱斌 王興華



基于麥克杜格爾模型對資本流動福利分析的精妙,2008年之前IMF等組織都傾向于鼓勵各國讓資本自由流動,不贊成對資本流動進行限制。但金融危機后,IMF發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鼓勵各國以應對系統性風險為主構建宏觀審慎監管體系。一方面,危機后的新興國家在應對資本流動風險中采取了多種措施,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國際教訓應該吸取;另一方面,中國在經歷2014年開始的一輪資本流出過程中,于2019年8月6日被美國列入匯率操縱國的金融制裁,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鵝”襲來過程中,外匯管理部門從實踐的角度在如何應對資本流動風險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顯著成效,經驗值得總結。通過對國際教訓及中國經驗的總結,將有助于更好地管理資本流動風險。
國際教訓:新興市場國家總體措施與危機案例
總體措施:宏觀審慎與資本管制并重
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將資本自由流動作為重要目標,同時也采取資本管制措施。金融危機后各國都加強了對本國資本流動的控制,更加重視以宏觀審慎管理的方式加強監管,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同時,通過直接限制交易降低外部資本對金融穩定的影響,也成為資本流動管理的做法。
從宏觀審慎角度來看,選擇宏觀審慎監管工具的國家逐漸增多并形成一定的監管共識,即針對系統性風險積累來使用。而資本稅、無息存款準備金是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先后有泰國、俄羅斯、印尼等國對流入境內的外方資金收取20%~50%不等的無息存款準備金;巴西、泰國、韓國等國先后采用資本稅的方式調控流入資本。其中,巴西的管理方式較為直接,采用收取資本流入稅的方式,2008年收取資本流入稅稅率由1.5%、3%調整為6%;泰國和韓國的稅收方式不一樣,2010年前后泰國、韓國等多針對外資購買的本國債券利息以及資本利得預征收15%左右的預扣稅。可以看出,盡管范疇上一致,但每個國家都是結合自身的跨境資金流動特征、資本項目開放階段和金融市場成熟度來設計審慎監管工具的。
從資本管制的角度來看,“資本流動管理措施”成為新動向。正如2016年IMF在《資本流動自由化與管理:機構觀點》中指出,“資本流動管理措施”包括資本管制及其他一些基于幣種區分的限制措施,認為對于防范破壞性的資本流出風險具有顯著作用,實際上是將資本管制放到與宏觀審慎監管并列的位置。實踐中,直接“叫停”某項交易成為許多國家都在采用的措施。如印度、阿根廷、冰島、烏克蘭等國限制的內容可以是交易品種、境外存放、轉移境外等多種環節,這些資本管制措施值得借鑒(見表1)。
危機案例:土耳其——運用宏觀審慎管理仍爆發貨幣危機的典型
危機背景
2008年土耳其出現經濟過熱征兆,短期資本大規模流入導致國內信貸高速增長,本幣里拉升值明顯。2011年土耳其根據宏觀審慎的理念,采用了利率走廊和準備金選擇機制來為資本流入降溫。2018年該國出現貨幣危機,貶值38%;2019年貶值幅度達12.81%。
具體措施
利率走廊。利率走廊指中央銀行通過操作對商業銀行提供的借、貸款利率區間來控制貨幣市場利率波動范圍。當資本流入時,央行通過下調隔夜借款利率,擴大利率走廊下限,降低短期資金交易的吸引力;反之,提高走廊上限。如2013年底美聯儲開始宣布退出量化寬松政策(QE)時,土耳其短期資本流出壓力增大,2014年初土耳其央行將隔夜存款利率由3.5%提高至8%。
準備金選擇機制。準備金選擇機制(Reserve Option Mechanism,ROM)指中央銀行規定商業銀行能以一定的轉換標準自主選擇在存款準備金中持有一定比例的外匯。資本大量流入時提高比例,可使更多的資金以存款準備金的形式儲存在土耳其中央銀行,退出市場流通,緩解本幣升值壓力;反之則降低比例。
基于周期性、結構性與體制性因素的分析
土耳其使用利率走廊和準備金選擇機制后,里拉匯率呈現出平穩波動的狀態。但自2018年開始,里拉匯率仍然出現了大幅度貶值,貨幣危機一直持續到現在,而且還遠遠沒有結束,在土耳其國內影響巨大。想要結束貨幣危機,就要分析其產生的根源,從源頭上遏制危機的蔓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的:“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前的金融風險是經濟金融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和體制性因素疊加共振的必然后果。”這一論斷為分析土耳其貨幣危機的產生原因提供了思路。
首先,基于周期性因素分析,利率走廊代表的經濟進入下降周期未反映在匯率上,里拉積累的貶值壓力容易在外部環境變化下集中爆發。利率走廊實際上在2017年就已經飛升,但匯率在一段時間內的表現較為平穩,因此在2018年里拉崩潰之前未出現劇烈的貶值。直到2018年7月26日,美國政府準備將對土耳其鋼、鋁產品關稅提高一倍,分別達到20%和50%。8月10日,里拉突然在一天之內貶值20%,資本隨之外逃。其次,基于結構性因素分析,土耳其的外匯流入、貿易、經濟增長等三方面都不穩固。從外資流入來看,土耳其依賴外債比重增加較快。根據土耳其財政部數據,2018年一季度土耳其外債總額為3032億美元,占GDP比例約為34%。從貿易來看,2017年底土耳其經常賬戶赤字高達390億美元,在全球赤字榜上排名第四。從經濟增長來看,土耳其2017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4%,但通貨膨脹率為10.9%,實際增長為負值。此外,增長的主要行業是房地產、旅游業和基建投資,缺乏制造業和科技創新企業,也沒有出口創匯企業,無實體經濟支撐。最后,基于體制性因素分析,該國為了通過跨境融資發展經濟,對資本項目開放過早過大,使得大量境外資金涌入,造成虛假繁榮;對匯率也缺乏管理,里拉對美元的貶值過于快速,造成投資者對土耳其經濟的信心惡化,這也是危機最具可能性的蔓延途徑。
“黑天鵝”的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應對資本流出的措施、成效與啟示
疫情應對措施
2020年3月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新興市場國家資本流出壓力增大,貨幣持續貶值。除我國外,新興市場國家資本流動主要呈現以下特征:一是資本流出規模和速度較2008年更加迅猛。國際金融協會(IIF)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疫情暴發以來,新興市場資金流出規模達925億美元,遠超2008年次貸危機期間的資本外流數量。二是亞洲和拉美新興市場成為資本流出重災區。三是帶來貨幣貶值。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平均貶值16.08%,巴西、南非、俄羅斯、墨西哥貨幣貶值幅度超過20%。這一形勢下,部分新興市場國家采取了應對措施(見表2)。
成效與啟示
新興市場國家的疫情尚未結束,疫情使跨境資本流動變得難以預測,風險尚未釋放,但新興市場國家采取的資本管理措施成效有限,特別是降息政策促使貨幣貶值。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不約而同降息,加劇了本國貨幣貶值,如墨西哥比索兌美元累計跌幅超過25%。
由此可獲得如下啟示:一是面臨“黑天鵝”事件時,常規化的宏觀審慎政策切換為資本管制,具有較大的必要性。如:巴西直接進行外匯干預;阿根廷限制購匯、跨境轉賬和外債交易,等等。二是以貨幣政策配套資本管制是通用手段,利率下調是否能刺激經濟尚不確定,但跟隨美國實行量化寬松政策是部分國家的共識。新興市場都下調了利率,如中東歐國家以及印度甚至已經是負利率,墨西哥、俄羅斯也擁有較大的貨幣政策空間。三是具有充足外匯儲備的國家抗風險能力較好。如印度采取了一系列資本管制措施后,外國證券投資資金流出放緩、匯率小幅走高,股市回振,外匯儲備回升。
中國經驗:政策實踐與效果分析
宏觀審慎管理成效顯著,但部分工具發揮作用不顯著
隨著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逐步推進,運用宏觀審慎工具成為資本流動風險管理的首要手段。如我國已對于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等早期工具賦予了新的逆周期管理理念,還新運用了遠期售匯風險準備金、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逆周期因子等宏觀審慎管理工具(見表3)。
銀行遠期售匯外匯風險準備金率效果明顯,應繼續作為常備使用工具。這一工具通過提高外匯衍生品交易成本的方式,抑制非理性的外匯衍生品交易行為,進而影響市場主體的順周期行為。2015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對銀行遠期售匯業務進行逆周期調節,要求各銀行按照其遠期售匯(包括掉期、期權)業務簽約額的20%交外匯風險準備金。此后,人民幣貶值壓力有所減弱。2017年9月,美元指數走弱,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中國人民銀行又將遠期售匯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由20%降至零。然而,2018年8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再次將遠期售匯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由零調整至20%,以應對不斷下降的人民幣匯率。進入匯率雙向波動時代,2020年10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為零。
考慮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的被動性與銀行外匯業務評估機制的時滯性。2016年4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本外幣一體化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對跨境融資行為實施市場化的逆周期調節。此后,中國人民銀行又于2017年1月進一步完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政策,不斷拓展市場主體的借債空間。2020年3月,面臨資本流出壓力,中國人民銀行將調節參數由1上調至1.25。但企業舉債與否以及舉債程度受多方因素影響,在抑制流出期間較為被動,更適合在流入較多時期使用。
銀行外匯業務評估每年都會進行,但由于評估并非隨時監控,存在時滯。2018年評估機制首次引入了宏觀審慎風險性指標,近兩年來又不斷進行了完善,形成了對關鍵主體——銀行的風險控制。從效果看,宏觀審慎經營評估對銀行外匯業務經營行為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導向作用,對跨境資本大幅波動具有較好的逆周期調節效果。但由于每年僅評估一次,不能形成即時監控。
基于匯率雙向波動新態勢,“逆周期因子”逐漸淡出具有必要性。“逆周期因子”的首次出現是在2017年5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模型由原來的“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調整為“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因子”。2018年1月,隨著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和外匯供求趨于平衡,“逆周期因子”回歸中性。2018年8月,“逆周期因子”又被重啟,以適度對沖貶值方向的順周期情緒。2020年10月27日,“逆周期因子”淡出中間價報價模型。人民幣升值使企業結匯率增加,售匯率下降,外匯供求和跨境資本流動形勢有所改善,外匯市場風險大幅下降。在此背景下,“逆周期因子”逐漸淡出,符合市場形勢變化,有利于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有序波動。
結售匯綜合頭寸管理作用逐漸減弱。該工具原理是通過逆周期的頭寸上下限設定調整及與銀行外匯貸存比掛鉤或脫鉤來管理銀行順周期行為。但近些年來,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得到了有效管理,且核定的額度基本沒有變化,對于銀行而言,額度基本是足夠的。
疫情下應對資本流動風險的典范:唯一未出現資本流動驟停的新興市場國家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我國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唯一一個未出現資本流動驟停的新興市場國家。國際金融協會2020年3月以來發布的關于新興市場跨境資本流動相關的報告,其中一個主要觀點是除中國外,新興市場資本流入“驟停”,流出創新高,外匯儲備將因資本大量流出而下降,經常賬戶出現大幅調整。
從實際來看,我國各類指標均表現穩定,人民幣匯率跌幅遠低于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貨幣。2020年3月份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僅貶值1.5%,遠低于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平均貶值水平(16.08%),人民幣匯率表現穩定;市場結售匯意愿平穩,外匯市場供求保持基本平衡。
總結經驗發現,從根本上看,由于我國經濟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具備抗擊資本流動沖擊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講話指出,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濟已經在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從數據來看,我國經常項目順差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現在的不到1%,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7個年份超過100%。可以說,國內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就是應對資本流動風險的根基。
從實踐上來看,我國能保持穩定的資本流動,原因有五點:其一,與國外跟隨美聯儲大幅降息形成鮮明對比,我國沒有大幅調低利率,人民幣債券利差優勢得到進一步擴大。其二,我國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日益完善。我國將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由1上調至1.25,體現對國際形勢的正確判斷與政策操作的靈活應對。其三,我國采取擴大再貸款和再貼現業務,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促進經濟特別是投資與消費復蘇,并未像2008年一樣采用多項微觀管理工具。其四,我國的外匯儲備仍然保持在3萬億美元以上,未動用儲備進行過多干預,而是發揮了外匯市場壓艙石的作用。其五,根據外匯市場和跨境資金流動形勢,我國動態調整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并淡出使用逆周期因子,促進經濟市場化自我調節。
總結與政策建議
通過對國際教訓和中國經驗的分析可以發現,一方面,危機后的新興國家在應對資本流動風險時并沒有完全放棄資本管制,但效果并不理想,如土耳其根據宏觀審慎理念采用的資本流動管理措施未能避免貨幣危機。在應對疫情中,新興市場國家采取的資本管理措施成效有限,特別是降息政策加劇了本國貨幣貶值。另一方面,中國是疫情下唯一未出現資本流動驟停的新興市場國家,究其根源在于中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和外匯管理部門的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管理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據此,筆者對我國資本流動風險管理提出了三方面的政策建議。
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形勢,對資本流向保持高度敏感。特別是要結合疫情在世界范圍的演變,關注出現貶值的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流向,科學評估其對我國金融體系構成的沖擊。
宏觀審慎以“治未病”為主,加強動態調整與靈活切換。我國應繼續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和跨境資本流動壓力變化,動態調整政策工具,推陳出新,設計適應國內宏觀經濟發展要求、符合市場運行規律的宏觀審慎工具。
微觀監管應該將資本流動管理措施納入備用。我國當前不應走資本管制的老路,但由于疫情尚未結束,資本流動管理措施應納入政策考慮。在宏觀審慎已無效的前提下,發生資本大規模破壞性流動時,資本流動管理措施可以而且有必要基于臨時、透明、非歧視原則使用。
(本文為國家外匯管理局重點課題“開放環境下跨境資本流動風險防范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昆明中心支行、國家外匯管理局云南省分局,其中朱斌系中國人民銀行昆明中心支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云南省分局副局長)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