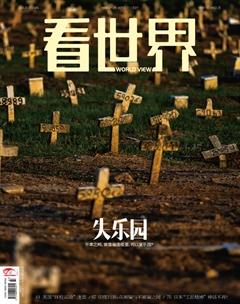去一個“光禿禿”的島嶼潛水
Luna

悉尼全年適合潛水,岸潛是這里既經濟又流行的潛水方式
說到澳洲潛水,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大堡礁。實際上澳洲四面環海,可以潛水的地方很多,悉尼也是其中之一。悉尼全年適合潛水,能見度一般在6~12米,偶爾超過15米,夏季水溫約為22度,冬天約為16度,岸潛是這里既經濟又流行的潛水方式。
最值得期待的海底生物是葉海龍和草海龍。這兩種海龍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亞,兩者都善于偽裝,混跡于海藻叢中很難被發現。草海龍的分布比葉海龍廣泛,相對多見;從外形上看兩者很容易區分,葉海龍是金色的,草海龍是彩色的。
而我這次的下潛地點,是在悉尼的禿島。
禿島與植物學灣
禿島也被譯作“裸島”,首位登陸悉尼東海岸的歐洲人詹姆斯·庫克船長發現了這一區域,并在航海日志中將此處記錄為“一個小的光禿禿的島”。
禿島與拉佩魯茲半島,位于植物學灣的北岬,兩者通過一條木橋相連。這木橋于1887年修建,在此之前出入禿島的交通方式只有高空滑索或者駁船。
1770年4月29日,詹姆斯·庫克船長的“奮進”號登陸的克內爾,位于植物學灣的南岬。他們到達的時候遇到了兩個悉尼原住民,原住民向他們拋出長矛,試圖讓他們離開,庫克向他們開槍把他們趕走了。
登陸的第二天,庫克在此埋葬了“奮進”號的船員福比·薩瑟蘭,后者在航行中死于肺結核。薩瑟蘭是第一個被埋葬在澳洲的歐洲人,庫克將克內爾東部末端的岬角命名為“薩瑟蘭角”,以紀念這位海員。澳大利亞皇家歷史學會于1931年,在“奮進”號登陸地附近,給他立了一塊紀念碑。
植物學灣算得上是現代澳大利亞誕生的起點。
“奮進”號在植物學灣待了8天,由于在淺水區見到了很多黃貂魚,庫克一開始將此地命名為“黃貂漁港”。隨船博物學家丹尼爾·索蘭德和植物學家約瑟夫·班克斯在此搜集了大量植物標本,為了表彰他們的發現,庫克隨后將此地改名為“植物學家灣”,并最終改為“植物學灣”。
庫克的登陸,標志著英國對這塊南部大陸產生了興趣(并最終殖民于此)。

禿島與拉佩魯茲半島,位于植物學灣的北岬,兩者通過一條木橋相連

葉海龍

提琴鰩
1788年1月18日,總督亞瑟·菲利普率領的第一艦隊登陸了植物學灣,準備將此地作為囚犯流放地。由于植物學灣缺少淡水不適合居住,他們隨后駛向了杰克遜灣,也就是現在悉尼港的所在地。他們登陸的1月26日就成了澳洲的國慶日(也是很多原住民口中的“哀悼日”),菲利普后來成為了新南威爾士的首任州長。
同年1月24日,受命于法國路易十六的讓·弗朗索瓦·加拉普·拉佩魯茲爵士和他的探險隊也來到了植物學灣。他們在薩摩亞與當地原住民發生了沖突,多人犧牲。
法國人在這里待了6個星期,與菲利普的第一艦隊交換了一些補給,并在這一帶建立了柵欄和菜園。他們于1788年3月啟航離開植物學灣,后來就失蹤了。幾十年后,有人在瓦努阿圖南部的圣克魯茲群島找到了他們的船只殘骸。
后來為了紀念他,這一區域就被命名為“拉佩魯茲半島”。
植物學灣算得上是現代澳大利亞誕生的起點,不過相比追溯歷史的熱情,我對它的潛水環境更加好奇:這里會不會還是跟兩百多年前一樣,有那么多黃貂魚?
禿島下的海底世界
出于安全考慮,每次潛水都要遵循“潛伴制度”—兩個或以上的人為一組,在下水前互相幫忙穿戴衣服、檢查裝備。
入水后給浮力控制背心充氣,讓自己完全浮在水上,準備就緒后,大家向周圍的伙伴比出“OK”手勢開始下潛。我按下了浮力控制背心的放氣按鈕,一邊下沉一邊做耳壓平衡。
水底覆蓋著茂密的黃綠色海藻,第一次來到溫帶的海底世界,我感到興奮又充滿期待。
隨著深度的增加,我慢慢看到一些魚類和軟體動物。游了一會兒后,激動人心的時刻來了:潛水向導指著一叢海藻向我們比劃。我踢動腳蹼慢慢靠近他所指的目標,發現海藻叢中藏著一只提琴鰩。
它似乎覺察了我們的到來,并對我們也產生了興趣。它緩緩地往外挪了挪,整個腦袋探出海藻。我深吸一口氣,再慢慢吐氣,讓自己下降到可以跟它對視的高度。它淡黃色身體上的褶皺清晰可見,而且就在我觸手可及的地方。我們就這樣對視了幾秒,我很想再跟它多一點互動,但是它似乎對我失去了好奇,又調頭潛入海藻叢中躲起來了。
潛水過程中,身體在水壓的作用下會吸收比在空氣中更多的氮氣。
我后來才知道,提琴鰩是一種比較溫順的海洋動物,也叫“班卓魚”。因為它的外形跟班卓琴有點像。澳洲有好幾種提琴鰩,較為常見的是東部提琴鰩和南部提琴鰩,區分兩者的關鍵是眼睛后的花紋。東部提琴鰩的花紋是一個三角形,而南部提琴鰩是三條豎著的平行線,根據這一判斷標準可知,我們剛剛見到的是東部提琴鰩。
第一潛之后,我們原路返回橋那頭的拉佩魯茲半島。在20度的海水里潛了幾十分鐘還挺冷的,我穿的3毫米的潛水濕衣在保暖方面實屬勉強,同行的其他人,穿的都是5毫米或6毫米的潛水濕衣。
大伙兒圍在一起曬太陽,也是為了讓身體有更多時間排出潛水時吸收的氮氣。在潛水過程中,身體在水壓的作用下會吸收比在空氣中更多的氮氣。由于氮氣不會被人體吸納,如果不能及時將這些氮氣排出,它們就會在體內形成氣泡,給身體造成傷害。所以,在多次潛水之間要預留足夠的水面休息時間,將體內過多的氮氣排出體外。
休息了一個多小時后我們開始了第二潛,可惜這次也沒有尋到任何海龍的蹤影。但并不是一無所獲,我們見到了一條紅色印度魚。當時它一動不動,如果沒有潛水向導提醒,我可能就以為它是一片紅色的葉子而錯過了。我們后來還看到馬賽克海星,它的身上有兩種互相拼接的顏色,外表看上去毛茸茸的,像穿了一件連體毛衣。
結束了這次潛水之旅,我意猶未盡。海底世界那無窮無盡的神秘與瑰麗,讓我想要一再探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