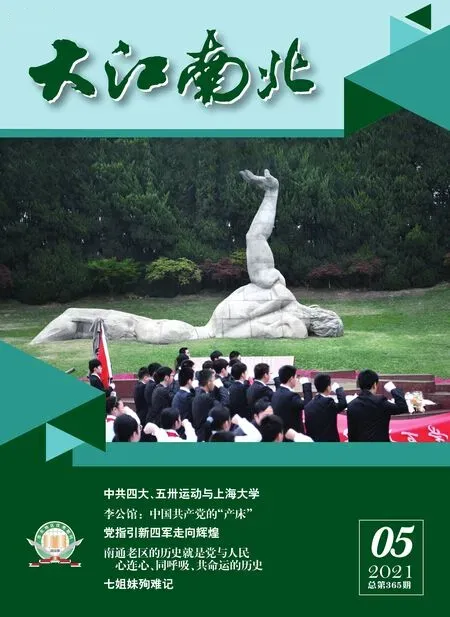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銀行創造的金融奇跡
□ 陳星荻 黃 亞
在中國革命史和中國金融史上,陜甘寧邊區銀行都具有極其特殊的地位。她既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的直接繼承者,又是中國人民銀行的前身之一。因此,可以說,陜甘寧邊區銀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金融事業中肩負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陜甘寧邊區銀行的成立及其發揮的重要作用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作為全國抗日根據地的中心,革命斗爭形勢十分嚴峻。抗戰初期,邊區以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為流通貨幣。為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調劑軍需支援抗日,邊區金融工作在摸索中發展,逐步建立自己的金融機構,形成自己的金融體系。
1935年11月下旬,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將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改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原陜甘蘇區的銀行也被并入西北分行。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共又將原陜甘革命根據地改組成陜甘寧邊區,成立陜甘寧邊區政府。1937年10月1日,陜甘寧邊區銀行在西北分行的基礎上宣告成立,成為抗日根據地人民的第一家自己的銀行。
西安事變后,為了共同抗日,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但國民黨仍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邊區經濟發展受到多方面阻礙。在這種情況下,成立了陜甘寧邊區銀行、光華印刷廠、光華商店等。邊區銀行成立后,繼承和發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的光榮傳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堅持獨立自主的貨幣金融工作方針,先后發行了從屬法幣的光華商店代價券、邊區銀行幣和商業流通券,滿足了市場貨幣流通需求。同時,通過開展信貸業務、治理通貨膨脹、開展對敵貨幣斗爭,建立正常借貸機制,維護了根據地貨幣市場的穩定和統一。
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后,邊區不再使用自己的貨幣,取而代之的是國民黨的法幣。但是,國民黨政府為了阻礙邊區的經濟發展,限制商品交易,只給邊區大額的法幣(只有5元和10元,沒有更低面值的法幣),使得商品買賣中無法找零、無法交易。在這種情況下,1937年10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決定成立陜甘寧邊區銀行,為了解決找零的需要,以延安光華商店名義發行壹元以下的代價券。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政府停發了八路軍和新四軍軍餉,陜甘寧邊區政府遂于1941年1月31日頒布法令,禁止法幣在邊區流通,并于同年2月授權邊區銀行發行邊區銀行幣,規定在邊區境內只準使用邊幣。邊區銀行幣擺脫光華券與法幣的主輔幣券關系,成為獨立于法幣之外的貨幣體系,為粉碎國民黨經濟封鎖,支持抗戰起到巨大作用,邊幣的發行充分彰顯了我們黨在經濟上一貫堅持的獨立自主性。

陜甘寧邊區銀行紀念館外景

陜甘寧邊區銀行紀念館內景
遵照“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邊區財經工作總方針,陜甘寧邊區銀行制訂了一系列具體的金融工作政策和措施,大力發展存款、匯兌業務,積極發放生產和貿易貸款。
經過艱苦卓絕的探索和實踐,邊區銀行由半獨立發展到獨立、從經營光華商店到全方面開展銀行業務,成為了邊區重要金融樞紐,在促進邊區工農業生產發展和繁榮商業貿易,幫助解決財政困難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抗戰勝利奠定了經濟基礎。
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在金融戰線的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緊密結合邊區實際加以創造性運用和發展,逐步形成中共紅色金融思想的雛形。邊區銀行的成功金融實踐,離不開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貨幣金融思想的科學領導。
毛澤東高度重視貨幣金融問題。在領導陜甘寧邊區軍民浴血奮戰的過程中,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貨幣金融學說,認清中國社會性質和具體國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基礎上,結合中國革命實際,針對近代中國金融市場,創造性論述了關于銀行、貨幣和金融等方面理論,形成了延安時期特有的紅色貨幣金融思想。
1940年1月,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銀行國有化理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在《論聯合政府》中,他又指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在《論新階段》中,他提出:“有計劃的與敵人發行的偽幣及破壞法幣的政策作斗爭,允許被隔斷的區域設立地方銀行,發行地方紙幣。”正是在充分吸取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必須掌握銀行、利用銀行的思想基礎上,邊區政府在延安成立了邊區銀行。
作為流通界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必要量規律,要求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商品供應量相適應,這就涉及了貨幣發行的方針和客觀依據。發展根據地經濟,需要銀行,也需要貨幣,更需要金融。因此,毛澤東非常重視貨幣發行,也一貫主張貨幣發行要根據經濟的需要,實行穩定通貨的方針。為確保紙幣幣值穩定,毛澤東明確提出根據地貨幣發行要以發展經濟為第一目的,即堅持經濟發行為主、財政發行為次的原則。
經濟決定金融,決定金融的穩定,決定幣值的穩定。這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貨幣金融思想。1938年8月,毛澤東認為紙幣發行要有準備金,要有適當的貿易政策做后盾,應維持不低于偽幣之比價,保持匯率的穩定,而不應超過市場上的需要數量。可以說,他是想通過考量貨幣發行量與實際物質產量之間的關系來穩定幣值,認為只要貨幣發行量不大大超過實際物質產量,貨幣就不可能出現大幅度貶值。
為維護邊幣的信用,毛澤東曾指出:“商品與貨幣流通量成正比例說,亦不宜堅持,宜估計到許多新條件,還有待今后研究。如持之過堅,將來不準,有損信譽”。他同意時任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的一些意見:“邊幣跌價的基本原因在于邊幣數量和商品數量的矛盾”,“出入口貿易不平衡,引起邊幣對外價格的跌落,邊幣對外價格的跌落,又轉回來促使其對內價格的跌落”,“邊區內部總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邊幣流通量,有一部分被法幣代替了,結果使邊幣量與商品量的矛盾更加尖銳化。”
邊區銀行的創新性金融實踐
由于抗戰初期邊區沒有經濟實力與法幣作針鋒相對的斗爭,邊區政府只能對法幣采取聯合或維護的政策。等到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政府充分暴露反革命本質,中共果斷嚴禁法幣在邊區境內繼續使用,堅決發行自己的貨幣,謀求建立獨立自主的邊幣市場。從1941年1月至1944年6月,在前后三年半左右的時間里,邊區政府共發行邊幣342321萬元。邊幣的發行,使國民黨企圖困死邊區軍民的夢想被打破,通過法幣搜括邊區人民財富的黑爪被斬斷。
1938年,毛澤東在《邊區的貨幣政策》中指出:“邊區軍費浩大,財政貨幣政策應著眼于將來軍費之來源。”在與謝覺哉討論邊區的經濟問題時,他指出,邊區的經濟政策“首先是根據于革命與戰爭兩個基本的特點,其次才是根據邊區的其他特點。”1941年1月,他又兩次致函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主張貨幣首先應從滿足革命戰爭需要出發,不要過于限制貨幣發行數量。在毛澤東貨幣金融為中心工作服務思想的指導下,邊區政府在皖南事變之后將財政工作方針由“爭取外援,修養民力”轉變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貨幣金融政策由支持財政發行轉變到支持經濟發行,銀行功能定位由財政支付機構轉變到管理金融機構。按照毛澤東在《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中提出的要求,邊區銀行設立農貸辦事處,在財政許可的條件下,逐年增加農業貸款。通過發放耕牛、農具、青苗等農業貸款,幫助農民解決了農業生產中的不少困難。隨著生產的發展、經濟的進步,邊區銀行財政性發行日益減少。所有這些措施,都直接支持了邊區人民武裝的發展壯大,支持了邊區的軍事工作,對于保障人民軍隊物資供給、軍費來源,起到了重要作用。
隨著抗戰進入艱難階段,一方面,國民黨完全停發了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而且還加緊對邊區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另一方面,此時的法幣幣值早已沒有抗戰之初的堅挺,呈現出不斷膨脹的態勢。1941年1月,中共中央與邊區政府發布了《關于停止法幣行使的布告》;2月,邊區政府連續發布了《關于發行邊幣的布告》與《關于宣傳發行邊幣的訓令》;10月,邊區政府發出了《規定鞏固邊幣穩定金融辦法的訓令(秘密)》。這一系列法令的發布,標志著法幣作為邊區本位貨幣流通地位的結束和邊幣成為邊區唯一法定通貨本位幣的開始。接著,邊區又相繼成立貨幣交換所,擴大邊幣流通范圍。1944年3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任命陳云為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陳云在經過調查研究和深入分析之后,首先確立銀行的企業性質,不讓財政隨便從銀行掏錢,使其擺脫財政出納地位,以控制財政發行;接著處理邊幣與法幣的關系,整理邊幣;最后通過發行商業流通券,“偷梁換柱”地使邊幣與法幣比價提高到1:1,在挽回邊幣信譽、防止通貨膨脹、穩定物價等方面,基本達到了整頓金融、穩定金融和發展金融的目的,取得了貨幣斗爭的決定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