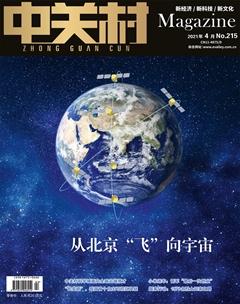國家行動:1079名烈士回家之路
呂高排

“外公的名字——‘羅振吉這三個字,由父輩傳給兒女,兒女再傳給孫輩,最終刻在整個家族每個人的腦海里。”清明節前夕,記者連線遼寧營口鲅魚圈經濟開發區的退役軍人何志巖,一段血淚史浮出水面。
何志巖外公羅振吉,于1948年參軍后便杳無音訊,他的外婆、羅振吉年輕的妻子從24歲開始等丈夫回家,一直等到82歲。她在彌留之際對外孫何志巖說:“你外公可能早就不在了,苦苦等了一生,今生無緣就看下輩子了……”
尋找親人的路,漫長,孤獨,不知終點。73年后的2021年,一條關于羅振吉的消息讓這個家庭瞬間沸騰:烈士找到了!羅振吉唯一在世的兒子、何志巖81歲的舅舅羅福全終究等到了這一天,這位因腦溢血臥病在床的老人,一個人無聲地哭了兩天,怎么勸都勸不住……
在一個民族發展圖譜上,英雄永遠是最閃亮的精神坐標。羅振吉只是千千萬萬烈士之一,何志巖也只是千千萬萬烈士親屬之一。“我們愿做提燈者,照亮他們回家的路。”退役軍人事務部褒揚紀念司有關領導介紹,截至2021年清明節,共發布烈士尋親信息12180條,為1097位烈士鋪平回“家”之路。
世界上最愛的人去哪里了
家住遼寧省營口市蓋州市的羅振吉是家中的寵兒。父母面朝黃土背朝天干了大半輩子,辛苦攢下的錢除了補貼家用,全部用來支持羅振吉上學。“我外公一直讀到了高中畢業,是當地學歷最高的人。”當過4年兵、已經54歲的何志巖對記者說,羅振吉內心也有不小的抱負,“他高中畢業后沒打算立刻回家,想先成就一番事業,但長輩給他操辦了婚事,他又極其孝順,就順著父母想法回鄉成婚。”
1939年,年僅17歲的羅振吉成了家。之后8年,他和妻子高氏靠著一雙勤勞的雙手,在自家田地里辛勤勞作,養育4個乖巧可愛的兒女。
平靜的生活一天天過去,心懷報國之志的羅振吉終究還是向家人道出參軍的想法。何志巖猜測,“外公應該是慎重考慮了很久才說的,不然,他不可能丟下二老和四個孩子就走”。
1948年,羅振吉參軍。彼時,大兒子6歲、二兒子4歲,大女兒3歲,最小的女兒才6個月。
全家人都盼著羅振吉能夠早日歸家,他卻消失在茫茫人海中,音信全無。此后,每年的年夜飯飯桌上,都有一個空缺——最歡樂的時刻,卻是這個家庭最痛的日子。
世界上最親的人去了哪里?
發出同樣疑問的還有孔照遠的家人。相距羅振吉家40多公里的蓋州市老古嶺子村,孔姓人家里有兄弟二人,哥哥孔照遠讀完小學后幫著父母務農,后與一位同村姑娘成婚。
孔照遠為人忠厚老實,心地極其善良。雖然家中光景不好,但每逢有人來乞討,他都會讓妻子送去兩碗飯:他怕別人吃不飽又不好意思多要。
對待他人如此,對待至親更是體貼入微。孔照遠孝順父母,關愛弟弟。從結婚到犧牲,從未與妻子吵過一次架。
1947年,解放戰爭已打響兩年,一支共產黨軍隊途經老古嶺子村,孔照遠看著這支即將前往戰場的隊伍心潮澎湃。可是父母年事已高,弟弟還沒成家,女兒才4歲,他實在于心不忍。
沒想到全家一致支持!于是,立志為新中國解放事業出一份力的孔照遠正式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2軍124師331團衛生隊的一名戰士。
1950年,全國很多地區都傳來解放的喜訊。然而,孔家人沒有等來歸人,只等來了孔照遠犧牲在外的噩耗。

2019年4月4日上午,第六批在韓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遺骸安葬儀式在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舉行。圖為志愿軍烈士遺骸的棺槨在官兵的護送下進入地宮安葬
“部隊來了人,說我父親在給戰友送水路上被敵人射中頭部,正在醫院搶救。”孔華說,當時母親懷著已經8個月的她,帶著7歲的姐姐晝夜不停趕赴部隊醫院。
“那時候我父親已是昏迷狀態,我母親看了他最后一眼,過了一會我父親就去世了。”71歲的孔華哽咽了,“我母親懷著我,哭得太傷心,身子也虛弱,部隊的人把她送回家。戰爭隨即又起來了,我爸爸那支部隊,轉戰南北,不知去向。再也沒人知道父親安葬到了哪里……”
對親人的思念,讓一個個家庭陷入綿綿悲痛之中——
1955年,福建莆田17歲的小伙子宋文桂,按捺不住與同胞們一起沖上戰場的愿望,迫不及待地加入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我們村一共去了10個年輕人,我二叔就是其中之一。”宋文桂的侄子宋德金告訴記者,他聽老輩人講述二叔出征時的場景,“他可勇啦,一聽有人來征兵,扔下手里的活兒就去報了名。”令人惋惜的是,當年參戰10人,9個平安歸來,唯獨宋文桂,一去不返。
1958年末,與宋文桂一同作戰的同鄉戰友,將其犧牲的消息帶回老宋家,頓時,整個家庭被悲痛吞噬、擊碎,此起彼伏的哭聲讓人聽了心痛不已。“我二叔的戰友帶回消息后沒多久,部隊的通知也到了。他是為救新兵而死。”
家里窮得吃完上頓沒下頓,“我們整個家庭,全靠二叔的撫恤金活下來,可是我偉大的二叔到底埋在哪里,連一粒骨灰也找不到……”
“請國家幫我找到姥爺,
讓我母親瞑目”
2018年5月10日,國家退役軍人事務部成立不足一個月。
“求助!我的母親臨終前有一個心愿,找到她的父親,請國家幫幫我,了卻她的心愿,讓我母親瞑目……”
一封求助信,飛到了剛剛組建的褒揚紀念司。彼時,這個年輕的司只有6名工作人員,大家都沒有多少經驗。而烈士尋親,像是在暗夜里尋找螢火之光,是一項非常復雜敏感的系統工程。

他們將這封信貼到辦公室最顯眼的位置,時刻提醒每個人的初心使命。
寫信的人叫謝從安,河南鄧州人,49歲。她的姥爺魏澤升參軍時,謝從安的母親魏慶祥只有8歲。4年后的一天,魏澤升在反三路圍攻戰役中犧牲,被埋葬在四川省通江縣一帶,從此石沉大海。謝從安永遠忘不了母親魏慶祥臨終時的囑托:“合不上眼啊,找了一輩子,也沒有找到你姥爺……”自此,她把尋找曾祖視為自己的責任。她覺得她與從沒見過的烈士魏澤升之間有一種極為玄妙的聯系——她一定要找到他,不讓他一個人孤獨地長眠。
可是在退役軍人事務部成立之前,謝從安一度有些絕望,母親和謝從安苦苦找了64年,什么辦法都嘗試過了,無果。
1960年,魏慶祥踏上赴四川尋找父親埋葬地的路途。從河南到四川,她走了整整31天。常年流落街頭,一個大字不識,生活貧困交加,她患上了嚴重的腎病。
尋找以失敗告終。這之后,她又三次出門,“找到父親”,成為她的人生信條,可是直到1984年去世,魏慶祥仍然沒有實現心愿。
魏慶祥的女兒謝從安接過了母親的心愿,一次接一次的失敗之后,她試圖用另一種方法彌補遺憾——她在魏家祖墳上,為先祖魏澤升設了一處“衣冠冢”……
2018年8月,就在退役軍人事務部成立4個月之際,全國著名的革命老區、福建龍巖市想在9月30日“烈士紀念日”邀請烈士家屬參加活動,但是很多烈士都是外省籍的,在龍巖當地找起來很困難。
6月25日,龍巖市委、市政府與頭條尋人首次聯合發布了《先烈后人,您在哪里?尋找江蘇常熟籍烈士任林生后人》的消息,啟動尋找戰爭年代犧牲在龍巖的先烈后人行動。
依托精準地理位置彈窗技術,頭條尋人將消息推薦給烈士家鄉部分用戶。2018年6月27日一早,頭條尋人項目工作人員接到來自江蘇媒體的消息。
科技與社會善意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蘇州電視臺“新聞晚班車”記者陳志佳一早就來了,她向頭條尋人的工作人員反饋,已經與當地政府部門電話核實,烈士任林生有一個妹妹任秀珍,今年97歲。
當大家趕到任秀珍家時,她正臥病在床。因為中風,任奶奶的語言能力已經喪失。她的女兒確認,烈士任林生就是自己母親的親哥哥。他們還獲知:烈士的兒子去世了,他的孫子和孫女仍然生活在常熟趙市鄉。
52歲的任麗文,正是烈士任林生的親孫子。在烈士老宅,他捧出一張泛黃的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軍區頒發的家屬證明書,泣不成聲:“爺爺1950年就犧牲了,68年后,我終于知道爺爺的名字刻在龍巖烈士紀念碑上。”
之后,退役軍人事務部門、烈士陵園與頭條尋人簽定合作協議。2018年6月27日,今日頭條正式啟動“尋找烈士后人”公益項目。時任今日頭條副總編輯徐一龍信心十足:“我們有能力做好這件事。”
2019年7月10日,重慶市退役軍人事務局和頭條尋人率先簽署烈士尋親合作備忘錄。9月24日,四川省退役軍人事務廳也與頭條尋人簽約,聯合開展“尋找烈士親人·傳承英烈精神”公益活動。雙方決定整合各界力量,構建協同高效的合作聯動機制,拓展新渠道、探索新方法,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方式,提高尋親效率,共同挖掘整理英烈故事,傳播英烈事跡,弘揚英烈精神。
簽約不到一個月,謝從安便從今日頭條App彈窗中發現一條尋找烈士后人的啟事,附有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的電話。
謝從安立即撥通電話,烈士陵園工作人員要了她曾祖父的名字,承諾三天內給予答復。
幾小時后她就接到電話,工作人員大聲說:“這里有你曾祖的名字,快來吧。”
謝從安顧不上說感謝的話,直接打電話通知家人:“全部準備好,我們要一起去川陜烈士陵園祭拜曾祖父!”
2021年3月10日,記者視頻采訪謝從安的時候,整個事情已經過去一年半時間,這個河南女子仍處在興奮中。她語速很快,仍處在興奮中:“當時特別特別高興,我為媽媽找到了爸爸,簡直有點不敢相信。當然,這不是我的功勞,是退役軍人事務部門的成立,了卻了全家人的心愿。”
信息技術助力,“終于找到你”
猶如在黑暗中見到一絲光明,猶如落水后出現浮板。聽說國家成立了退役軍人事務部,遼寧營口的孔華,思親之火再次點燃。她不斷祈禱:一定找到父親,一定找到父親!
孔華捧著2014年補發的烈士證,淚水吧嗒吧嗒地向下掉。在她的悉心保存下,7年的時光似乎沒有留下痕跡,紙頁仍舊光彩如昨。
每當想念父親,孔華都會拿出烈士證明書,撫摸著紙頁上父親的名字,回想記憶中那張老照片里父親的模樣,內心傾吐著對父親的思念。
“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母親懷著我才八個月,從小到大我都沒有體會過父愛。現在,我是父親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骨血。”孔華回憶道,打她記事起,母親就帶著她去河邊給父親燒紙,“在紙包上寫上父親的名字,然后隨紙錢一起燒了……也不知道我父親在地下能不能收到……”
1992年,孔華的母親去世。如今回想起母親去世前的叮囑,孔華仍記憶猶新:“我母親說,她這輩子最難過的就是沒有找到我父親的安葬地,她讓我一定找到,一定去祭拜……”
2020年7月27日,大連市烈士陵園與頭條尋人聯合發布一則名為《尋遼寧營口籍烈士孔照遠親人,他長眠大連市烈士陵園,靜待親人》的消息,精準地域彈窗到遼寧省營口市。
孔華和家人們并沒有第一時間獲悉,等她從烈士尋人志愿服務團志愿者丁一朕處得知消息,已經是2021年1月31日。“我給高興得啊,立馬找來看了。一看到信息發的沒錯,眼淚立馬就掉了下來……”
疫情稍一穩定,孔華就讓孩子陪她趕到大連。“一想到這輩子還能親自去祭拜我父親,我這顆心就激動得狂跳……我太感謝退役軍人事務部門和頭條尋人這個平臺了。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我到死都圓不上這個夢。”
“找到了我爸,就找到了‘根。”那一天,孔華在烈士陵園一坐就是半天,眼淚也不知道為何這么多,流完一遍,又來一遍,像長河,無窮無盡。臨別之前,她跪在父親的名錄前磕了3個響頭,從墓地取了一抔土。“爸,我們帶您回家……”
歷史的傷口就這樣彌合。與此同時,羅振吉烈士的下落,也傳來好消息。
羅家人以為,這個遺憾永遠難以彌補,直至退役軍人事務部門發布的一條消息,讓全家人看到了希望。
以烈士籍貫地為圓心、向特定的頭條用戶推送尋人消息。隨著時間推移,不斷擴大推送半徑。科技帶來的效率,相比過去在電線桿上張貼尋人啟事大大提高。2019年12月12日,一則尋人消息,像一根接力棒,傳遞到一個又一個人面前。
“我們蓋州市的戰友有一個微信群,那天晚上12點多,我順手點開戰友轉發的尋人消息。”草草瀏覽信息的何志巖沒有想到,竟然看到了那個刻骨銘心的名字——羅振吉!
“我看到外公名字激動得顫抖。”何志巖難耐內心的欣喜,凌晨一點半,他給姨父、表弟撥去電話,“我實在是太高興了,太想告訴他們這個好消息了!”
多年的思念終于迎來一個圓滿句號,2021年清明節前夕,何志巖和家人迫不及待動身,前往平津戰役紀念館。在刻有姥爺名字的烈士紀念墻前,多年的思念一下子噴涌而出。何志巖一家再也控制不住情緒,嚎啕大哭。
何志巖淚水婆娑:“姥爺,我們來看您來了……”
“你閨女更想你,想了一輩子,也去那里陪您了;你兒子也81歲了,身體不太好……”
眼淚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生者與逝者的對話。墓碑上沉寂的文字此刻也鮮活起來,有血有肉。
何志巖將那個陌生又熟悉的名字擦了又擦。這雙親人的手,拂去了80多年的塵土和孤寂。
轉機同樣發生在宋文桂烈士親人身上。
“2021年1月5日,我得知消息,激動得很啊。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們家人只知道二叔的遺骨埋在廈門某一處,具體在哪里卻一無所知。”宋德金說。
聽聞宋文桂的英名鐫刻在廈門后巖山烈士陵園,宋德金的內心焦急萬分,立即與工作人員取得聯系,著急得連話都說得磕磕絆絆,“謝謝你們,謝謝你們!我一定親自去一趟廈門,離家這么久,他該想家了。”
點亮烈士回家之路
全國在行動
這是記者發稿前采訪到的最后一例烈士尋親——
遼寧省蓋平縣(今蓋州市)第十區東溝村徐家的供臺一隅,紅色的臺布上悉心擺放著紅燭、高香、酒盅、香爐和水果,供臺后方色彩鮮明的背景,是徐家的家譜。家譜上依次記載了九代人的名字,輩分更迭中,一個家族的歷史盡顯其中。
“我二伯名字就在忠字輩那一欄。”村民徐其森操著東北話說。他口中的二伯,是犧牲在抗美援朝戰場的烈士——徐忠貴。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如箭在弦,東溝村村干部挨家挨戶動員年輕人去朝鮮支援前線,大家知道徐家的大兒子犧牲在戰場,便沒有再去動員。
徐忠貴聽聞征兵消息,早已動心良久。“我不知道我二伯是怎么和我爺爺奶奶說的,也不知道我爺爺奶奶有沒有勸他,但是他義無反顧地去了戰場。”徐其森說。
上天并沒有眷顧已遭喪子重創的徐家。1952年4月20日,徐忠貴在朝鮮戰場犧牲,待家人得知消息,已經是好幾個月后的事情。“大兒子、二兒子接連犧牲,想想二老得有多難過。”徐其森抹了一把眼淚說。家人聽聞徐忠貴犧牲的消息,也有過前去尋找遺骸的念頭,“但是遠在朝鮮,又在戰火中犧牲,這怎么可能?”家中兩位烈士都不能落葉歸根的遺憾,深深扎在徐家人的心窩里,“家中長輩們按照當地習慣,在山上給大伯和二伯建了兩座空墳,后來逢年過節,我們都去給他們上墳、上香、燒紙錢。”

向英雄烈士敬獻花籃
2021年2月10日,一個名字,像一顆神奇的石子,在徐其森的心中激蕩出一圈大過一圈的漣漪,他激動得難以言喻:“我真沒有想到,那么多年了還能知道二伯伯的消息。我伯伯用生命為國家效力,國家也沒有忘記他,我特別特別高興,特別特別激動。”
徐其森趕忙捧出烈士證,他的手有一點點顫抖,那張烈士證似乎很輕很輕,又似乎很重很重……
至此,1097名烈士的回家之路圓滿結束。每一個數字背后,都是一個家庭幾十年的期盼——是等待了一輩子的父母終于知道兒子的下落,是守了一輩子、怨了一輩子、苦了一輩子的妻子終于釋然,是面孔已模糊在記憶里的孩子得知父親的故事……
1097名,只是一個起步的數字。記者寫出的,也都是圓滿的故事。更多的家庭,沒有找回親人。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
“烽火歲月,無數英雄烈士為了國家的繁榮和民族的昌盛奉獻出生命與熱血,然而,由于時間間隔久遠,信息資料查詢困難;后人年歲較大,家人知悉情況不全;行政區域變化,缺少有效聯系方式等原因,許多英雄烈士還沒有找到失聯的親人,還沒有圓魂歸故里的遺愿。”退役軍人事務部有關領導告訴記者。
“更多的烈士親屬、退役軍人、志愿者服務團體走進尋訪先烈的隊伍中來,‘尋找烈士后人公益項目已逐步實現從退役軍人事務體系到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延伸轉變,極大地提升了成功率,在全社會樹立起緬懷英烈、崇尚英雄的良好風尚。”4月2日,與退役軍人事務部簽訂合作備忘錄的頭條尋人公益項目負責人周有強告訴記者,“我們的工作,就是在大數據信息時代的推動下,搭上迅速快捷的超車道,為烈士回家搭建橋梁。”
烈士尋親工作任重而道遠。記者遺憾地發現,革命戰爭年代犧牲的烈士約有2000萬名,目前有名烈士僅196萬,其中有明確安葬地的才55.9萬;此外,我國在境外作戰犧牲安葬人員約20萬,現已查實安葬地的不到11萬,與烈士親屬、社會公眾的期待之間還有較大差距。
“英魂永在,烈士千古。戰爭年代,有很多無法想象的現實條件和無奈之舉。我想,我的英雄爺爺在保家衛國的戰場上慷慨赴死的時候,不可能也不會想到自己要留下什么英名,贏得什么尊崇。國家沒有忘記他們,人民在紀念他們,就是對他最好的慰藉。”一位至今沒有找到遺骸的烈士的親屬向記者表達了自己的心聲。
令人欣慰的是,這一國家行動每天都在和時間賽跑,每跑贏一次,就會多找回一位烈士親人。“我們愿意一直跑下去,幫助更多烈士回家。”他們的信念堅定如磐。
記者了解到,退役軍人事務部在去年成立烈士紀念設施保護中心(烈士遺骸搜尋鑒定中心)基礎上,還將成立國家烈士遺骸DNA鑒定實驗室,對烈士進行信息采集,建立數據庫;同時,還要建立一個烈士家屬信息庫。通過兩個信息庫之間的有效對比,繼續尋找其他烈士的親人。對那些沒有對比成功的,將在公安部DNA數據庫中進一步對比。對已發掘的烈士遺物進行清點整理,全部建立電子化檔案。通過遺物線索,繼續為其他無名英雄開展尋親活動。
一個全國人民共同參與的烈士尋親活動,正在蓬蓬勃勃的開展。記者深信,在這個陽光明媚天正好的清明時節,一個又一個家庭,走進一個個烈士陵園,將家鄉的一抔厚土、家人的一片綿長思念,一起帶給長眠于地下的英雄,讓他們魂歸故里……
(本文得到退役軍人事務部褒揚紀念司、烈士紀念設施保護中心、“頭條尋人”項目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謝。)